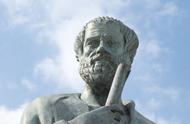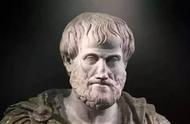《物演通论》作者:王东岳先生
引子:广义与狭义谈到哲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哲学,借用《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可用于涵盖任何达到“形而上”的思维。
所谓“形而下”,就是直观看到的事物;所谓“形而上”,就是超出直观的思维。举个例子,在生活中,我们能见到各种具象的马:黄马、白马、胖马、小马、母马等;而在头脑中,当马的视觉形象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立即得出马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形而上的最初级的抽象。
从这个意义来讲,广义的哲学,基本上等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哲学一词,涵盖了任意抽象的思考。
狭义的哲学,基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研究,仅见于古希腊。钱钟书先生曾在《围城》一书中,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到:“中国只有哲学家学家,而从来没有哲学家。”
所谓“哲学家学家”,即研究某一个哲学家的学者,比如尼采专家、康德专家等。真正的哲学家,研究的是狭义哲学,即在通常人思维够不到的那个深点上进行讨论的学问。
我们还是通过哲学家们自己的话语,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狭义哲学吧。
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这样指出哲学探讨的起点:
对一个人而言,假如他看见的众人和万物,都不曾时时看上去仅仅是幻象或幻影的话,他就不会是一个拥有哲学才能的人。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这样评价智慧:
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这样介绍哲学家的精神状态:
对自然万物,任何事物始终保持惊异和追问感,才是哲学的起点。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这样说明哲学家的事业:
哲学家的事业,正在于追究所谓自明的东西。
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这样描述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主流知识观念:
不可知论,是唯一可靠的哲学。
由这几位的观点,容易看出,狭义哲学和我们日常理解相去甚远。
接下来,让我们仍然从古希腊说起。
古希腊的追问三种用智方式
谈到古希腊,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狭义哲学,仅见于此地呢?
这需要从人类的三种用智方式谈起。
第一种方式,叫信主。其基本思路,是在宗教信仰下整理文化。
自远古迄今,人类的主体部分,都有着信主文化。也就是说,世界是由造物主缔造的。只要确信这一点,一切问题都得到化解,因此用不着探究。
信主文化,会对人类的智慧运用产生明显的遮蔽和压抑。当神学将世界的终极归咎到造物主那里之后,随后的哲学追问,只能是造物主是如何操纵世界的。因此,早年的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婢女。
有趣的是,这种对神学展开哲学追问的现象,仅见于古希腊。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神学本身停留在追问终结状态,也就是神已经把所有问题回答了。
古希腊人,信的是众神。但古希腊的神,非常接地气,拥有着与人类一样的*与弱点。实际上可以说,古希腊的众神,是人格在天空舞台上的另一重展现。因此,古希腊的神学,不构成思想压抑的状态。
不仅如此,古希腊的神学,反而成为古希腊哲学家智慧调动的一个启动点。
对此,苏格拉底曾经就古希腊哲学与神学的奇特关系,做过精辟的总结:
当人用智慧调动到极端,追问到神那里,仍然不肯罢休,而要搞清神的能力所在的时候,就是哲学探讨问题的开端。
第二种方式,叫重德。
中国古代,作为最典型的农业文明,见证了单位土地所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成百倍的增长。人口暴涨,而土地资源却是有限的,于是带来强烈的人际关系和资源关系的过度紧张。
这就导致中国先秦时代的先贤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在人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探讨之上。他们的思想,表达为人际关系的整顿,因这一脉学问的重点在于道德讨论,因而称为重德。
重德文化,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和基础,进而堵塞了其他智力调动的通道。产生的结果就是,自先秦时代,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学者很少有过对自然学的整体追问。
重德文化,对中国思绪的明显遮蔽,体现在孔子的一句名言之中: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伦理道德之外的思绪,被孔子称为异端,并号召大家对其进行攻击,从而消除异端思想所可能带来的危害。由此可见,在重德时代对思想压抑的程度,何其之重。
第三种方式,叫爱智。
爱智,就是哲学一词在希腊文中的本义。在日常生活中,智慧的调用主要是在实用层面,所以称为学以致用。然而,古希腊哲人认为,但凡能够应用的学问,它就是学问的完成态,不再构成学者应该继续追究的课题。
这种只研究不能用的东西,纯粹的无用之学,才叫哲学。在这一点上,它和中国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思路,刚好相反。
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会这样说的原因:
我听过许多人谈话,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所有的人都离智慧很远。
因而,爱智是一种智能运动的非常规特殊调动方式。
人类的智力,和其他身体器官一样,是有功能储备的。我们所有人在正常情况下,是做不了这种功能储备调用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智就是对智力功能储备部分加以调动。
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狭义哲学的爱智,指的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调用的寻常智慧,而是调动深层的智慧潜能。
作为“物理学之后”的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这个词,从字面层面看起来几乎完全一致。然而,两者的内涵却有很大不同。
中国的形而上学,不做智慧储备的极端调动,仅表达为意识对直观的初级整理。而“物理学之后”的哲学,指的是对直观物理现象之后的智慧形态进行精密琢磨。
因此,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曾经说过:
哲学,需要有自己的专用符号系统。
这说明,哲学的思境不在日常思境之中,以至于哲学的表述,用日常语言都不足以进行。
为何是古希腊
了解了三种用智方式之后,很自然地会问:为什么爱智成为古希腊的首选方式呢?

古希腊地图
简单来说,答案是:由古希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
首先,古希腊地貌多山石、土壤贫瘠,同时雨季在冬天、旱季在夏天,共同导致农业文明难以展开。而地中海,作为欧亚非三大陆包围的内湖,具有极为便利的经商交通条件,这就导致半农业、半工商业文明得以展开。
其次,工商业文明的发展,与农业文明相比,需要更高程度的智力调动。同时,腓尼基人在环地中海地区广泛的贸易交流中,缔造了拼音文字。而拼音文字,是造成语法逻辑思维结构的前提 。
再次,古希腊的地理结构是碎片化的,由诸多半岛和岛屿组成。因此,它形成了独特的、无法完成政治一统的生存结构。古希腊文明,因而成为典型的城邦文明。
综上,碎片化的地理结构,不利于农业、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经济基础,以及非统一性的城邦政治格局,共同缔造了古希腊思维的开放,和思维多样化的交流。
在各个不同城邦和不同地域,可以发生不同的思绪,然后在便利的交通条件下,不同的思想不断地发生碰撞与交流,激发起智慧潜能的充分调动。
这一切,共同为古希腊哲学的诞生与茁壮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和外部条件。
因而,哲学在古希腊的发生,不是由少数人设计的,而是由特殊的生存结构所决定的。
哲学与逻辑假设与证明
西方文化,基本的展开形式,叫假设与证明。
所谓假设,即我不承认我所看见的是实在,它只是假象或者现象。既然我看到的都是假象或现象,那么实在和真存是什么?
于是,我就只能假设。有了假设,自然就需要证明。而且,既然是假设,眼见为实的证明,当然无效。因为眼见的东西都是假象,所以不足以作为证明。
因此,假设之后的证明,就绝不是常规状态下的思境和见识的总和。
实际上,假设才是人类智慧深度调动的关键点。试想,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文明成果,哪一样不是假设的产物。
而正是对假设进行证明的需求,引发了逻辑学的开端。
经典的哲学与科学巨著,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及王东岳先生的《物演通论》,整本书的核心内容都是证明。
由于证明是纯逻辑环节,是一环套一环、不能有任何缺环的过程,所以读起来特别费劲。由此引发,一切学问与知识,实际上是假设和证明的产物。
概括来讲,纯逻辑的假设,加上纯逻辑的证明,共同构成哲学和科学追问的开端。
逻辑的规则
既然假设的证明,不能依赖于感观,而是依赖于逻辑,这就要求逻辑的运行必须要有严谨的规则。因而,假设与证明,所使用的逻辑,也被称为精密逻辑。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门逻辑学,就是亚里士多德创造的形式逻辑。这里的形式,不是指事物的外形,而是指思想的形式,或者说感知的形式。
在人的思想形式里,2 2=4 永远成立。而这个给定的逻辑形式,决定了世界万物的假象,其实是被规定死的。从而,才能解释万物假象因何而流变,这是形式逻辑的内涵。
亚里士多德,给予逻辑的定义是,必然的导出。当素材给定的时候,你在逻辑上推演,结论是给定的。也就是说,结论被逻辑形式给定,所以逻辑形式才是核心与关键。
所谓形式逻辑,就是抽掉对象的具体要素,看逻辑形式怎样运行。对此,亚里士多德总结了三条定律:
- 同一律:即A=A;
- 排中律:即A是B,或者A不是B;
- 矛盾律:即A不是非A。
以后,由德国近代古典哲学家沃尔夫和莱布尼兹追加上第四律:充足理由律,就是当你做A、B等判断的时候,你的判断得有延续性的根据。
形式逻辑的四律,还可以从知性的角度,加以深入解读。所谓知性,是指生物体在识辨跟它生存相关的依存条件时,所不得不发生的判断行为。
知性是与感性相对的概念。对多个对象判别求断,谓之知性;如果判断的对象单一化,谓之感性。
从知性的角度,同一律表达的是,最原始的只能看见跟它生存相关的依存条件;排中律表达的是,同一律A=A不能保持,被复多对象B、C、D等所干扰的情形;矛盾律表达的是,A已经在排中律那里发生了动摇,需要在复多对象中识辨确定,识辨完成之后还得再度确认,识辨错误没有发生的情形。
当判断的对象进一步增多,甚至达到无穷之多的程度,我们已经无法在实体反应上面对无穷多的对象,产生推导反应和A=A的识别确认,于是我们必须把对象归类为概念,然后在概念上,而非实在对象上处理模型推演,然后再回归实物反应,这个时候理性就登场了。
也就是说,理性是把对象抽象和归类简化为概念,然后做软性推理反应,其目的仍然是对复多对象加以判断。只不过,这个时候硬态实物判断已经无从进行,必须在软态逻辑概念沙盘上运行,这叫理性。
更进一步,理性逻辑的高端状态,叫做理想逻辑。所谓理想,指的是纯粹推理之想,它纯粹在概念层面运行,而脱离了实物对象。比如,数字3,可以代表任何物体,但也不指任何东西,在实物对象上永远没有3,它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概念符号,它后面已经没有实物要素来支撑。
作为对比,当我们说杯子的时候,尽管也是概念,但其背后仍然有实物要素做支撑,也就是杯子这个概念并没有完全排除感性素材。因而,基于杯子的概念推理,仍然掺杂感性要素,并不像数字3那样,是完全纯粹的推理。
与亚里士多德的知性逻辑相仿,在理想逻辑层面,也有着类似的推理定律:
- 简一律:对应于同一律,即A系=A理;所谓A系,即达成A的一整个系列,比如哺乳动物,包含了猫、狗、虎、豹等;比如物理概念力,其动量形态可以表达为F=ma。
- 排序律:对应于排中律,即不再做排中,而是做排序,也就是把A和所有非A之间的关系理清;比如,达尔文用自然选择这一个原理,把所有生物排序为一个进化层级。于是,万物呈现为清楚的链条序列。
- 消矛盾律:对应于矛盾律,即A只为A,正在于它源自非A或导致非A,从而消除A和非A之间的断裂和矛盾;比如,达尔文谈进化,是从一个点导出另一个点,或者还原了一个点;比如脊椎爬行动物,往前可以归类为水生脊索动物,往后可以归类为两栖爬行动物。
- 追本溯源律:对应于充足理由律,即为避免多因素分析所可能带来的思维混乱,必须追本溯源到一个终极点上;追本溯源所达成的结果,实际上是对简一律的回归。
看到这里,我们就能够清楚地分辨出,人类高端理性逻辑,实际上是动物知性逻辑的顺势延展。人类的逻辑进展,是在知性逻辑、理性逻辑和理想逻辑一脉上的不断纵深和顺延发展。它的内涵,实质上是处理信息增量的差别。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类对逻辑的使用,主要有三大方式:
- 纯逻辑:比如,数学与几何学。问题在于,不知道纯逻辑与对象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比如,大量的数学模型在逻辑上成立,却找不到与外部世界的对应关系。
- 归纳法:比如,根据亚洲、欧洲、美洲与非洲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归纳出“凡天鹅皆为白色”的结论。问题在于无法穷尽所有的天鹅,因而只能证伪,不能证明。比如,澳洲就有黑色的天鹅,一经发现立即导致原先的结论崩塌。
- 演绎法:是归纳法的后续应用。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所有人都会死(大前提),亚里士多德是人(小前提),所以亚里士多德也会死(结论)。问题在于,演绎法的前提由归纳法得来的,因而只能证明,不能证伪。和归纳法刚好相反。
看到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人类使用逻辑的全部三类方法,都存在着缺陷。因而,不能因为证明使用了逻辑,且逻辑推导过程没有错误,就认为结论是真理。
实际上,先天思维格律的规定性,导致感观素材基础上的逻辑推理结果,一定是在原来感观扭曲的基础上,进一步扭曲的思想性结论。
这样的一个用思维来考察感知序列,以及思想序列的反思过程,就是认识论的展现。
哲学与科学一脉相承
科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
在当时,所谓科学,实际上是博物学或者自然哲学分科化的产物。我们把这个分科之学,简称为科学。
亚里士多德,从实体论的角度详细探讨了分科之学。他把当时的知识,分为物理学、形而上学、生物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等,总数达19门之多。所以,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科学的开端。
为什么自然哲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必然引出科学的诞生呢?
这是因为,所谓科学,本质上就是哲学思想模型的大信息量、分科处理状态。比如,我们今天讲的数学与几何学,就是由毕达哥拉斯与欧几里得这一批古希腊哲学家缔造的。
当初,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创造科学应用工具,而是为了寻求世界存在的终极原因。因而,数学与几何学,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哲学产物,是形式因追究的终极结论。到了今天,它们成为整个科学工具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再比如,原子论是当年古希腊哲人质料因追究的一个终极结论,也是纯逻辑推演的产物。到了19世纪,卢瑟福把它做成行星系模型,刻画成电子围绕原子核在空中运转的形态。直到今天,粒子物理学的前沿研究,仍然还在努力回答2500年前由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提出的问题。
罗素晚年,针对哲学和科学的一脉相承,在《哲学问题》中指出:
所谓哲学,就是对科学问题的前瞻性、非确定性讨论。
也就是说,这种提前对问题加以讨论,却不能达成精确而确定的讨论结果的状态,叫做哲学。换句话说,哲学问题,是科学问题的提前探讨,是信息量不足情况下的预讨论准备。
因此,哲学带有科学问题的前导和引领作用,构成科学后继展开的前驱角色。反过来,凡是不产生狭义哲学的地方,都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系统文化。
哲学与科学的深度融合,还体现在历史上的哲学大家,或者本身就是科学大家,或者对自然科学十分熟悉。
同时,在西方真正懂科学的人,他一定有基本的哲学思维在前面,进而导出科学的高深进展。
不仅如此,神学与哲学和科学,同样是一脉的思路。
神学与哲学的一致性,体现在对终极原因的探讨之上。古希腊哲人对于神是如何运作世界的好奇,直到导致了哲学思脉的蓬勃发展。
而区别之处体现在工具使用上,神学借助的是信仰,而哲学和科学则共同使用理性。同时,科学探讨的是具体的问题,从而与神学和哲学有所区别。
当今时代,人们之所以对哲学和科学内在一致性的体悟,不再如古人那般深刻,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对科学实用性的强调,以及实用科学教育的普及,导致人们的日常思维与哲科终极思维之间产生了显著的距离。
而只有通过历史的回溯,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这一点。
逻辑变革
古希腊哲学家高尔吉亚,是宛如先知一般的存在。他曾经提出著名的三命题:
- 第一:无物存在;
- 第二:即使有物存在,也无可认知;
- 第三:即使有所认知,也无从言表。
惊人之处在于,这三点恰好说明了西方哲学在发展历史上,所经历的三次重大转向。
第一,与古希腊时期的本体论相对应,回答诸如到底存在是什么,有没有存在之类的问题。第二,与近代古典哲学时期的认识论相对应,即使有存在,也无法认识。第三,与现代哲学的语义论转向相对应,既然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一个主观感知逻辑体系,那么这个逻辑体系的体现是以语言结构系统表达的,而语言结构系统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这就导致语言的运行会超脱逻辑的羁绊,而走向自己独立的运行状态,从而导致对逻辑体系的扰动。
这样的一个演化历程,表达出哲学越来越脱离终极本源追问的深度。从追问世界的本源,逐步飘离到追问感知的状态,并再次飘离到追问语言的状态。这个状态,导致了西方哲学走向的逐步浅薄化的总发展趋势。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要返回古希腊、重新追问存在的原因。
西方哲学的演化历史,清晰地表明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不是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主观感知模型和主观逻辑模型。因而,任何宇宙观和世界观,都是一个主观逻辑模型体系而已。人类文明,不是铺垫在客观世界之中的,而是铺垫在思想家的思想通道之中的。
在这个过程中,康德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第一次明确指出,人类所谓的知识,绝不是外物的单纯反应,是外部信息和主观给定的感知规定性(先验规定格律)组合出来的一个系统。
如果没有感知系统、思想系统、逻辑系统的调动和训练,接受的不叫知识,只叫信息。如果先验感知系统,或者先验逻辑系统是有漏洞的,用它们来整理信息,就必然会带来知识的漏洞。因而,知识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信息的先验整理模型。
我们来看,爱因斯坦就宇宙运行,所给出的例子:
宇宙就像一个打不开外壳的钟表,永远不知道实际是怎样运行的。
我们一切做科学的人,只不过站在表外,不断地模拟宇宙之表运行的方式。
在这个例子中,宇宙的运行提供了信息的来源,而人类的知识,是借助先验的逻辑模型,对宇宙信息整顿的结果。
回溯宇宙论的发展历史,我们大概经历了五次重大的逻辑变革:
- 盖天说:天圆地方,远古时期人类基于直观提出的原始模型;
- 地心说:托勒密提出,符合人类的日常经验;
- 日心说:哥白尼提出,颠覆了人类的日常经验;
- 机械论:牛顿提出,由万有引力和三大定律组成,绝对时空观;
- 相对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时空观念,颠覆了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
由这个例子,我们得出科学绝不是客观真理。宇宙之表是打不开外壳的,我们看着宇宙运行,只不过做了一个逻辑模型,然后去揭示它运行的可能方式。
既然知识就是逻辑模型,那每一次的认知升级,实际上就表述为逻辑模型的更迭,即所谓的逻辑变革。
而逻辑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新的宇宙信息的发现,从而对现有逻辑模型构成挑战。这就使得哲学家与科学家,需要在信息增量的基础上,构建出更具包容性的新的逻辑模型,来加以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哲科学者所提出的逻辑系统,需要和客观本真达成融洽。我们将在下一节,做进一步阐发。
真理与正确
我们知道,西方主流的知识观念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成立的前提,是默认了我们能够获得真知。由于我们的知识,受到主观规定的约束和扭曲,而不能得到真知,因此认为不可知。
然而,“知”如果不是为求真而设定的呢?
在这一点上,王东岳先生提出了重大的创见:
知不是为求真设定,而是为求存设定的。
在递弱代偿理论中,万物的演化进程,就是感应属性的增益进程。比如,在基本粒子层面,负电荷的电子,与正电荷的质子之间相互感应。分子层面,酸根与碱基相互感应。在细胞层面,细胞膜的跨膜电位差异所引发的生物电冲动,发展出神经细胞的感知。从基本粒子、分子、无机物到有机物的演化过程,感应属性越发丰富。
在感应的过程中,实际上并不能发生真感。比如,电子与质子感应之后,变成了电中性。酸根与碱基感应之后,变成了盐。人类的视觉,将可见光的能量感应成明度,将可见光的波长感应成颜色。人类的听觉,将机械波的振动感应成声音。人类的嗅觉和味觉,将特定分子感应成为香臭等气味与酸甜等味道。
换句话说,在感应的一瞬间,主观的感知属性,一定是对客体可感对应属性的耦合扭曲。而且,感应反应,并不求全知。比如,电子除了感应正电荷,用不着知道质子的质量与形状等其他属性要素。
有机体的演化历程,从5亿年前扁形动物出现视觉开始,神经网、神经节、下中枢、上中枢、高级皮层依次出现,构成从感应开始,到扁形动物的感性,到脊椎动物的中枢性知性,到人类额叶前皮层的理性。
这就使得,从最基本点上注定了人类的感知本身,不是求真,而是求得有效依存结构反应。
由此,求真变成了妄谈,于是不可知论的问题,就化解掉了。
在递弱代偿原理中,感应属性的增益,本质上表达为存在度下降的代偿。这就意味着,知的程度受限于在的程度,能知是能在状态的属性表达。然后,能知状态和能知规定性,决定了所知形态和所知内涵。也就是说,
我们的知识,不是一个随意进取量,而是一个自然规定量。
不仅如此,人类提出的理性模型,是一个不断变构的不稳定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在感知属性代偿层面上,表达为越底层越稳定、越高层越动荡的特征。
比如,粒子和分子层面的感应,不受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影响。感性层面的视觉色彩,不受知性和理性的影响,即使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在进化到猴子之前就是如此,也不会改变人类对色彩的感知。进入知性,比如在一片绿树叶中寻找一个青苹果的时候,判断的过程就表现为一个非常动荡的状态。
到了理性状态,当我们探讨为什么植物会发生、为什么植物会进化的时候,就几乎没有稳定性可言。古代我们说这是神的缔造,中世纪西方提出活素说,接着被植物学家做分类,此后被达尔文说成进化论的产物,再后来被孟德尔说成是遗传基因的规定。也就是在理性模型上,呈现为不断变构的不稳定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底层感知,比如激情,它实际上是知性的一种表达。它左右着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我们的理性左右着知性。
因而,康德总结道:
纯粹理性的高度发扬,会带出二律背反的不恰当绝对理念。
理性,只不过是激情的奴仆而已。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新的问题:不真的感知,为什么会有效?
先来看一个概念:广义逻辑自洽,就是从理性、知性、感性各层面上,在逻辑内部结构上,不发生冲突,这就是问题得到确认的状态。
反之,当信息量进一步增大,原有的广义逻辑不能维系自洽状态而发生失恰,就称为广义逻辑失恰。一旦思维模型发生广义逻辑失恰,就必然带来逻辑变革。
而广义逻辑自洽,是一个理论达成当时稳定正确被接受的基本条件。当新的信息增量,导致原有理论模型发生失恰的时候,原有的理论模型立即发生破溃。
如果说,广义逻辑自洽说明了模型为何有效,再进一步,何为正确,或者说,何为恰当?
这包括两个方面:
- 他恰:即对不能否证的其他学说,不能与之发生矛盾。比如,相对论的出现,并不能否证牛顿学说在宏观领域的匹配和正确。
- 续恰:即对新出现的信息增量,原有的逻辑模型要能够容纳。比如,牛顿学说成功了解释了宏观领域的力学现象,却无法处理十九世纪以后出现的微观世界运动,导致理论破溃。
所以,理论的正确,即非真理论模型的适当,表现为符合逻辑三恰,即在理论内涵上自洽、在理论外延上他恰、在现实层面上续恰。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正确,不是求真,只不过是生存形式的匹配;正确和适当,只不过是生存形式的恰当代偿增量的满足。这就是感知的生存匹配维护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做个总结:
宇宙万物的发展过程,就是信息增量不断产生的过程。
新的信息增量,通过挑战原有思想模型的广义逻辑自洽,而带来逻辑变革。
由此产生新的思想模型,涵盖新的信息增量,达成新的广义逻辑自洽。
正是在广义逻辑自洽和失恰的不断运行中,在逻辑变革随着自然信息量的增大而发生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知识增益和知识翻新的含义。
后记:哲学的意义一个多月前,一位师兄得知我正在学习西哲,给出了他的看法:
哲学是过时的东西,今天已经是科学的时代。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也成为这段后记的缘起。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洋务运动,祈盼“师夷长技以制夷”,因而学习的重点放在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侧重于西方科技的具体应用。
1916年的新文化运动,胡适为中国引入西方哲学,由于其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因而引入的是美国本土产生的实用主义哲学。这一脉思路,跟中国自古“学而致用”的思想,十分接近。然而,却距离西方真正的哲学深层,相去甚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深究。
时至今日,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各级教育已经全面科学化,甚至国策也叫科学发展观。然而,就我的个人经历来说,却全然不知:
科学的基础是哲学,科学是哲学思脉的分科化、大信息量延展模型。
王东岳先生认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哲学是什么,就从根本上不能理解科学是什么。
今天对科学的态度,已经接近一种信仰。如果说某事是科学的,基本上大家就不再深究。我们认为科学就是客观规律,就是真理,可是什么叫客观规律,什么叫真理,什么叫感知,什么叫知识,我们并没有做过充分的探讨。
由于科学的底蕴,它的思脉运行,不在科学应用层面上流淌,这就导致如果我们不对西方哲学思脉有深刻的钻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科学是什么,甚至会对科学产生重大误解。
甚至可以说,对科学基层的思脉缺乏必要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能力。
现代文明,也叫做工商业文明,其对应的基本文化和思维方式,叫做哲科思维。今天的中国,已经全面的科学化,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主动加入了工商业文明的行列。
所以,这一轮的东方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学习,于我来说,是一次系统的补课。
因而,我以王东岳先生的《西方哲学基础综述》作为这个小系列的收官依托,以表达对先生的景仰与感激之情。
最后,用先生的几句话,来为这个小系列落下帷幕:
中国传统文化早已衰落,却是下一期新文化再造的重要参考系统;
西方哲科文化并不代表未来,却是下一期新文化形成的持续通道。
而在新一期文化的再造之中,哲学依然会扮演引领与先导的角色。
我们,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