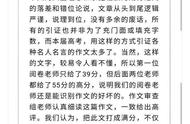校园迎接一届又一届学生入校,又在每一个夏天目送他们远去。老师还在那里,用自己的诚意与心血,尽可能影响到更多年轻人。
---------------
珍贵四年,我们和他都不是“课抛型”
凯莉
大一那年春天,一个平平无奇的午后,我和室友气喘吁吁跑进公选课教室。一路狂奔早已精疲力尽的我,整个人趴到桌上。选这节课的学生不少,大家的心态大同小异:老师要“不麻烦”,作业少,考试容易过。
一位格外年轻、清瘦的男教师,正站在讲台上摆弄一摞书。看样子是一位刚执教没几年的新手。他沉默许久才对我们说:“我这门课可能和你们其他课不太一样,学习没有压力,不会让任何人挂科……”
底下的我们发出了一阵轻微的欢呼,几个趴着快睡过去的学生也都好奇地抬起头。老师的目光扫过来:“甚至如果你们觉得比较累,想去图书馆看书,都可以不来上课,只要自己真的有所收获,不浪费一下午的时间就好。”
呀,这老师挺有意思!我顿时来了精神,在小说和电影里,通常这么说话的都是神人,“人狠话少”,非同凡响。我好奇地想看看这样“佛系”的老师,究竟会怎样教书。
这是一门历史类选修课,老师的讲法和想象中格外不同。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也会提前“做功课”。课下,他认真了解了所有选这门课学生的专业构成,充分结合我们的学科属性,展开教学内容。
如此一来,我们这些跨专业选课的学生,听课时并不会感到与历史系“有壁”,甚至经常有意外收获:喔,原来历史学和我们专业也有这么多密切的联接!
老师还会带很多推荐书籍到课堂来,供我们课后借阅。一谈起好书,他就像一座移动的“人形图书馆”,滔滔不绝地谈论每本书的推荐理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宏大精神世界。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门公选课的考试,我们完全不用专门背诵复习。那张试卷过于与众不同,考察我们的问题,是让我们谈谈学习这门课的体会与收获。当场有同学惊呼:“老师,您是不是太过善良了……”
看着我们写完姓名学号,老师让我们停笔,真诚地分享他授课的感想以及对我们的期许。同学感慨,这位老师真是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
在大学的初始年级,这样一位选修课老师用他深厚的积累告诉我们:大学不该是凑学分和混日子。我们在课堂里的每一分钟,都应该非常喜悦、疯狂地吸收精神养分,保有那些青涩又十分可爱的“理想主义”。
而后来的大学生活表明,这位老师对我的影响,绝不仅限于这一学期,他终究不是一个“课抛型”老师。
学期结束后,我们班两三个一起选课的同学,因为感到受益颇多,便和下一届学弟学妹强烈“安利”这门课:“大胆选修!你若觉得后悔,算我输!”
同时,我们似乎早已习惯了有问题还要向老师请教的状态。即使不再上他的课,我们也会“组团”带着学习和读书的问题去办公室请教他,甚至有了职业规划、生活选择等“人生课题”也会去咨询他。由于拜访的频率过高,与他同办公室的老师都深感好奇:“这几个孩子确定不是咱们历史系的吗?学习热情好高啊!”
久而久之,我们也开始调侃自己是老师的“编外门生”。有时候在学校举办的人文沙龙上,作为主讲人的老师,一眼瞥见底下的我们,还会微笑着和大家特别介绍:“她们选修过我一学期的公选课,现在基本和我们学院的学生一样。”
大三的某一天,有外校师生来人文学院和老师交流,老师特意打电话让我们一起去喝咖啡,聊聊天。当时外校同学感叹了一句:“这么多学生对非本专业的学科有如此深厚的兴趣,说明你们学校的教学风气很特别,课堂是有魅力的,学生不是得过且过。”
交流结束后,走在校园的河边,我问老师,为什么会让我们一起参与交流?老师说,他认为大学生就应该这样,拥有“丰富的精神底色”,对这个世界抱有强烈的困惑、好奇与热情。
临近毕业,在校报做学生记者的师妹,请我帮忙联系那位老师做人物专访。校报刊出时,我忽然想到,可以送一份给老师留作纪念。
那天恰逢公选课的考试日。我去教学楼找老师,走到那间熟悉的教室,又听到老师与当年一样,发完试卷后对着所有学生侃侃而谈……这样的场景和声音恍若昨日重现。校园迎接着一届又一届学生入校,又在每一个夏天目送大家远去。老师还在那里,用自己的诚意与心血,尽可能影响到更多年轻人。
老师出来,我送上校报。老师笑了:“时间好快,你们也要毕业了。”
我回答是啊,没想到一门课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持久,居然贯穿了整个大学。
那一刻我蓦然明白,如果没有遇到这位良师益友,如果我只是“课抛式”学习,绝对不会拥有这样珍贵的大学四年。我对这所校园的怀念,是对那片精神底色极其丰富的人文土地的无限热爱,其中有一份眷恋,专属于通过这位老师而感知到的“理想主义”。
---------------
线姐饭圈在“抗线”中随她前行
焦俏
线粒体是呼吸作用的场所,呼吸作用分解有机物,释放能量。在线姐的“折磨”下,我们一边痛苦无比,一边能量满满,像呼吸作用一样,永不停息。
线老师一开始就特立独行。
初一开学前一个月,学校布置了每天的练习。自行打印完成,下午4点发当天答案,自判自改,5点之前线上提交。一个小时改五科的作业,略显紧迫,其他老师都给我们放宽到了六七点,唯独她没有。
那段时间我正在老师的琴房里备战钢琴九级,会条件反射地距ddl还有10分钟时,从钢琴上跳起来,烦躁而怨恨地改生物作业。改完也得不到她的赞许,线老师会在评论区发几条近一分钟的语音,说出一堆我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
开学后生物暑期题目重测,我意外拿了满分,不过这依然抵消不了对线老师及生物的怨。她上的课也像她的“亿”分钟语音,事无巨细,极为周全。
开学一个月后,班主任让我和几位同学在自习课去另外的班,学习课外知识。不出意外,线老师又来挡路了。她的要求和暑假一样,5点前在学校完成生物作业。我们5点前是回不来的,所以必须在大课间写完。我在其他同学的谈笑中赶作业,窝着一肚子火跑出教室。这时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对我说了一句:“我爱线姐。”
我有点吃惊,这个学生好直接。两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展开:一,黑到深处自然粉;二,她真的喜欢线老师。
出于谨慎我没说什么,此后越来越长的时间表明,反转来了,线姐的粉丝疯涨,直接变成大V。
我们学《细胞的生活》时,同样姓线的“线粒体”成了我们的粉丝名。班里同学一口一个“我爱线姐,我爱生物”,线姐的名言口口相传,像“只字不漏阅读”“思维完整”“重视知识间的联系”,乃至“死亡会阻止你愚蠢的基因向后代传递”……
线姐教的另一个班,也就是四班的一个同学,把生物学习群的名字改成了“线姐全球后援会”(但这个学生也因此差点被线姐踢出去),而在我们班,同学把“线姐语录”排版作为朋友圈封面,全班每个人的微信“拍一拍”都与线姐有关……
没有人知道线姐是怎么毫无预兆地走红的,也没有人知道沉寂了一个多月的同学们如何统一为线姐粉丝的。这里有唯粉、路转粉,可能还有黑转粉,线姐的确成了整个学期线老师的代名词。我们也在讨论中尝试以另一个视角看待老师,放下以前的成见,放下少年的叛逆……
线姐很负责任,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我们班有句名言,“我们不配拥有生物课前和课后的课间”。
课间,线姐随时进来,有时还在上节没下课的时候在后门蹲点。转头看见门口的一张意义不明的笑脸,后排的同学心脏一定非常强大。线姐拖堂,没有同学反抗,一是不敢,二是她拖堂讲的东西都很值得我们放弃十分钟的休息。但其他老师就不一定这么看了,一次线姐继续拖堂,地理老师站在门口,笑眯眯地来了一句:“线老师,这节是我的课吧,你怎么还不走呀?”
第一次班会,她就告诉我们,所有人的目标都是生物中考满分。我们要记录完成时间来锻炼时间把控,做完先预测自己得多少分,再和实际得分作对比。“什么时候这两个分一样了,就是你进步的开始,因为你对自己的水平有了精准的认识。”预习要做笔记,改错要还原到书上对应知识点、分析错因,线姐会一个一个看,有时候还会贴在本班,或和四班交换,让我们互相学习。
她教育我们要珍惜和感恩:一道题给你训练的机会只有一次,不认真完成就是在浪费题目。讲*和分娩的时候,她让我们班把书包装满,背在前面逛学校,让四班这样背着上了三节生物课。我们班全员“社死”,四班同学则说这样很不方便,字都写不好。那天刚好是妇女节,她只留了一项作业:对妈妈说一句我爱你。
但线姐这样的大V,也会与学校规则有小摩擦。我们似乎把生物永远放在第一位,以至于超越了学校要求。拜线姐所赐,我们班的生物成绩次次年级第一。班主任也常半开玩笑地说:“不如让线老师当你们的班主任好了,感觉生物都快成主科了。”
当然也会有黑粉捣乱。一个小长假,线姐的作业量达到了年级统一作业的好几倍,于是她被班里几个黑粉举报了。在年级和班主任的协调下,我们成功减负,全班欢呼。我们边“抗线”边随她前行,冲向生物这门学科的奥妙深处。
小海马与我们只有一身校服的距离
薛凯文
相比于严厉,他可爱的时候更多。可是,他为什么把我拉黑了呢?
红圈圈里一个感叹号!什么情况,小海马把我拉黑了?
我试着又发了一条微信,没错,“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
小海马是马老师,教我们地理。作为班主任,他可一点都不“板正”。头发很有喜感地烫了几个小卷,衣服上印着日本漫画“五条悟”,手机壳上贴着“炭治郎”,办公桌上摆着许多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动漫手办,反正就是很随意,很不“班主任”。
地理课上,他也这样。我们从来不用一动不动地坐好,不举手就可以提问题。有人举着地球仪在班里玩,他也不会生气。讲到有趣的地方,我们还接过话茬开玩笑,40分钟过得很欢乐。
前段时间,他半夜定闹钟爬起来看欧洲杯,第二天还会点评一番。不过,那表情分明就带着炫耀——谁让你们看不了呢?他的朋友圈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喜欢的歌手出新歌了,要发;为玩游戏买了PS5,要发;做了奇奇怪怪的测试,要发……时间一长,我们都发现,他跟我们之间就是一身校服的距离,各种话题交流无障碍。
在学校一年一度的合唱比赛来临之际,他却突然认真了起来。
他把我们在学校每一分每一秒的空闲时间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排练的时候,他不断地向我们强调音调、队形、动作,甚至连表情都要仔细观察。他绝不允许我们排练时做任何其他事情。聊天、写作业、睡觉、传纸条都会惹得他大发雷霆,有一次还直接给一个同学的家长打了电话,把我们吓得不轻。
比赛前夕,他突发奇想,要跟我们一起参赛。没听说哪个老师会参加合唱,我们都穿校服,他站在里面多突兀啊!我们七嘴八舌议论了很久,小海马最后宣布了他的解决办法:我也穿校服!
天不遂人愿。他借了一圈校服,结果都比他那胖嘟嘟的身子小一圈!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他,他跟我们说:“以后,我要跟你们一起上体育课,一起跑步!”经过他不懈地寻找,最后在学校的失物招领处找到了一件勉强能穿的上衣。于是,合唱比赛上,大家都看见了一个穿着小号校服的“假学生”放声高歌。
直到今天,我们想起那滑稽的一幕,还是忍俊不禁。当然,我们也没在体育课上见过说要跟我们一起跑步的小海马。
没错,相比于严厉,他可爱的时候更多。可是,他为什么把我拉黑了呢?
我仔细想了想,最近一切如常啊。去他办公桌上拿零食?也不是第一次了,很多同学饿了都会想到他的办公桌。是因为午休的时候偷偷打篮球吗?可我们已经被他揪去办公室站成一排,挨过骂了……
第二天课间操的时候,我颠颠儿地追着小海马,想知道被拉黑的原因,“我怎么跟您交流,怎么跟您请教问题啊?”
“你可以在学校当面跟我交流。”小海马看我一眼,不急不慢地说道,“你瞧瞧,你问我的都是什么问题?耳机推荐什么牌子、降噪效果好不好,游戏主机配什么显卡、PS5怎么样……我又不是导购!”
突然间,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可爱了,哼!
---------------
“O”老师 富氧能量站日日相伴
楼杭之
这位当天就吃了半锅豆腐的“罪魁祸首”一边吃一边说:“作为你们的化学老师以及一个吃货,我感到非常幸福……”
作为一名学生,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老师——有的严肃古板,有的温柔和蔼,有的幽默风趣。然而我的化学老师却不能被任何一个四字词语概括。
认识她是在八年级开学的第一天。化学这门课,对大部分同学来讲还十分陌生,教室里弥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紧张气氛。她很年轻,身材不高,戴着眼镜,一头及肩短发染了浅棕色,哪里都算不上特别,只是镜片之后的眼睛闪烁着古灵精怪的光芒。
全体起立道过老师好之后,她就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字母“O”。同学十分不解,以为自己要上一节英语课;但熟知元素周期表的几位同学马上猜到了老师的用意:字母“O”是氧元素的符号,也是老师的姓氏“杨”的谐音。果然,她就是这么解释的,并且还加上了一句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我是化学老师,自然要用化学的方法来自我介绍。”
而后我有幸成为化学课代表,与杨老师的接触也随之增多。一天,我们几个提前预习过酸碱盐知识的同学被她神秘地叫到办公室,她拿出两个小纸盒递给我们:“你们现在应该能打这副牌了,之前我都没办法跟你们玩。”
我心存疑虑,打开包装,里面是一张张写着不同化学物质的卡片,需要按照正确的化学方程式把反应物打出去,或者为别人打出的反应物接上生成物……“试着玩两局吧。玩了这个,肯定能把酸碱盐的知识记得特别牢。”杨老师一边说着,一边已经把牌分完了,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同学小王率先打出氧气和磷两张牌:“磷在氧气中燃烧。”他挠了挠头,“酸碱盐的那些反应我还不熟,只能先出这个了。”
一旁的小李嘿嘿笑了笑,将“五氧化二磷”的卡牌放在小王打出的两张牌旁边,“这是生成物哦。”
杨老师笑眯眯地点了点头:“不错呀!又轮到小李出牌了。”
如此“交锋”了数十个回合。在“战局”稍有缓和的时候,她*句嘴:“这不都学得挺快嘛,肯定也能顺便把知识记得很牢。”
众人回忆了一下,果然,自学时背得十分吃力的几个方程式现在已经能脱口而出了,顺带着把那些离子化合物的溶解性也记下了大半。
看我们已经尽兴,杨老师开始整理桌上散落的卡牌,狡黠地眨眨眼:“我早就说了吧,化学很有意思的——有空再来跟我打牌。”
接下来她可惨了,午休时间或周五放学后,我们几个不约而同都会去办公室堵截。以至于我妈每到周四都会问一句:“明天又要去*扰化学老师吗?”
上学期,学校研学活动的行前讲座上,其他老师和学生都在忙着询问即将要拜访的名胜古迹和博物馆信息,她却在一片喧哗中大大方方地举手提问:“咱们要在柳沟村体验自制豆腐,是用卤水还是用石膏点卤啊?”
主讲者愣了愣,笑着告诉她:“这次是用那边特制的酸浆来点卤。”
“好的谢谢。”她坐下来,给旁边的我们使了个眼色,“作为我的组员,你们是不是有义务复刻一下这个酸浆豆腐……”
现在想到此事,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爆笑。杨老师也在此行充分暴露了她对美食的热爱。当所有人都体验过磨豆浆、参观点卤以及吃豆花之后,她仍然没有满足——在我和小赵打包好两瓶酸浆的时候,只见她竟然多拿了一盒豆腐!我俩哑然失笑:“您还强抢人家的劳动成果!”我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个难忘的“杨老师吃豆腐”时刻。
回京之后,在杨老师指导下,我们完成了名为《凝固剂种类与浓度对豆腐品质的影响》的研学论文,也兑现了对她的承诺——小赵同学在自己家里复刻了一大锅酸浆豆腐,带到学校,引得杨老师连连称赞。这位当天就吃了半锅的“罪魁祸首”一边吃一边说:“作为你们的化学老师以及一个吃货,我感到非常幸福……”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例如她私下和物理老师一起去买盲盒,想抽什么就能抽中什么,这份“欧气”令我们羡慕了许久;又如她在元旦联欢会上和另一位女老师当众靠在一起,大气地表示我们可以随便“嗑cp”;再如化学办公室里随处可见的零食,或许与她在柳沟村吃豆腐的表现一般无二……
这位只能被元素符号概括的“O”老师,真正人如其名,点燃兴趣,元气满满,是我们日日相伴,课前课后都离不开的那个富氧能量站。
---------------
量化指标下,他是一股“泥石流”
王翼鹏
老闫尽管一大把年纪,身上却依然带着一股书生气,对待有些人和事桀骜不驯,对待学生却温和诚恳。
高二那年,文理分科,我来到一个数学老师当班主任的班级。老师姓闫,年纪不小,已有些谢顶了,因而私下被大家称之为“老闫头”。
他操着一口带浓重鲁西口音的普通话,慢吞吞地,一句一顿,每次讲到笛卡尔、欧拉等西方数学先贤的名字时,他的普通话都会大翻车。在我们这所竞争压力较小,以“国际视野”闻名的省城中学里,他的气质有些格格不入。
尽管老闫是数学老师,但坊间却传闻他是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学《孔雀东南飞》的日子里,语文老师上课抽背,连抽了七八个同学都背不下来,盛怒之下把全班同学都罚到教室墙外站一排,背过了才许进教室。时值夏天,走廊里热气腾腾,空调房看得见摸不着,一片怨声载道。这时老闫从门口过,同学们便七嘴八舌地向他抱怨一通。老闫乐了:“这有什么难的!你们谁给我起个头。”于是,他一口气从第一句背到最后一句,留下鸦雀无声的人群扬长而去。
每周的班会课,学校都会按照统一的主题做好幻灯片发到各班,但老闫头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一次班会课件上有“大象”字样,他看了一眼,随口说了一句:“大象,大白象。”台下响起一阵笑声,他便作严肃状:“笑什么!你们知道大白象是谁的外号吗?”看到我们一脸迷茫的表情,他便得意地说:“大白象是鲁迅的外号。许广平在写给鲁迅的信里,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他在开班会这件事上颇有天赋,尽管天马行空,时常给人以不着调之感,但却胜在事例丰富,大家听故事简直比听数学课还要专注。以至于后来,大家都不怎么购买作文书,班会课上讲的素材足够撑起大多数议论文写作。
高三运动会那天,年级主任特地在前一晚来到各个班里宣讲纪律:“可以吃,可以玩,可以聊天,就是不许写作业。”听到这儿,我们都偷偷看了一眼老闫。此时需要介绍一下我的学校。我们学校是在教改中探索的实验中学,在追求升学率的大环境下,办学风格如同一股清流,历来以“素质教育”闻名,不那么看重学习成绩。对各班来说,“量化指标”才是最重要的——体育、卫生、搞活动、纪律这些事决定着一个班级的最高荣誉。可是,老闫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说过,教育理念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要不偏废就好。“量化指标”虽然重要,但对你们来说,毕竟高三了,成绩决定着未来前途,作为学生,学习是你们的本质要务……所以,年级主任刚走出教室,他就走上讲台,小声说:“参加完项目的同学,还是适当写点作业吧,别太过分就行……”一边说,一边斜眼去瞟年级主任已经远去的背影,忽然眉头一舒:“挨批的话我来担着!”
在“量化指标”主宰一切校园里,老闫实在称得上是一股“泥石流”,他有自己的一套价值准则与教育理念:“反正我早就评上高级职称了!”这样的老师,在学生、同事与家长中广受好评,他带过的连续四届学生,重本录取率都是年级最高的。
不同于年轻班主任们桌上摆着的教育类、学科类书籍,他的办公桌上,除了几本教参外,更多是文史类书籍。他也鼓励我们多读,虽说是理科班,但《全球通史》《人类简史》,白岩松、易中天等当代文化人物回忆录与评论集,余华、金庸作品和其他流行小说,都在班里长期传阅。我至今都觉得,高二是我人生中读书最多的时候,也是第一次领略人文社科领域的魅力。而对于没上课间操却跑去打球、翘自习泡图书室等,他也一概不太管,在集体与纪律、分数与能力的博弈中,老闫按照自己的理念,打造出了一片张扬个性,颇有情怀的自由天地。
老闫并不是个善于与学生打交道,和学生称兄道弟的老师,甚至可以说是不善言辞的。尽管一大把年纪,身上却依然带着一股书生气,对待有些人和事桀骜不驯,对待学生却温和诚恳。作为老师,我愿意用他最喜欢的鲁迅的诗句来描述他:俯首甘为孺子牛。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09月10日 06 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