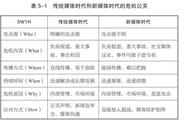父亲生于兵荒马乱的1930年,是背生的。爷爷不到四十岁就因病去世了,奶奶又改了嫁,于是父亲不到一岁便与年近七旬的祖母相依为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从小就跟着二爷爷学了一手的好农活,10多岁便耕、耩、锄、割无一不精,15岁那年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
那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司令厉文礼的部队割据安丘西南乡。司令部设在现在的辉渠镇夏坡村,驻扎我们土山村的是高部一旅一团。后来厉文礼在城顶山战役增援51军时被日军俘获投降,从那时起他的部队就被老百姓骂作“汉奸、伪军”。他们不但横征暴敛,无恶不作,还把我们村里成材的树木全部砍走,在村西北角强占了村民的数百亩良田叉起了高高的木寨,建起了碉堡和吊桥,并在木寨周围挖了十多米宽的濠沟,当地人称作“围子。

父亲在中共山东省委派来的地下党员徐连喜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经常利用夜幕掩护走村串镇张贴“誓死不当亡国奴,团结起来打东洋”、“打倒汉奸分田地,群众翻身做主人”等宣传标语,并多次利用卖粽子、香烟等机会到圈子里侦查地形。
“一九四五年哪,八路军打汉奸。一团围夏坡,二团攻土山……”一一这是父亲经常唱给我听的歌谣。1945年初秋,谷子正黄时,漫山的黄厥与遍野的谷穗连成金黄的一片,一望无垠。身着黄色军装的八路军队伍从沂蒙山区浩浩荡荡开了过来。围子里的伪军惊慌失措,胡乱地打枪、开炮,
而八路军依然保持着整齐的队形前进。“大炮打不动,便知老八纵”一一来的正是华东*军的主力第八纵队!
围子东门就在我家老屋对面,距离不到100米。住在我们家的八纵二团一营的战士们便在我家西面的土墙上挖了一个大洞,架上了一挺需要加水的重机枪。喝着喷香的小米粥,吃过祖母亲手擀的白面双饼,战士们就在我家院子里休息。也许是年龄相近的缘故吧,一位刚满16岁的战士小李和我父亲谈得最投机,他说家乡在沂蒙山深处,那里也种好多好多金灿灿的谷子,等打完了仗带父亲到老高老高的蒙山上去玩呢。他还偷偷地告诉父亲他正在预备考验期,不久就能正式入党了!看着父亲羡慕不已的样子,他便摘下挂在腰间的用一根红线串起的弹壳送给父亲。
第二天拂晓,战斗打响。突然一颗炮弹呼啸而来,给重机枪续子弹的小李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碉堡上的伪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实施火力压制。几次冲锋下来,许多年轻的八路军战士倒在壕沟里。我父亲急地不顾一切冲上前去,给负伤的机枪手续起了子弹………经过近4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围子终于被打开了,伪军被全歼。村民们争先恐后地冲进围子去抢粮抢物,而父亲却只是默默也将脚下的那一大堆弹壳收起,足足有半麻袋。

后来闲暇的日子里,父亲用一根根红线把一枚枚弹壳拴成一串串,挂在屋门两边的土墙上,恰似一个个金黄的谷穗。每当风大的时候,这些凝结着斑班血迹的金黄的“谷穗”便会叮当响起,就象一首时而高亢时而深沉的乐章,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提醒着什么……而每每此时父亲总是深情地凝望着这些金黄的谷穗,眼里常常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2021、2、26夜郑冠清写于山居斋
作者简介:郑冠清,笔名鸿斌,山东安丘人,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1988年至今已在《中国建材报》、《齐鲁晚报》、《黄河诗报》、《诗选刊》、《农家生活》、《潍坊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300余篇,有诗文多次获奖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