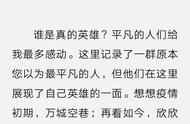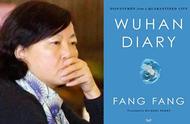【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下,每个人的悲欢离合,无奈与抗争,都是一份独特的命运体验。
《@武汉——抗疫故事接龙》是澎湃新闻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联合推出的特别策划,以新闻人物报道接龙的方式,记录正在武汉与疫情搏斗的人们,呈现出相互联系的他们在疫情之中的经历、心情与感悟,以及面对生命考验的自我重建。

程翔于2月17日在家拍摄的绿地中心,这是武汉一座超高层地标建筑物,他每天拍一张照片作为日记封面,称之为“武汉塔”。这是封城第26天。 本文图均为 程翔 图
“你们在畅饮/我也举起了酒杯/可我举起的全是泪水。”大年三十晚上,读着朋友写的诗《我从未为武汉哭过》,程翔(化名)站在阳台边,阴沉沉的天空笼罩着空荡荡的大街,他心里忽然生起悲壮:“经此一遭,我和这个城市,也算是患难与共了吧?”他把这首诗转发了两遍。彼时是武汉封城的第二天,也是他写封城日记的第二天。
76天,20万字,累计近45万阅读量。从武汉封城到解封的这段时间里,程翔每天坚持做个体视角的记录与叙事,称自己是“平民视角真实记录”。他曾经是记者,在《湖北日报》干过十一年,如今在大学教书。他保持了作为新闻媒体人的敏感度和工作习惯,每天阅读新闻、找选题、撰文,再发表在自己的公众号“程翔星期五”上。
“封城日记”里,他记录了疫情期间许多生活横截面的碎片。他写下与儿子可乐的居家生活趣事,也叙述了家庭的至暗时刻。他作为旁观者记录了朋友的病情与康复、华科校友会的抗疫行动、陌生人的生离死别,也记录了自己的各种梦境、眼泪和辗转难眠的夜晚。激动难言的时刻,他甚至直接写起诗歌。
“我想记录下来,等儿子长大了,告诉他这是爸给你写的,你自己好好看一下。”程翔说。

2月24日,程翔带父亲前往省人民医院就医,父亲正在发热门诊抽血。这是封城第33天。
以下是程翔的口述:
最压抑的时刻:父亲病了
1月23日早上10点封城。其实22号晚上,一些企事业单位就已经通知不要离开武汉了。好多人对于封城根本没概念,那几天很多人都在打听这条路能不能走,往哪里走。知道消息以后,我当时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就是像非典一样,一段时间就好了,也没有想到未来会封这么久,影响这么大。
家里物资储备足够,一开始我不是很慌,后来我爸生病的时候我紧张了。他是封城前三天到武汉来的,我也让他在火车上戴了口罩。但是2月20日左右他就有点低烧,烧了三四天,到最后饭都吃不下。我们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不咳。
最严重的时候,我爸自己用头撞墙,后悔来武汉,觉得“哎呀这怎么办?”当时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冒险出去了,我就开车带他去人民医院检查。
我们先去发热门诊做CT、抽血,确认了不是新冠,再去非新冠病人的诊疗区。当时就两个医生是接待一般病人的,好多人从头天等到第二天,医生才有时间给他看。
病人把急诊室都围满了,外面也是人,躺在病床上的、坐在椅子上的、被人扶着的,还有护士,挤满了。心电图的“滴滴滴”、氧气瓶的“滋滋滋”,仪器各种各样的响声,真的没法待。后来我找朋友在另外一个医院拿了一点胃药,就回来了。我爸慢慢也好了。
现在回想其实他也没吃多少药,我怀疑他是因为自己紧张,他当时很恐惧很害怕。这在以前是很简单的事情,该什么病就怎么治,现在医院没法很快给你确诊病因,所以就觉得很无助、很无奈。
父亲生病那一段时间其实是封城期间我最压抑的时候,真的像座山一样,你知道吧?
那几天,我妻子喉咙疼,我儿子突然有点低烧,我妈也有点不舒服。当时我一个人,确实非常紧张,我背着家人在房间里哭。在武汉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生病,我真的怕生病。
我日记影响力最大的应该就是带我爸去看病那一篇——《封城第33天:请给特殊病人一条生路》。那是我用作为一个记者的笔法,写下了一个很完整的经历。阅读量有四五万。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发微信,其中有新华社、央广的媒体朋友跟我采访。社区也给我打电话,问我爸的事怎么处理,至少他们在关心这个事。

3月4日,程翔在社区做了一天的志愿者,为邻居发放团购食品。这是封城第42天。
“像把伤口重新翻开一样”
我写日记的初衷就是为了我儿子。
他还小,就七八岁。我七八岁的记忆全没了,非常模糊。但是他也在经历这个事情。我想记录下来,等他长大了,告诉他:“这是你爸给你写的,你自己好好看一下。”
以前我上班可能比较忙,跟我儿子也就是早上见个面,晚上见个面,现在一天24个小时在一起。我也一天天地看他长大,以前有的时候还打他,现在一般都不打了。我们强迫他每天写日记,他天天写的是跟我在一起,“今天跟爸爸打球”“今天跟爸爸打游戏”“今天太高兴了”,天天写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收获。
关于疫情,我没有刻意地把一些恐惧和悲伤传达给他,我觉得他应该快乐一点,没必要吓唬他。
清明节全国哀悼,我跟儿子说了,这么多人是被病毒*死的,他们都是无辜的。我们不要吵,不要跳,要默哀。
他不懂,他似懂非懂。
我印象最深刻是,老师布置了朗诵作业,我以他的口吻写了一首诗《今年,武汉没有春天》,我写的时候有一句“我哭了”,他就会说:“我没哭!你怎么写我哭了?”就跟我尽扯了。小孩子就这样纯真,是吧?我觉得多保留一点纯真,他长大后那么长的时间里,自然有够他痛苦的。
但是我自己不回避,哭了很多次。有的视频,有些人看一遍就过了,不想看了,不想哭。但是我不一样,我要再看一遍,甚至看到别人发我再看一下。我觉得我能把这东西写出来,别人体会一次的痛苦,我要体会三四次。
我看一遍,上传一遍,写一遍,回忆一遍,像把伤口重新翻开来一样。
妻子说我一天到晚把自己放到悲伤的音乐里,搞得自己很痛苦。但是要写东西,必须要在这种氛围里,陷到里面去,才能写出好东西来,就像我以前做记者时一样的。
2月2日之前我们都是懵懵懂懂的,当时觉得封城半个月、一个月就了不起了,觉得没那么严重。一开始我对钟南山为什么流泪不大理解,那个时候公布的人数不多,后来才慢慢体会到,他们见得多了,可能他眼中看到的死亡,我们没有看见。
我好多天以后才写那篇文章——《封城第十一天:钟南山的泪,我懂了》,我才能体会。一开始不能深刻理解,后来再看又不一样了。这是我情绪比较低落的阶段,直到方舱医院建立我才好一点。
其实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好多校友都在做志愿者,武汉校友会的秘书长方华,我采访过她,她每天在协调组织各种援助物资,到处跑。
我能做什么?
我在我的社会网络里扮演着很多角色,我的好友将近5000人,我有几百个群,大概分为几类:亲戚、中小学同学、华科校友、社区邻居。我的信息来自于他们,我记录的也是这些人的真实故事,所以我记录了很多华科的事情、我小区的事情、我家庭的事情,并且也是通过这些渠道传播开来。

3月18日下午,程翔带儿子可乐下楼转一圈,可乐戴上口罩和帽子,还不忘带上滑板车,早早在电梯门口等待。这是封城第56天,可乐被“关”第81天。
“一鲸落万物生”
4月7日是“封城日记”的完结篇。
写日记期间,我早上一般是八九点钟吃饭,吃完早饭我就刷一下微信,看看今天发生了些什么新闻,看一下我昨天写的稿子,有没有留言。午饭吃完我就开始准备今天的选题了,日记最重要、最难的就是找选题,下午三四点可能选题就基本上找好了。
晚饭过后我就开始写,写完就发,在各个群发,跟各个群的人互动。
我现在是重症微信依赖症,一天刷微信刷十来个小时。
现在我星期五下午上网课,教新闻采访和写作。学生都蛮喜欢我的,还给我写了篇稿子,说我是“网红直播”。我一来就“老铁们”,都没有叫学生,我上课从头到尾都发红包,一看有多少人抢,表面上是活跃气氛,其实也是在关注他们的动态。
我老家是湖北阳新的,2000年到华科读大学,六年本硕连读,然后在《湖北日报》工作了11年,自己开公司5年,去年开始在武昌首义学院教书。在武汉待了快二十年了,说实话我以前一点都不喜欢武汉,觉得自己和武汉人格格不入。这次(疫情)之后,我觉得武汉人民,我们还是有大局观的,大家还是忍住了。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韧性的城市,宽容坚韧,我觉得它什么事都能承受得过去。
昨天看了一个视频,中国首次在南海发现鲸落(注:指鲸鱼死亡后落入深海形成的生态系统),有一句话叫“一鲸落万物生”,因为鲸身体庞大,它死了以后可以养活很多小动物。我觉得跟“解封”这个情景蛮适合的。“林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鲸落也算是一种重生。
4月8日,武汉人可以出去了。
这个周末我可能要送爸妈回老家,他们在这待太久了,让他们散个心。
(指导老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师 周婷婷;澎湃新闻记者 崔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