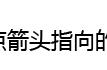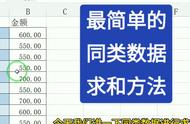李白,就其人生理想来说,是失败而不幸的,这从他那临终之作、悲怆绝望的《临路歌》中可以看出。但就其生命过程及每一个当下生存状态来说,则是生动活泼、生龙活虎、浓墨重彩。
也就是说,他的生命过程,实在是快快活活的,随心适意,肆意为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其实呢,他是在“得意”时尽欢,在不“得意”时创造“得意”也要尽欢。“人生在世不称意”时,他不也一样“对此可以酣高楼”?这个“此”,不过就是谢朓楼上极目所见之景罢了。他是“平生不下泪”的,虽然偶然“于此泣无穷”,但只是一瞬间,他永远如同一个孩子,脸上还挂着泪珠,却已在那里兴高采烈了。
对了,李白的人生,是兴高采烈的;他的诗文,亦是兴高采烈的——他永远有“高”的兴致,所以他也就有了那么“烈”的文采。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忧患”传统的文学历史中,找到李白这样一个人实在不容易,他是一个另类,但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另类啊!
他从不作严肃状,不作忧心忡忡状,不作忠臣孝子态。对仁义礼智信,他不反感,却也不挂作招牌。他嘲鲁叟,笑孔丘,他视万乘若僚友,合则共事,不合则去。他不拘检而纵逸,不小心而大意。他“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人不以为非”(苏辙《诗病五事》)。他大谈政治,却似纵横家;谈军事,却是书生倜傥之论。看他“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永王东巡歌》),令人掩口胡卢而笑,但这不是耻笑,我们是觉得他可爱。
他那么自信自大,把自己的政治热情与政治理想当成了政治才能,把自己个人发展的*当成自己的实际才干,天真也好,幼稚也罢,总之是坦荡磊落,大言不惭。像他这样毫无心机的人,为什么不让人喜爱?他的人生是艺术的人生,正如杜甫的人生是政治的人生。李白把政治、军事都弄成了诗歌艺术了,又正如杜甫把诗歌写成了政治批评,如果我们不得不向杜甫表示尊敬,那我们更不能不打心眼里喜欢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