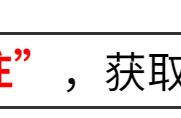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202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实际上,她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成为了法国文学界地位最为稳固的作家之一。她对于自我的书写更超出个人经验范畴,成为了法国全体公众所共享的记忆。
日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埃尔诺的三部作品《一个女孩的记忆》《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在2022上海书展思南文学读书会日前举办的活动上,诗人欧阳江河、华东师范大学法国文学教授袁筱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以及这三部作品的编辑赵伟共同分享了阅读安妮·埃尔诺的心得。

用下层法语寻回父母
《一个男人的位置》里写埃尔诺父亲讲的是大众法语,一种与普鲁斯特运用的精细的、文学的法语完全不同的粗鲁语言。欧阳江河对大众法语与文学法语的区别十分在意。“埃尔多经常用一种读过书的、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领域的语言,来纠正父亲。他们家中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哪怕是在最基础的物质层面。”埃尔诺凭借婚姻进入了资产阶级家庭,在她先生的家里,如果有一个杯子打碎了,先生的母亲会说,杯子已经破碎了,别去碰它,这背后藏着法国诗人普吕多姆的诗句。而在她自己家中,父母最日常的语言就是吵架,亲情也依靠吵架沟通,在婚后埃尔诺感到没有办法与家人对话。
“我其实有点幸灾乐祸,法语这么优美的文学的语言都有下层。”欧阳江河说。埃尔诺重写了不那么优美的法语,法语太优雅就容易变得唠叨、炫技和自恋,而埃尔诺使用的是给父母写信的记事簿语言,就像卡夫卡使用的是公文般的枯燥语言一样,当它们变成文学宝库的一部分,就会特别有力地触及现实。欧阳江河继续说,“触及真实就是天开了一道口子,一道天光照在你身上,一下子让你傻眼,痛得你都不敢叫痛!很多语言太文学,触及不到这种真实了,就像一场雨下到一半被太阳晒干了,雨点都落不下来,打湿不了你,你的眼睛里已经没水了!”

埃尔诺怀着愧疚、羞耻与背叛感,当她已变成了另一个阶级的人,唯一能找回父母的办法就是回到父母所使用的语言,只有在他们使用过的语言里,她才能唤起活生生的感觉。“这种语言是被人活过的、有呼吸的,心脏在跳动的、眼睛在湿泪的语言。我们不可能通过普鲁斯特的法语触及到这样的现实。”
在书中,安妮·埃尔诺曾提到普鲁斯特纠正女仆说错方言的事情。袁筱一说,埃尔诺用一种反讽的笔调写道,许多人迷恋风景如画的大众法语,普鲁斯特就很有乐趣。他纠正他的女仆方言不是这么说,其实女仆讲的才是真正的、正在变化中的方言,如果说方言的是他的母亲而不是女仆,他绝对不会这么做。关于安妮·埃尔诺与普鲁斯特语言的区别,赵伟补充道,埃尔诺在访谈里讲过,她不认为普鲁斯特式的形容词繁多的优雅语言适合她的写作,使用这种语言是对她父亲的再一次伤害,她父亲之前已经被她的文学教育伤害过一次了。
不断重新确认自己的位置
安妮·埃尔诺曾想成为普鲁斯特,毛尖说,她的出身相对底层,因父母辛勤工作,她才能进入中产阶级私立学校念书,可是在那里,她突然觉得自己的语言不对了。旁边的女孩子使用很多形容词,这些词在她生命里从没有出现过,她羞愧于自己的语言,也想习得她们的语言,想要成为像普鲁斯特那样拥有丰富形容词的人,但后来发现这些形容词跟她不匹配。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埃尔诺在一次电视访谈里被问道,是否有一点从自己“位置”出发对所受的教育进行报复的感觉?她坦然,有一点点。《一个男人的位置》中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埃尔诺的父亲买了二等座的票,上了一等车厢,这让她觉得非常羞耻,“这在我们生活中经常发生,如果你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出现在商务座里,你知道他搞错了位置。”袁筱一说,只是一般人容易忘记产生羞耻的细节,在这一点上,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有真实的勇气,不怕真相残酷,仍溯回源头寻找。
毛尖认为,安妮·埃尔诺写作时也在不断重新确认自己的位置。1952年6月15日,她目睹了父母的一次吵架,父亲“啪”地打了她的妈妈,耻辱感此后一直印在她的肉身上。“一个女性从出生开始,就天然站在一个被压迫的结构里,这也是很自然的,现在她看到被压迫的不仅是她本人,还有她母亲。那一天便成为她记忆的起点,那记耳光把她打在了一个位置上,改变了她一生的站位。”
埃尔诺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58年去参加夏令营。在那里,她喜欢上了一个男人,并且发生了关系,当时她很骄傲,自觉长得非常美。然而在写作时,她思考1958年时为什么把自己放在那样一个位置上。毛尖说,她反复地把生命中的事件像幻灯片一样放在公众面前,正因为对个人的经历有所反思,她的个人记忆才得以变成公众记忆。“看她的书也勾起了我自己的童年记忆,小时候,我外婆说脸盆我就知道她说的是那个洗碗盆,家里没有那么多脸盆,木桶就是洗衣妇的桶。”一个杯子就是用来喝咖啡的,一个碗就是用来吃饭的,这体现了埃尔诺语言的简洁,从书名上我们也能看出——“位置”、“女孩”和“女人”,每个词都重新爆破出生命力。

埃尔诺写下了人生中许多的羞愧时刻。有次婚后她回家看望父母,送给父亲一份郑重包好的礼物,父亲一看就愣住了,这是须后水,他一生中从来没用过的。父亲说,“这不是让我成为一个轻佻的女人吗?”女儿顿时感到羞愧,她为不能与父亲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感到愧疚,而想要挽回关系的努力又经常是错误的。“送错礼物这样的小细节带来了极大的文学震撼,这是不能追的瞬间,一追下去就看见深渊般的晕眩。”欧阳江河说,作家这时也揭示了另外一个欧洲,“一个不是有教养的、弄不懂瓦格纳和巴赫、不是须后水的欧洲,一个下层的、来自土话的、普鲁斯特想要纠正女佣人方言的欧洲,一个用错文法的、老爸签错调查表的欧洲。这是一个招魂时刻——在优雅得让人羞愧的欧洲后面,有一个土得掉渣的欧洲。”
战胜接近事实时的种种屏障
《一个女孩的记忆》看上去是写过去的记忆,但已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袁筱一说,埃尔诺以第三人称视角看到了她自己——“外省某宗教学校的好学生来自普通家庭,向往成为放荡不羁的中产知识分子。”这句话透露了很多信息,波伏瓦是典型的中产知识分子,其“放荡”和底层被迫的“放荡”不是一回事。可这个女孩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刻完成人生的蜕变,一定要找一个男人?这是她对于阶级还是性别的反叛?那时的她是真的爱吗?
并不是,可能是某种文化造成的爱情的幻想。她期待发生什么,也真的发生了,但她没有任何的愉悦感,也没有爱情的感觉。袁筱一说,埃尔诺的自我书写不是自我暴露,而是告诉人们应有勇气战胜接近事实时的种种屏障。

毛尖说在观看埃尔诺的家庭自传纪录片《超8岁月》(Les années Super-8)时发现,她仍保持着女性被摄影的相对低位,但在文本中又会对这样的女性位置进行反省。她提到,当年张爱玲进贵族女校的时候,也感到格格不入的羞耻,周围女孩光鲜亮丽,只有她穿着继母给的衣服,“但张爱玲相对地留在了那个地方,当她把自己的过往挖开来时,她用了许多的云遮雾罩的东西。你能从中感到深刻的背叛、可耻和可悲,但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埃尔诺全部敞开来,她已经不是中产阶级的埃尔诺,而是那个走错了车厢的衣衫褴褛的人,”毛尖评述道。
埃尔诺的写作分裂成了代理人的写作与自我的写作,这是写作带来的分裂也正是写作想要超越的。欧阳江河说,“埃尔诺让有点虚胖的、唠叨的、审慎的资产阶级魅力的代理人的法语变成了下层的法语,给我们指明了法语作家通过文学追认和书写下层,让她羞愧的老爸老妈认出自己,不像有些人升到高层就像割尾巴一样割掉自己的过去,这是作家的勇气与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