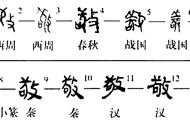三十岁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是在这一年,曾国藩确立了“学作圣人”的目标。
早期的曾国藩原则性很强,做事刚直不阿,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因此得罪了很多人。然而到了后期,曾国藩突然变得圆滑起来,做事不再一味坚持原则,以至于后人用“老奸巨猾”来形容他。
那么曾国藩是如何从刚直不阿变得“老奸巨猾”起来的呢?

曾国藩画像
一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开启了自己的京官生涯。这一年曾国藩29岁,一入京便入职翰林院,此时的曾国藩意气风发,想着如何在官场上大展拳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然而没过几年,曾国藩在诗词中就流露出一种颓丧的情绪,比如这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增形影良可咍。
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我既无法像汉代大臣汲黯那样不顾性命直言进谏,也无法像张禹那样,甘言媚世,谋取高位。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
…………
径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
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在他的家信中甚至透露出想辞官归隐的念头:
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也就是说,生在宦场中的他已经厌烦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很多,在写给家人朋友的信中,他多次表达了想辞官归隐的想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他还不到四十岁,便已经是礼部右侍郎了,搁现在已经是副部长级了。如此高的职务他为何还是如此郁郁寡欢呢?
二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道光帝画像
清朝的由盛转衰是从乾隆后期开始的,到了道光后期,腐败已经像病毒一样感染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
曾国藩迫切地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然而帝国上层多是些“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道光帝也只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修修抹抹,苟且偷安,曾国藩想凭他的一己之力将这辆驶向悬崖的马车勒住,并且改弦易辙根本是无法做到的。也正因为如此,一种巨大的无力感笼罩着他,纵使身居高位,纵使没日没夜不停地工作,做的也只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想要推动帝国机器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根本没有可能。
道光帝薨逝,咸丰帝继位,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官场氛围看似为之一振,曾国藩也被这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一年的时间内,他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他满怀期待地以为,新皇帝年轻有为,一定会采纳他的建议。然而没过多久,现实证明他是何其的天真。咸丰帝心中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宏伟蓝图,也没有推动改革的魄力,相反他心胸狭窄,气质庸弱,所谓的“求言”不过是为自己博得一个虚心纳谏的美名,对于下面官员呕心沥血想出来的改革措施,好的话他会夸奖两句,更多的是以“毋庸议”三字了之,然后便弃若敝履,扔进了废纸篓。
曾国藩很快便认清了现实,在强烈的责任感的支配下,他效仿海瑞,冒死向咸丰呈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这篇奏疏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新皇帝的三个缺点,希望这封奏疏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新皇帝幡然醒悟,从此改弦易辙。
这封奏疏和海瑞的奏疏一样,没能让皇帝幡然醒悟,却深深地伤害了皇帝的自尊心。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死罪难免,活罪难逃,在此后的日子里,虽说因为太平军咸丰帝不得不依仗曾国藩,但他从没有真正信任过曾国藩,还经常给他穿小鞋,这也是曾国藩性格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咸丰二年,曾国藩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在赴任的途中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当即结束行程回乡奔丧,结束了自己十四年的令他厌烦的京官生涯。
哪知渔阳鼙鼓动地来,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陷各省市。咸丰一道紧急命令传到曾国藩的家乡,命令他以守孝之身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保卫乡里。
曾国藩没有推辞,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兴办团练的工作中。在这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曾国藩都一一克服。而令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最大的困难竟大多数都来自他的同事。
曾国藩勇于任事,恢复了社会秩序,不但没有得到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了重重怨怼。在兴办团练的过程中,曾国藩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忽略了某些人的感受,动了某些人的奶酪,他们变着法子阻碍曾国藩的步伐,曾国藩迫不得已搬到衡阳兴办湘军。
湘军从无到有,逐渐增长成为一只拥有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在这过程中曾国藩动辄得咎,皇帝的不信任和同事的嫉妒心令他步履维艰,好在他都一一克服,练兵也初见成效,在咸丰四年的湘潭之战中,湘军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胜利。咸丰帝大喜过望,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军,还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
这封上谕并没有让曾国藩的日子好过到哪里去,兴办军务的过程中,他照样受到多方掣肘,唯一的区别是对方更加客气了,事情答应得好好的,但大多都没有兑现,这让曾国藩很是窝气。

咸丰帝画像
地方官吏不听他的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咸丰帝。咸丰虽让他帮办团练,但并没有给他实权,继位之初的奏疏事件让他如鲠在喉。他不信任曾国藩,这个人胆子太大了,没掌权的时候就敢骂自己,几年时间就组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如果再让他掌握地方实权,一旦消灭了太平军,振臂一呼反戈朝廷,到时候还有谁能阻止他?再者,即便他不反戈,作为一个汉人他拯救了满族的政权,那让满洲的八旗子弟颜面何存?
正当曾国藩万分痛苦的时候,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他以为他的机会来了。他立刻上疏请求丁忧,并不等皇帝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回到了湖南老家。
皇帝当然不会让他回去守孝三年,下旨催他快回军中。借此机会,曾国藩上了一道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说在没有实权的情况下,筹饷如何之难,地方官员如何不配合,并且告诉皇帝,如果没有总督实权的话,自己只能在籍终制”,不复出山。
话说得如此直白了,本以为能等来总督的任命,没想到咸丰跟他较上劲了。此时正值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内讧,势力大衰,咸丰以为太平军指日可平,便顺水推舟,批准了曾国藩在家守孝三年,剥夺了他的军权。
四这个消息对曾国藩无异于晴天霹雳,冷静下来,他重读老庄的著作,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行。他发现,自己之所以在官场上一再碰壁,不光是因为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也有很多的缺陷。在为人处世上,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高己卑人,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
不光是对同事,对待自己的家人他也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神气,没事总是以长辈的语气批评教育他们,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
总结下来,他发现了自己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自傲了,一味蛮干,行事过于方刚。殊不知,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几千年来慢慢形成的,要想做成大事,你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圆滑柔软,和光同尘。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
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于是当两年后太平天国势力再次强大,咸丰不得不再次启用曾国藩时,曾国藩没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
不仅如此,对待同事方面,他变得和气谦虚了,做事不再直来直去,而是和普通官员一样注意礼仪排场。他不再抱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度, 开始包容那些官场的丑陋行为。
对待皇帝,他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皇帝给他的命令,他不愿执行,便以种种理由拖延,而不是像之前那样直接拒绝,丝毫不给皇帝面子。这样,两年以后,他终于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职务。
五总的来说,后期的曾国藩虽然在一些事上不再那么讲究原则,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来都没有含糊。在晚清的封疆大吏中,曾国藩是最忠诚的,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也能做到不计自身利益,舍身许国。他是变得圆滑了,但这种圆滑是以内心的质朴刚直为基础的,和世俗的取巧圆滑本质上是不同。他的圆滑只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的一种妥协,一种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他的目的,一直都是高尚而明确的,那就是所谓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