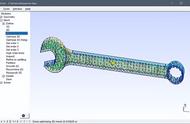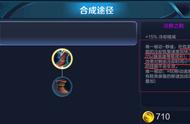孔子删诗的真相
孔子删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说孔子在编修《诗经》(当时叫《诗》)的时候,把没有被选用的绝大多数诗歌统统烧掉了。“删”实际是“烧”,是“焚诗灭迹”,不是打入冷宫弃之不用那么简单,否则,后人也就没必要为此争辩了。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最早记载了孔子选诗的原始数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自从孔子选了三百零五首诗歌以后,剩下的两千多首诗就很少见了,属于大规模集体失踪,难免让人生疑。所有史料都查不到孔子烧诗的记录,但不能证明他没有干这事。当时的书籍都是竹简,适合用来当柴烧或烤火,说他“烧诗”也是比较符合现实的描述。
历史上,围绕孔子是否“删诗”(烧诗)的争辩,有三个派别:一、反对派:孔子没有删诗,只是在当时既有的三百余首诗歌基础上编修而已,批量删诗的事情是前人(也不知道是谁)*;甚至认为司马迁的数据不可信,或怀疑史记可能被人动了手脚;二、支持派:孔子绝对删了那么多诗的,甚至也许还不止那个数;三、中间派:孔子删过诗,但应该不会删那么多的。
从司马迁《史记》记录孔子删诗算起到现在,两千多年,时有争辩。资料显示,认为孔子删诗属实的有司马迁、郑玄、陆机、魏征、欧阳修、程颢、王应麟、马端临、顾炎武、范家相、赵坦、王崧、章太炎等;为孔子辩护,否定删诗的,有孔颖达、郑樵、朱熹、吕祖谦、叶适、黄淳耀、江永、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在参与考证的现代教授与学者中,特别是清华大学教授马银琴的相关研究报告,值得一读,她认为孔子删诗的真实性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就差没有亲眼看见。
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名家牛人,参与孔子删诗言论(有记录的)的大人物并不算多,为什么呢?孔子是封建皇权推崇保护的圣人,形象不容诋毁,也不容揭露,考证出真相的也不敢说,不能说,说了也不准记录。这也是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都没有明确结果的根本原因。到了当代新社会,马克思主义才是最高权威,讲究实事求是,圣人也是人,难免有错,后人需要知道真相,终于有了像马银琴那样的教授学者,敢出来公布非常充分的考证结果:
孔子删诗的情况属实!

但奇怪的是,在百度上能搜到的“孔子删诗”,更多的是执否定态度的辩护,甚至专门的词条也是不认账,这些帖子基本上覆盖遮蔽了认定孔子删诗属实的帖子。细心的人会发现,辩护者的帖子大多是人云亦云,所引用的论点,也都是出自近代以前的人物,并没有提及当代教授与学者们的研究结果。
看看那些为孔子辩护的理由,有的甚至像是在开玩笑。不是辩护,是应付。比如,有人说:孔子在编修《诗经》之前,就说过“诗三百”这样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说明当时就已经只有三百首,孔子只是再次编修,批量“删诗”的事情是前人*。
这个问题,根本轮不到专家学者来质疑,连现代中学生都知道,当时的情景,孔子说的“三百”并非一定指实数,极可能是虚数,指“很多”。比如,在《诗经》里的《伐檀》就用了三次“三百”,都是指“很多”:“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如果你有时间,还能在春秋史料中找出那个时代更多这样的表达方式。辩护方一定知道这点文言知识,绝非水平问题,只能算是他们在搪塞应付。
有的人尽力发挥想象:司马迁的史记可能被人动了手脚,孔子当时应该没有见到三千多首诗,数目夸大了,这是“莫须有”。请问,周朝到孔子那个年代已经有五百多年历史,官方库存三千余首诗,多吗?虽然那时华夏人口不多,有文化的也少,但诗人的品性你不知道,爱好写诗的,具有善感的细胞,也就是“天赋”,有了感触就会写,有了灵感必然写,会写诗就像是一种病,难治。历史上,因为写诗获罪的人不少,流放在外还会写,思想有所收敛,但诗却写的更好了。有的人在*头之前,都还要来一首。你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诗人,关进了牛棚还会偷偷摸摸地写。
司马迁说孔子删诗的理由有“去其重”(去掉在创意上重复类似的)。重复类似的东西,浪费竹简,占用空间,妨碍查阅,影响搬运。“去其重”,是周朝礼乐官员的本职工作,根本轮不到孔子来干这事。五百多年时间,才三千余篇诗歌,如果这个数字是真的,正是礼乐官员在大量诗作中“去其重”的结果。所以,司马迁也有为孔子减罪之嫌,“三千余篇”也许已经被减过数量,在尊重事实的同时也顾及当时统治阶级的感受,正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有人讲到政治条件,说孔子当时不是周王室的礼乐官员,没有那个职权删诗。
周王室的采诗官几乎都不是自己写诗,是到民间去采集诗,这是王室体察民情的重要途径。不难想象:当时周朝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基本没有了,相互猜忌,直属周王室管辖的采诗工作必然受阻,诸侯国会把流窜乡间的采诗官当成周王室的眼线或间谍(这种事情可以有),你敢来我的地盘“采诗”,失踪了我可管不了。另一方面,朝贡的物质少了,周王室资源匮乏,裁员情况也可能涉及大小礼乐官员,他们无所事事又面临裁员,见大学问家孔夫子来借诗歌编写教材,完全可能让孔夫子与弟子们把汗牛充栋的竹简统统搬走,反正都是废品,可以不用还了(这一点很重要)。大批诗歌的生*大权就落到了孔子手里。那个年代,竹简书卷不容易拷贝复制,借书都是费力气的,这也是容易成为孤本被灭迹的客观条件。
更有人为了帮孔子避删诗之罪,居然放弃了孔子编诗的功劳,说诗经里有“淫诗”,绝不是孔子圈定的三百零五首,说诗经不是孔子编的。
孔子也是人,他的弟子也都是些大男人,我相信他讲课的时候,为了避免枯燥无味打瞌睡,偶尔来个笑话或黄段子是极其可能的,只是弟子们不会将之编进论语而已。诗经里有“淫诗”,也是读者阅读诗经的一点动力,也算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实践。关键的问题是,诗经里面的不雅内容,根本不是直接的露肉描写(哪像现在有的诗人就像写畜生一样直接),这正是诗的优点,采用象征暗喻等修辞手法,你心中想它有则有,想它无则无。比如《溱洧》里的“芍药”,你想它是花就是花,你想它是根就是根(说是像男人的东西)。你不能根据自己不堪入目的想象来当成是诗歌的描述,自己意淫怪诗人。这个问题,孔子定然明白。只要艺术性强,字面上符合“礼乐”,“诗无达诂”(董仲舒),你要怎么理解,他管不着。这里又重复一下孔子的那句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有人解释“无邪”是“纯正”,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是孔子,也会说是“纯真”(真情的流露),不可能说“纯正”(思想纯正),否则,一些容易让人想入非非的情诗就说不过去。

当然,为孔子辩护的理由还有很多,比如说,他也许把竹简都还给了周王室的礼乐管理部门,或者压根就没有借回家,直接就在那里选了。后来毁于战火,与他无关。假设当时借了需要归还,肯定是三千余首诗歌竹简一起还,无论借回家还是现场去查阅,孔子与弟子们除了选诗,还得抄录选出来的三百首,这得需要一批新的竹简和劳动时间。在“礼崩乐坏”,世人觉得诗歌形同废品的情况下,孔子与弟子们有多大必要去浪费竹简的成本和抄写的劳力?孔子选诗的目的很明确,希望能为周王室的复兴做贡献,自己觉得不利于周王室复兴或艺术性不高的内容,大可以烧掉,要是有意见,谁还能辩得过他?(除非老子李聃在场)基于对当时客观现实的认同,历代争辩孔子删诗的各方,未见有孔子把三千余首诗歌是否归还周王室去做重点考证,也难以考证。
孔子删诗的事实已经毋庸置疑。这也绝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弟子一起*。如果*理直气壮,内心无愧,必然在论语中谈到删诗的原则,根本等不到司马迁说。论语里没有只言片语对删诗说明,避而不谈。烧诗的理由必然存在私心,绝不是大部分诗歌在创意上重复类似(刚才说了,“去其重”的工作根本就轮不到孔子干,礼乐官员早就干了),也不仅仅是不符合“礼乐”。将余诗烧毁,后人再也无法选出一本与之相左的诗经来,再也无法对他们的编修水平与观点有所比较置评。
我们对孔子删诗的不满,都是因为大家总是觉得、怀疑、猜测、假想有很多很多无辜的好诗被他干掉了,可惜了,罪大了。如果他烧掉的诗都是一些烂诗呢?就像现在的诗歌,三千首诗歌中选出三首是不是都选的太多了呢?更别说三十首三百首。当然,历史没有假设,三千余首诗歌里面肯定有不少无辜的好诗被忽略了,冤死了。五个世纪,三千多首诗,该是周朝礼乐官员多次优中选精了,孔子的“去其重”,该是精品中选极品了。
历代为孔子删诗极力辩护人,也许都明白,一旦孔子删诗的事实成立,就不是仅仅删诗那么简单了,还有其他事情会让人联想。大家知道,易经以前有三个版本:连山、归藏、周易;孔子编修的《易经》是周易,连山、归藏至今下落不明,后世出现的,都被疑是伪作。今人不能超越时空,去抓古人的现行,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疑罪从无。但孔子删诗的事情,司马迁的记录让他成了嫌疑人。
根据现代教授学者的考证,孔子删诗的情况属实,那他犯了多大的罪呢?笔者的意见是:拘留七天,无罪释放。后人根本没有必要再花时间和精力为这件事情争辩不休。圣人也非完人,也有私心,功罪也得三七开(观点不同,比例不一样)。拘留七天,是对众多好诗亡魂的一个交代,有错就要认账,也是圣人之德。孔大圣人拘留七天,并不算少,胜过常人五百年。
好诗如人,皆有劫数,躲过了礼乐官员,躲过了孔子,还需要躲过秦始皇……如果好诗被毁,也是读者之不幸。渡过劫的好诗,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对诗人来说,要力求写出人们能永远铭记口口相传的好诗,别以为在什么刊物发表就沾沾自喜,也许,根本用不着孔子、秦始皇这类大人物参与,收废品的大爷大妈几声吆喝就能让它进入麻袋永远消失。

孔子删诗的警示
孔子删诗,对我们现代的教育意义非常大,新诗百年(1917到现在),产生了不少垃圾。浪费了不少纸张就罢了,关键是浪费了人民群众宝贵的阅读时间。我们再看看司马迁对孔子编修诗经的介绍:“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给我们当今的诗歌作者有什么启示呢?
首先,为了避免被“去其重”(“重”即在创意上重复类似),要么创意与众不同,要么在相同创意下你写的最好,否则就死路一条;在创意上要下功夫,不要写些平庸、俗套、泛美、混世之作(现在大多诗作都是这样的,即使有一些你感觉不错的,都形同韩国的美女,感觉上类似,充满空洞无物的泛美的伪描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杜甫《春日忆李白》),“不群”就是与众不同,这是杜甫对李白的评价,也是对自己的评价(注意那个“也”字),杜甫也是个充满自负的狂人,他有那个底气,“语不惊人死不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都是他的自我要求与激励。
其次,写诗要“可施”,即有用。那时的诗,可以配曲、伴舞。唐诗、宋词讲究格律,元曲更不用说,直接叫“曲”了,合乎音律,可以被用来说唱,多少诗家词人与歌妓往来,可以说是词作者与歌手的关系。现在的诗歌呢,“诗歌”已经被分家了,“歌”分到流行歌曲上去了(哪一首歌词不是广义的“诗歌”呢),剩下的只是“诗”(我们还是叫它诗歌,都动了变性手术了,我们还是叫他“哥”),你要讲究音律也可以的(不是必须的),但已经没法与歌词去比了。现代诗歌的音乐性很弱了,可以朗诵就不错了。诗歌的用处,大家能想到的,就是给人思想上的启迪、精神上的振奋、心灵上的慰藉,是益智的、励志的、安抚情绪的,是正能量的,甚至可以引用警句到别的文章里增添文采的,谈个恋爱表达心迹的,等等。如果不能开卷有益,我们为啥要读诗?装小资或文艺吗?现在是满世界的新闻、视频、段子,大家都过得像以前的皇帝,每天都有很多奏折要阅,有很多表演要看,能瞟上一眼诗歌,那是因为心中的孽缘未了,若还能一心扑在诗歌上胡啃乱舔,那是因为上辈子亏欠太多,有天赋,也有因果。
诗要有用处,应该做到易懂。诗人说我的诗就是良药,是最有疗效的,如果令人难咽,呕吐,那你的诗不适合阅读,适合注射。诗人说我的诗就是佳肴,是最好吃的,如果都是些光鲜的秕糠或者过期的陈粮,那就只适合做饲料。一个饲养员,就别把自己当成一个王者。物以类聚,你是人,靠的是同类把你拟人。
再者,就是要有思想高度,关心人民与人类,合乎“王道”。如果只是适合自娱自乐或圈内划拳猜酒猜中奖,于国于民没有一丝用处,浪费群众阅读时间,这样的诗,迟早会被灭迹,还等不到下一位孔子动手。别以为放在电脑硬盘就能存上千秋万代,上了媒体就是世人皆知(大多数都是自己朋友圈的哥们姐妹几个在意而已),诗的意义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当前多少写进媒体写进选集的诗歌,也写进了人民的心中?多少诗媒与选集都不过是不断更新的活棺材而已,只有死者亲属与盗墓者才感兴趣,不是吗?要是诗人臧克家还活着,也许还会写:有的诗活着,它已经死了,有的诗死了,它还活着。有的诗,在一些媒体或选集里能查到(活着),但无人记得(死了),有的诗,即使媒体或选集都被烧了或者不在其中(死了),但很多人还记得(活着)。
一句话,希望大家写出好诗,汉赋无愧于大汉的武力,唐诗无愧于大唐的强盛,宋词无愧于大宋的持久,元曲无愧于大元的辽阔,新诗也要无愧于中国梦!
欢迎提出宝贵意见,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谢谢!
2018年4月28日 绵阳涪城 樊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