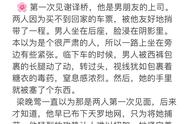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卑湿酷热的湖南永州用滂沱大雨迎来了一位颇负才气的大师。永州太寂寞,瘴气和兽类充斥着山野河泽,唯独缺少智慧的生命和浩荡的人文精神,于是,好像上天有意要安排一位文化使者来开拓永州的蒙昧与蛮荒,柳宗元蹒跚而来。
柳宗元的心境异常复杂。这里没有京师的繁华与喧嚣,有的只是宁静,孤寂落寞的宁静。事实上,在奔赴永州之前,柳宗元的人生一直都是畅达而风光的。作为河东名门望族后裔,柳宗元少有才名,年仅十三岁,便以一篇辞采飞扬的《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名动长安;二十一岁时,更是在没有通过任何请托的情况下,在长安科举中成功胜出,跻身仅仅三十二人的耀眼榜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和来自江南的刘禹锡一起,都是一举中的。风华正茂的年龄,共同的志趣爱好,让柳刘二人相交甚笃,而更让当时的文人为之羡慕的是,这个年轻气盛的组合会在几年之后,以火箭般的速度获得别人苦苦攀爬数十年也未必能得的中枢之位,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
柳宗元彼时的风光,来自中唐时期那场雷霆万钧的变革,史称“永贞革新”。“颇读书,班班言治道”的太子侍读王叔文在东宫十余年,深得太子李诵信任,而王叔文的视野显然不在东宫这片小天地,暗中结交了柳宗元、刘禹锡这些朝中的新锐,静候时机而待有为。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李适薨逝,王叔文一派冲破宦官和政敌的重重阻挠,终于将太子李诵扶上御座,是为唐顺宗。彼时的顺宗虽已中风失语,但这位早在当太子时就有重振朝纲之志的皇帝,已然将王叔文看作是自己意志的执行者。在他的力主之下,王叔文携王伾、刘禹锡、柳宗元、韦执谊等人迅速地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个小圈子中,真正有实职的,只有宰相韦执谊,但谁都清楚,身份只是翰林学士的王叔文才是真正发号施令的“内相”,而新晋的少壮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虽官阶仅提为正六品,却是强有力的改革主力。柳宗元后来曾撰文回忆说,“仆当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可见在当时已是极尽风光。
“永贞革新”的“动刀”之处甚多,宫市、税收、藩镇、宦官,都是王叔文集团力主亟待割除的“毒瘤”。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名年轻气盛的“急先锋”,柳宗元承担的是起草诏诰制命的工作,虽然只是案头工作,却涉及革新的核心。在笔走龙蛇之间,满腹豪情的柳宗元感受着积极用世的快乐,更找回了祖上黯淡已久的荣光。
然而,这场被柳宗元寄予极大热情的革新,面对一堵堵难以撼动的高墙,仅仅持续了一百多天,便随着顺宗被迫内禅进而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惨淡收场。被宦官拥立的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由于当初王叔文集团在继承人问题上并没有站在李纯一边,导致即位之后的李纯对王叔文集团采取了疯狂的报复。就在他登基当月,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参军,不久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其余八名重要成员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在瞬间由巅峰跌入谷底的八司马中,柳宗元的贬谪之地是相当蛮荒和偏远的湖南永州。柳宗元曾在其《与李翰林建书》中,说“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足见生存环境之恶劣。作为一场政治改革的失败者,柳宗元的安身立命之所只能是荒僻和不毛之地。皇帝将御笔直指永州,人烟稀少,再有韬略也不足以举事;远离京师,再有才华也不能乱我朝纲,这时再配上一个监视的官员和满眼的崇山峻岭,就锁住了一个中国封建文人的视野和心灵。
……哀余衷之坎坎兮,独蕴愤而增伤。谅先生之不言兮,后之人又何望。忠诚之既内激兮,抑衔忍而不长。芈为屈之几何兮,胡独焚其中肠。
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
——柳宗元《吊屈原文》(节选)
这段文字,出自柳宗元的《吊屈原文》。赴永州途经汨罗江时,柳宗元迁想当年投江自溺的屈原,不禁触景伤怀,写下此文。一千多年前,由于群小的攻讦加之国君的多疑,让胸怀家国的屈原被迫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悲回风之摇惠兮,心冤结而内伤”,王朝的障壁是如此坚实,他无力推倒,更无力重建,微弱的烛火之下,屈原,只能用一柄长铗挑起火光照亮心中的绝望。公元前278年,当秦将白起率领浩浩荡荡的秦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克楚国郢都,游走于湘水之滨的屈原再也无法抑止心中的悲愤,抱着一块巨石自沉于汨罗江中。从此,幽深阴沉的汨罗江,便容纳下一个诗人的生命和梦想,哀婉的诗行滋生成水草,昭示痛楚,也昭示孤独。
作为一个贬谪之官,柳宗元用一篇长长的祭文,和千年前的屈原进行时空的对话和精神的共鸣。永州在初来乍到的柳宗元眼中,自然也是一片蛮烟瘴雨,浊气妖氛。神志荒耗之中,柳宗元和家人一起寄住在永州龙兴寺,木鱼的笃笃声敲击着一代文豪日趋疲惫的才思,也在用佛国的梵音审视着这位失魂落魄的异乡人。“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新唐书·柳宗元传》)真的无恨吗?真的命由天定吗?事实上,受母亲卢氏影响,柳宗元自幼便笃信佛教,他曾言“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但在“永贞革新”期间,以求道明道为己任的儒家意识,还是让柳宗元无暇沉下心来诵一段经文,听一阵钟声。而彼时,坐在龙兴寺的禅院之中,永州一下子把精神的空寂和时间的杳渺全都抛给了柳宗元,手托厚重的贝叶之书,疏离梵音太久的柳宗元,总算可以盘膝静坐,寻找心灵的慰藉了。青灯微弱,寺院的钟鸣却一声紧似一声,从何处悟透禅关?从何处点亮久已废弛的诗思?这是一种痛苦的拷问,永州的山水平摊在柳宗元面前,像是在拒绝着孤独的对视,又像在等待着一个热烈的回答。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这首充满禅意的诗歌,曾被元好问称为“深入理窟,高出言外”,范温在《潜溪诗眼》中也赞不绝口:“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向因读子厚《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一段,至诚洁清之意,参然在前。”而杨慎之赞更是直接,直称此诗“不作禅语,却语语入禅,妙!妙!”事实上,这首诗正是柳宗元初到永州,寄居龙兴寺时所作。龙兴寺位于永州城南,时住持僧为重巽,坐禅于龙兴寺净土院,与住在龙兴寺西厢的柳宗元相邻。由于重巽是楚之南的“善言佛者”,故称其为“超师”。如果说,刚刚踏上永州这片土地,柳宗元还带着贬谪之臣的况怨,对永州山水人文并无感情,那么,当禅院的烟霭弥散于一张空白的宣纸之上,当佛国的井水冲涤开诗人封闭的心扉,柳宗元与永州的距离,已经在一点点地拉近。
是的,让柳宗元的骨子里融入永州意识的,正是他笃信三十年的佛教。史载,唐时的永州,虽地处偏远,但佛教活动却并不匮乏,南北往来的僧侣都将永州作为暂时的落脚之地,在这样一座荒僻小城,坐落着大大小小三十六处寺庵禅院,包括柳宗元寄住的龙兴寺在内,华严寺、开元寺、法华寺等,都拥有着众多虔诚的信众。正是在与这些寺院的高僧大德往来之中,心情郁闷的柳宗元找到了生命的出口,释放了心灵。他拜龙兴寺重巽住持为师,时常到其讲经说法的净土院研习佛经。对佛教精义有了深入了解之后,他仿佛醍醐灌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进而产生了援佛济儒、统合儒释的设想。“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当在浩荡的梵音中安下心神,当佛国的水汽漉湿渐染斑白的额角,柳宗元拭去感伤的泪痕,“自肆于山水间”,开始重新谛视命运,谛视人生,谛视永州。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由此,响遏行云的《江雪》的横空出世,便顺理成章!这首流传千古的诗歌,垂髫小儿皆能吟诵,历代画师更是借此诗意境,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卷。按理说,柳宗元的贬所永州,地处湖南南端,与雪缘浅,但上苍好像有意要和柳宗元开个玩笑一样,就在柳宗元来到永州的几年间,旱涝频繁冰冻十分严重,竟然出现了少有的极寒天气。柳宗元在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漫天大雪之中,柳宗元感受着永州的山寒水瘦,更对自己的内心进行着观照与自省。他把自己放逐成一个独钓寒江的渔翁,让自己成为大片留白中一个坐如磐石的黑点,而这个孤寂的黑点,恰与一千年前的屈原形成跨越时空的应和。自从“屈原既放,游于江潭”之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渔父意象,便成为中国文人遗世独立清标孤高的标准意象,而将这个意象置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荒原大野之中,更显出一个文人的超拔与独立!寒江之上的柳宗元,就是那个划动孤舟的蓑笠翁。彼时,经历了丧母之痛和居所火劫的柳宗元,太需要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覆压住内心的伤痛了,而偏偏永州有情,读懂了诗人,理解了诗人。凛冽的寒风夹带着多年不遇的鹅毛大雪,为诗人铺展开一张洁白干净的“宣纸”。这张“宣纸”,是永州为柳宗元量身而定,这张“宣纸”,摒弃了所有局外之人,只允许柳宗元一人跳进跳出。当柳宗元最终以一首冠绝千古、令人“读之便有寒意”的《江雪》,让自己成为永远的画中人,他不会知道,自己已然跨越了小我的悲喜,将人生的*怨与旷达融入一种拔俗自树的大孤独之中。
至此,荒僻的永州,终于有了淋漓酣畅的脚步声,那是柳宗元踏察永州山水的脚步。山水永远对应着中国文人的情绪:中国文人困厄感郁,山水也就黯然无光;中国文人激情澎湃,山水也就熠熠生辉。正是在对永州山水的踏察之中,柳宗元才发现,最早在他眼中满是毒蛇沙虱出没的永州,其实是中国道德文化的源流所在。坐落在这里的九嶷山,是舜帝南巡的长眠之地。接替尧帝的首领之位,舜面对的是滔滔洪水和纷乱的九州,于是,他要爱德施均,他要稽查巡视,就这样,他带着以后帝王少有的热情走到苍梧之野,走到了九嶷山,并最终崩逝于此,成为山谷之间的一抔黄土。而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在听闻夫君崩逝的消息后,便一路溯潇水而上,震彻天地的哭声回荡山谷,带血的泪水染红竹林,让浸着血斑的湘妃竹和巍峨高耸的九嶷山一起,共同构成了洪荒永州特有的文化符号。
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璇玑,七政以齐。九泽既陂,锡禹玄圭。……此焉告终,宜福遗黎。庙貌如在,精诚不睽。
……敢望诛黑蜧,抶阴霓,式乾后土,以廓天倪……
——柳宗元《舜庙祈晴文》(节选)
这段文字,出自柳宗元的《舜庙祈晴文》。融入永州的柳宗元,不仅融入了当地百姓崇舜、祭舜的习俗,更以卑微的永州司马之职通过撰写长文的方式为百姓消灾祈福。由于当时永州水患不断,他便在长文中一面极力歌颂舜的神威和对人民的爱护,一面又祈请舜能*掉黑蜧,击散阴霓,让土地变干,让天空晴朗。彼时的柳宗元与永州的关系,早已不再是初来乍到时的疏离感和陌生感,而是在和山水的亲密接触之间,和永州实现了不可切割的勾连。最能体现这种关系的,莫过于柳宗元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正是由于柳宗元的激情书写,永州,才得以于遥渺的传说之外,以一脉清逸的禅理汇入中国文化的激流。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这篇不足二百字的美文,是柳宗元《永州八记》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一篇,也是柳宗元献给永州山水的诚意之作。《永州八记》按写作顺序,依次为《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从这些题目看,摄入诗人笔端的永州山水不过是些土丘石陵,溪流浅洼,但柳宗元却以细腻的观察和灵动的笔触,让永州的山变得奇峰屹立,让永州的水变得空明澄澈,尤其是这篇《小石潭记》,更是将一个不知名的小潭写得气韵生动,出神入化。这是一处“竹树环合,寂寥无人”的人间秘境,又何尝不是柳宗元在与永州消除心理隔膜之后为自己也是为永州营造的一处心灵秘境呢?写这篇小品之时,柳宗元已由暮鼓晨钟的寺院搬到了愚溪。愚溪原名冉溪,是潇水的最后一条支流,愚溪这个名字,是搬迁至此的柳宗元所改,一字之差,自嘲之意尽显。柳宗元不会想到,这个愚溪的命名,会在此后千年,成为永州人恒久炫耀的标签,而永州本身,也因柳宗元的润色和经营,成为滋养和启迪中国文人心性的圣地。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宪宗元和十年(815),一纸来自长安的诏书送达永州,在谪居永州十年之后,柳宗元终于等来了重返长安的一天,心情自然无比激动。永州十年,柳宗元的政治郁气已经消弭于山水之中,此番返京,柳宗元只带上了始终萦绕耳畔的永州梵音和静水深流的文稿。当他于次年二月到达灞亭这座抵近长安的驿站,不禁百感交集,“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在柳宗元的眼中,缤纷绚烂的驿路之花张扬着满眼的春天的气息,更预示着自己未来美好的前程。然而,这种喜悦还没能持续一个月,便变成了兜头的一盆冷水。尽管“永贞革新”已经过去十年,但宪宗对柳宗元这些先朝旧臣仍旧耿耿于怀,心存戒备,而恰在此时,和自己一起重返长安游览玄都观的刘禹锡随手写就的一首小诗,触动了统治者敏感的神经,这些昔日的革新闯将,只能再次踏上贬窜之路。这一次,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为播州刺史,其余几人也都官贬远州。从司马到刺史,看似官阶晋升了,但贬地却更远了,尤其是刘禹锡被贬的播州,地处贵州,更为偏远荒凉,而八十岁的老母亲还要和他一起长途跋涉奔赴贬所。看到好友如此境遇 ,柳宗元慨然提出,愿意和刘禹锡的贬所做个互换,将自己换到播州去,“虽重得罪,死不恨”,这是一种怎样的道义使然!同为天涯沦落人,柳宗元只是贬所稍强于刘禹锡,便蹈死不顾,选择艰难,千载而下,这样的文人之交,怎不让人感动!尽管此后经老臣裴度从中斡旋,刘禹锡最终改贬连州,但柳宗元慷慨沆然的文人风骨,还是成为传诸后世的一段佳话。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
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柳宗元《种柳戏题》
被后人称作柳柳州的柳宗元,尽管自谦对柳州百姓“惭无惠化传”,但柳州百姓却将这位千里迢迢而来的贬官看作了心中永远的宗师大儒和清明之吏。经历了贬谪永州的精神洗礼,柳宗元在柳州很快就进入风风火火的为政状态。他不鄙其民,“因其土俗,为设教禁”,短短几年便将这一荒僻之地打造成了奉儒尊孔的区域文化中心。对“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没为奴婢”的恶习,柳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庸,视直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两袖清风的柳宗元自然没有太多余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自掏腰包,救助那些已没为奴婢的贫苦百姓脱离苦海,这样的父母官,又怎能不赢得百姓的拥戴!
柳宗元病逝于赴任柳州的第四个年头。这位一生多舛的诗文大家虽然如一颗流星,匆匆走过了四十七载人生岁月,但长安的“永贞革新”,有他激情擂响的青春之鼓;永州的山野草泽,流淌着他深沉内敛的散文之河;柳州的崇山峻岭,更是生长着他幽默生动的讽世寓言。这位将自己的名字镌刻进“唐宋八大家”的文化大师,给我们勾勒了形态各异的世间意象,黔之驴、临江之麋、永氏之鼠和那只虚构的小虫蝂,早已成为柳宗元对时代的思想投射,而柳宗元本人留给我们的生命意象,永远是那个独钓寒江的渔翁,在苍茫的雪野,手执钓竿,一坐千年……

(摘自《去唐朝——诗人和人世间》 常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编辑:殷华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
一校:王欣 二校:何建 三校:董小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