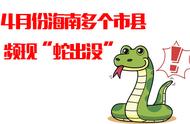让我们现在穿越到明朝嘉靖二十年的赣南山区。暮色里的黄泥墙渗着潮气,檐下挂着几串发黑的粟米,这便是佃农陈阿土的家宅。
他蹲在门槛上搓着麻绳,粗粝的掌纹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垢。灶台上那口豁了边的铁锅,还是他太爷爷那辈传下来的。
草棚里的聘书
"纳征要三斤官盐,老丈人还要两匹夏布。"媒婆染着凤仙花的指甲敲在木桌上,声音脆得像山涧的卵石。
陈阿土的指节在土墙上磨出血痕——去年给王老爷交完租子,全家粮缸里只剩半瓮掺糠的黍米。墙角堆着修补过三次的陶瓮,瓮底沉着去年腌的苦菜,霉斑像老人脸上的黧记。
新妇是十五里外李木匠的幺女,瘫在床上的老丈人要用女儿换棺材本。山里人娶亲简省了"六礼",但"纳征"的规矩断不能少。
陈阿土摸出藏在房梁裂缝里的碎银角子,这是全家人三年间从牙缝里省下的,原本要给咳血的老娘抓药。
村东赵货郎送来半升芝麻,算作"批田银"的添头。村西张寡妇连夜缝了件红绫衫,针脚里藏着去年她儿子娶亲时欠下的情分。山涧采的野茶晒干充作聘礼,靛蓝染的夏布裹着三枚永乐通宝——这便是穷汉的"三书六礼"。
织机上的晨昏
陈家院里支着单锭纺车,陈阿土的婆娘在晨光里摇着纱锭。寅时的露水浸透单衣,全家要赶在立夏前织出两匹布。
这种粗夏布市价每匹值银三钱,可抵半亩薄田的夏税。油灯下纳鞋底的活计交给了老母,针尖扎进指头也顾不得——这双千层底能换十五文铜钱。
"请期"的日子定在谷雨,陈阿土背着竹篓翻过三座山。篓里装着十二个染红的鸡蛋、三斤官盐,还有用葛布包着的铜镯子——那是他娘当新妇时的陪嫁。
山道上的碎石磨破草鞋,他想着新妇过门能帮着捻麻线,嘴角才扯出点笑纹。
村东当铺的柜台后坐着朝奉,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铜熨斗死当六钱,活当四钱二分。"陈阿土攥着死当的银子,去屠户家赊了半扇猪头——成亲那日若没有荤腥,要在乡邻面前丢尽脸面。
最愁人的是婚房。陈家把牛棚改成新房,土墙上糊着掺了稻草的黄泥。床板是拆了门板凑的,被褥里塞着芦苇絮。
陈阿土的堂兄去后山砍毛竹,准备搭个喜棚遮羞。这光景倒应了乡谚:"新人进门笑,老牛睡稻草。"
百家席上的盐粒
迎亲那日,村道上的唢呐声有气无力。陈阿土举着松明火把走在轿前,这是祖辈传下的规矩,再穷也得有把火照姻缘路。
四个轿夫都是本家堂兄,说好每人给二十文钱,最后只给了两升麦麸。新妇的嫁妆是口杉木箱,里头装着半匹粗麻、三双布鞋,还有她娘陪嫁的锡酒壶。
婚宴摆在祠堂檐下,六张瘸腿桌子是从全村凑来的。陈阿土咬牙买了两斤黄酒,掺了三瓢井水。
主菜是芋头炖猪头,油星子漂在汤面上,像穷人强撑的笑脸。女眷们带来的霉豆豉凑成四碟,孩子们盯着那盆粟米饭咽口水。
最体面的是里长送来的"茶仪钱"——二十文钱用红纸裹着,刚够买半斗粗盐。陈阿土挨个给乡绅作揖,瞥见债主袖口露出的借据,驴头红印在月光下渗血似的。
厨娘是张寡妇充任的,工钱是两把干菜。帮工的后生们偷啃猪头骨,被逮到时嬉笑着说"沾沾喜气"。
喜轿抬到门前,新妇的红盖头下藏着泪痕。她腰间系着苎麻绳——这是赣南的风俗,寓意"千里姻缘一线牵",实则是穷人家买不起红绸。
拜天地时供桌上摆着三个麦麸团,插着芦苇杆充作香烛。这场喜事,从头到尾都浸着汗水的咸涩。
月光照债台
喜宴散场时,陈阿土蹲在灶间数铜钱。收来的礼金共二百二十文,抵不上酒肉开销。
最要命的是赵货郎送来的"贺礼",实则是来讨两年前欠的两升芝麻。新妇默默摘下铜镯子,这是她身上唯一值钱的物件。
洞房花烛夜,月光从茅草缝里漏进来。新妇带来的杉木箱成了屋里最体面的家具,陈阿土摸着箱角的虫蛀眼,想起明日要去地主家扛活还债。床底的陶罐里埋着当票,赎回铜熨斗要再加三分利。
鸡鸣时分,新妇就着月光捻麻线。纱锭声惊醒了圈里的老牛——这牲口是全家春耕的指望。陈阿土摸黑去溪边挑水,盘算着秋收前要还清六钱银子的债。田埂上飘来当铺朝奉的咳嗽声,像条吐信的毒蛇。
回门那日,新妇挎着竹篮,里面装着借来的糙米和赊来的黑糖。李木匠摸着米袋直叹气,他想要的柏木棺材还差三尺。山路上,夫妻俩的草鞋都露出了脚趾,却还要强装笑脸应付乡邻的调笑。
喜字褪成白
腊月里讨债的拍门声,比迎亲的唢呐还响。陈阿土蹲在屋檐下,听着钱庄掌柜拨算盘的声响。
去年婚宴欠下的猪肉钱,利滚利竟成了一钱二分银——借据上的驴头印已盖到第七个,月滚五分利的规矩能把人骨头碾碎。新妇的铜镯子终究进了熔炉,换回的钱刚够买治痢疾的草药。
村头的土地庙贴满褪色喜字,陈阿土在这里磕了九十九个头。
他求的不是子孙满堂,而是来年雨水匀称。供桌上的麦麸团长了绿毛,香炉里插着芦苇杆——和成亲那日用的竟是同一把。
新妇临盆前仍在捻麻线,直到阵痛袭来才躺上稻草堆。接生婆要收二十文钱,陈阿土只能送去半筐腌菜,婴儿的襁褓是用婚宴剩的红布改的。
十年后的清明,陈阿土跪在爹娘坟前烧纸钱。火堆里飘着半张褪色喜帖,纸灰打着旋儿落在新坟上——那里埋着早夭的二丫头。
新妇把当年的红盖头裁成尿布,裹着刚满月的幺儿。山风卷着当年的唢呐声,在荒草丛里忽远忽近地呜咽。溪对岸王老爷家正在纳第五房小妾,十八抬嫁妆映得河水泛红,倒比陈家当年的喜字更鲜艳些。
草灰里的命数
嘉靖四十五年冬,陈阿土躺在透风的茅屋里咳血。当年当死的铜熨斗终究没赎回来,倒是钱庄的债滚成了五两银子。幺儿蹲在织机前纺苎麻,指头冻得像个红萝卜——这孩子明日便要去李地主家当放牛娃,一年工钱抵三两银。
新妇从樟木箱底掏出那截苎麻绳,绳结里还缠着当年的野茶渣。她给幺儿系在腰间时,忽听得村口锣鼓喧天。里长家的傻儿子娶亲,八人抬的朱漆轿子压塌了陈家菜畦。
月光照在当铺"裕民通财"的匾额上,那四个鎏金大字比土地庙的泥塑菩萨更亮堂。陈阿土的幺儿攥着麻绳沉沉睡去,他不知道这截绳子将来要系在自己的新娘腰间,更不知道朝阳升起时,村西坟岗上又多了个土包,而最顽强的喜字,始终刻在受苦人的命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