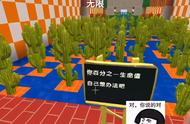这些日本学者们的潜台词,貌似践行“求真第一位”的学术理念,其实心态很微妙,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怀好意。这手法,和他们很多历史考辨相似,差不多就是釜底抽薪,是要深文周纳地要抹煞《藤野先生》文中,那种对日本军国主义批判的合理性。后来,我们不少中国学者跟着跑,委实是被带偏了。文学作品,多有艺术加工,或记忆有出入,是无比正常之事,和“虚构”是两回事,所谓“事或所无其理必有”,多简单的文学理论常识啊!

而且,在这则师弟子故事中,我最感兴趣的,始终还是鲁迅与藤野先生的真实关系。我们知道,鲁迅去世前写作《藤野先生》,一些表述确实是有意带点“滤镜”的,正如《朝花夕拾》诸篇也只挑拣美好回忆谈一个心理。他说,这些都是“残存的旧梦”,置身“旷野的黑夜里”,是不忍稍加打破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有位女副教授名为吴真,很青年的学者,向以研究中日文学闻名。近年,她出了一本新书《勘破狐狸窗》,专谈近现代中日间的人与书,颇受读书界关注。昨天买来一看,不料开篇就是谈鲁迅与藤野先生的,有意思。而且,一些材料或观点,也令我挺吃惊:

鲁迅在仙台时住所
1,藤野先生可能并不喜欢青年鲁迅,甚至有所不满,只是多年沉默。他们之间,仅相差7岁,其实是同龄人,都是铁汉子直心肠,有所误解很常情常理。比如,《藤野先生》开篇,鲁迅讲述在仙台的烦心事,说“一位先生”几次三番三番几次地要求他们搬到别处,让鲁迅不胜其烦,而这位先生后来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藤野先生,鲁迅是很含蓄地表达过当初的不满。

再比如,在鲁迅之后,藤野先生其实还陆续教过10几个中国留学生。这些人归国后都如约跟老师告知近况,不曾断联。唯独鲁迅,那位惦念他最深、成就也最大的伟大作家,是违背了“将来照了相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知近况”的诺言的。藤野一生把承诺看得格外重要,如此以来或许真耿耿于怀过,这个未经明证的解读,符合他的生平性格与为人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