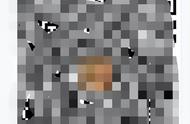奥洛穆茨圣母柱照片。 (捷克旅游局供图/图)
路边,一幢普通的深灰色楼房,凸角处有个凹口,放着一支白色的蜡烛,上面一粒小小的火焰随风飘摇。蜡烛旁边有几朵白色小花,花丛中一张很小的照片,下面有行字。我的心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也许一条生命曾在此处意外消逝。
在欧洲城市游走,对这样的情景并不陌生,特别感念当地人对人和物事的纪念,小到这样不起眼的点滴标志,大到各种人物、事件的纪念碑。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过去哈布斯堡王朝属地,如今的中欧,包括奥地利、南部德国、北部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部波兰、北部巴尔干地区,很少见到没有圣母和圣三位一体石柱的旧城区广场。这些圣柱的建造很多源起于感念上苍祛除黑死病的念头,于是,人们习惯称之为“鼠疫柱”。
当然,这是我们用现在的一切尘埃落定的眼光观察,而一切的一切,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轨迹。
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佩剑跪像

维也纳市的三位一体圣柱
维也纳。
充满皇家气派、浪漫气息的现代都市,格拉本大街两畔名店林立,大街中央矗立着一座精美华丽的塔形建筑,顶端的三一圣像金光闪闪,柱体环绕着玉白色的浮云和九位云端天使,他们是神与人之间的使者,也象征着鼠疫女巫被天使推向地狱。三层基座为人而设,面向西南的主立面上,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佩剑跪倒、右手抚胸,作为代祷者摘下王冠向上帝祈祷。
“利奥波德一世,您谦卑的仆人,将尽所能感激您祛除1679年奥地利的瘟疫灾难”;“仁慈的上帝,您谦卑的仆人,于1679年向救世主耶稣基督发誓:我及我的家族、臣民、军队和所有领地将永远在您的仁慈佑护之下”;此外还有赞美上帝的誓言、故事浮雕和属地徽章,分别装饰着三个主立面和三个方向的副面。
正西方向的副面上镶嵌着神圣罗马帝国双头鹰和奥地利纹章,东南方向镶嵌着匈牙利的双十字盾和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王国纹章,东北方向是波西米亚双尾狮,以及上卢萨蒂亚、下西里西亚纹章,刚好涵盖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几大组成部分,也刚好大致对应了实际的地理方位,同时,金色的徽章上方,分别镌刻圣父创世、圣子救世和圣灵净化。
圣柱最初于1679年动工。
鼠疫。
从世纪之初,伴随人类两千年,时隐时现,如魅影随形。十四世纪中期在欧洲大暴发,十五世纪中末期在英国,整个十七到十八世纪在欧洲此起彼伏,以至十九世纪。时至今日,2010年到2015年全球共报告了3248例鼠疫,其中包括584例死亡,也有中国的数字通报。(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1679年。
此前三百多年的1346年,暴发了鼠疫第二次大流行。当时人们没有治疗的药物,对公共卫生的认识也很有限,只能采用隔离的方法。
此前二百多年,意大利的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出生,他研究了梅毒的传播方式,被视为流行病学创始人。
此前165年,布鲁塞尔的安德雷亚斯·维萨里出生,他在1543年主持过一场公开解剖,制成的骨骼标本至今收藏在巴塞尔大学。他著有七卷本《人体的构造》,被视为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
此前101年,英国的威廉·哈维出生,他根据实验,证实了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现象,实验生理学创始人之一。
这一年,荷兰的安东尼·菲利普斯·范·列文虎克47岁,他最早记录观察了细菌,被誉为“光学显微镜与微生物学之父”。
这一年,临床教学以及现代学术医院奠基人荷兰的赫尔曼·布尔哈夫11岁。
1679年的60年之后,“疫苗之父”爱德华·詹纳诞生,他在书中首次使用了病毒一词。有人认为医学的现代式便始于爱德华·詹纳十八世纪末发现天花疫苗。
1840年代世界上首次尝试进行卫生改革和建立公共卫生机构,1848年英国通过《公共卫生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市政卫生要求,许多城市才开始建造普遍的下水道系统。
1854年约翰·斯诺发现伦敦霍乱流行的原因在于公共水井的水,将流行病学带入科学领域。
1679年,维也纳。
哈布斯堡家族自斐迪南一世开始垄断皇位,维也纳成为神圣罗马帝国事实上的首都;1160年建造的史蒂芬教堂已经矗立在市中心,维也纳大学也已经于1365年成立,最早版本的美泉宫于1640年代建造。
1679年,维也纳。
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维也纳同时也是沿着多瑙河从黑海到西欧、从地中海到中欧的贸易枢纽重镇。建筑密集,无排水系统,生活垃圾丢在街头,卫生条件落后。这一切为鼠疫暴发提供了条件。
终致12000人到75000人丧生。
数字。
340年前的数字背后,同样是340年前的数万个鲜活生命,以及每一粒尘埃压垮的家庭。到底是12000还是75000,到底有多少生命是数字,又有多少连数字都不是,已经说不清。
瘟疫,伴随着人们的恐慌;社会,从来离不开各种势力的角逐。
当时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本人逃离维也纳,他任命保罗·德·索拜特为议员及卫生条件总监,并发誓在疫情结束后,将建造一座纪念柱感恩。
保罗·德·索拜特一边施行隔离与卫生管理,一边对抗反对的力量,提出在远离城市范围的地方焚烧污染物和死者尸体,同时,为了规避不确定的风向把污物残渣吹到人群密集的地方,也进行深埋,对比此前的不触碰、不处置有了进步。同时,圣三一兄弟会成立了专门的医院,集中照顾被感染的病患,病死率比过去有了改善。
维也纳的黑死病纪念柱,就在这样的社会发展程度、文明条件之下,这样的一场大瘟疫之后建造。
开始是一根临时的木柱。1683年,重做总体设计,直到1694年揭幕。
而1683年,瘟疫之灾仅仅四年后,维也纳遭到奥斯曼帝国军进攻围城,终于在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当年的9月12日,和波兰立陶宛协作,解围城之困。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圣柱
格拉本大街上金光熠熠、玉光莹莹的黑死病纪念柱,21米高,利奥波德一世翘着典型的家族长下颌栩栩如生,有人说这是欧洲最精美的巴洛克雕塑。
而唯一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黑死病纪念柱,位于维也纳向北偏东二百多公里处的奥洛穆茨,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属下的摩拉维亚地区重镇,当今捷克共和国境内。
在原来的哈布斯堡属地、当今的中欧地区,作为唯一被收录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圣柱,这座雕塑的确与众不同。
大体上说,圣柱还是三层结构,顶层金色的三位一体圣像,中间十米高的石柱上,悬挂着圣母升天群雕,金色童贞圣母玛利亚被两位展翅的天使托举,衔接着神界与人间。基座分为三层,装饰繁复,每层都环绕着六位圣人的立像石雕,基座下面,还有七层台阶的底座,并围有石栏。
从台阶上去,可以走到基座的第一层,通过拱门,内部是一座礼拜堂。圣柱的基座里,容纳了一座小教堂。
整座建筑,高35米,最大直径17米。
参与圣柱建造的所有艺术家、工艺师都来自奥洛穆茨本地,圣柱上绘制的圣人,其事迹也和本地相关。
圣柱在1716年到1754年之间建造,38年之久,有些艺术家和工艺师,甚至没等到竣工就去世了,没能看到倾注心血的巨作诞生。
鼠疫肆虐摩拉维亚地区是在1713年到1715年之间。
而圣柱建成后不久,就赶上波及世界的“七年战争”。1758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对奥洛穆茨发动进攻,炮火击中圣柱,市民们为了保护心目中最神圣的珍宝上街游行,带兵的詹姆斯将军果真回应了敌对国的民意,网开一面。后来,人们在圣柱上被击中的部位,做了镀金标志,提醒后世铭记历史。
当我们从眼前的尘埃落定出发,试图追寻事件的发展轨迹,真是不胜唏嘘。
人类一路走来,坎坷不平、凶险无比。
被捷克人推倒的圣柱
中世纪中欧地区的圣柱,最早的灵感来自罗马帝国的圆柱,那些石柱顶端一般都竖立皇帝雕像。大约十世纪,开始出现圣母玛利亚站立柱顶的奉献柱。
文艺复兴开始于十四、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初期马丁·路德在德意志发起宗教改革,最终影响整个欧洲。传统的宗教势力与之对抗,发起反宗教改革运动,为使传统宗教统治更加稳固,利用标志性的形象强化信仰权威以及恩主与罪民之间的关系。十六世纪中期开始,圣玛利亚和圣三一柱便流行起来,庆祝灾难终结,对拯救者感恩或悔罪并奉献虔诚。
1636年到1650年间建造的那不勒斯的圣·热纳罗尖塔圣母柱,源于对1631年当地遭遇大地震的纪念。
1650年布拉格老城广场建造的圣母柱,则是为庆祝三十年战争结束,但捷克人也因此把圣母柱视为哈布斯堡统治的象征之一,于1918年脱离哈布斯堡专制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际,群情激愤之下推倒圣柱。布拉格老城广场成了中欧地区不多见的没有圣母三位一体石柱的旧城区广场。
布达佩斯圣三一广场上的三位一体圣柱,为保佑民众从鼠疫中生还,于1694年经议会决定,1700年奠基,1713年落成。
斯洛伐克科希策市中心的圣玛利亚石柱,和维也纳如出一辙,呈现华丽的巴洛克风格,建于1723年,纪念1709年到1710年的鼠疫终结。
捷克库特纳霍拉的圣玛利亚石柱,同样呈现着浮云天使的主题,建于1713年到1715年,纪念被鼠疫灾难夺去的一千多个生命,以及人们的感恩祈祷。
遗冢不断增多的人骨教堂
库特纳霍拉小镇郊外,还有一座与灾难和死亡相关的人骨教堂,里面的各种装饰、装置,全部由消毒晾*人骨构成。
五堆灰白色的人骨,堆积成谷仓般的塔。
几束细细的白骨连接成中轴支架,碎骨编成八条吊线,垂吊着,并与八个灯头相接,每只灯头均由八块骨片层叠散开,好像盛开的莲花,中间托着骷髅头,头顶上放着蜡烛。
纯真可爱的天使随意地坐在锥形柱顶端,举着胖嘟嘟的小手,稚气的眼神有些哀怨,天使下面的柱棱,从上到下七层,每层都摆放着口衔长骨的骷髅。
1278年,塞德莱茨修道院长从耶路撒冷带回一捧圣土,于是,“圣坟”的名声吸引了很多中欧地区的富人,希望身后葬在这里。但真实的死亡来得比人们的预想快而且迅猛。十四世纪,黑死病蔓延,仅1318年,“圣坟”遗冢就增加了三万多个。十五世纪胡斯战争后,墓园更扩大到3500平方米。
1511年到1661年间,教堂的神父陆续将这些骨骸收藏在地窖中。1870年间,受雇于施瓦岑贝格家族的木刻师傅灵特,将从此地挖掘出来的四万具枯骨,彻底消毒,排列成十字架、门楣、家徽与签名,做成装饰。这是对永生的象征和对复活的信仰。
新冠疫情中,布拉格重建圣母柱

布拉格市2020年1月23日开始重建老城广场玛利亚圣母柱
2020年1月23日,对于布拉格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市议会批准了重建老城广场玛利亚圣母柱的提案。
2月17日,老城广场的圣母柱原址,被围出了一个区域,开始施工。人们预计在3月21日完成地基部分的工作,不至于影响为期一个月的复活节市场活动。
没有想到的是,布拉格做出重要决议的1月23日,也是武汉封城的同一日,新冠病毒之后开始了全球大流行,捷克也在3月中旬进入紧急状态,实行了以保持社交距离作为关键词的措施,各种聚会停止,老城广场寂寞,复活节市场取消。但是圣母柱的建设,却没有停止,甚至意外地获得了更充分的时间,复活节之前,底座部分已经浮出地面,如同重生。
人类并非先天、必然地拥有智慧,但好在每个时代都产生了智者,他们从对人的好奇开始,也从解脱困境的需要开始,不断摸索、尝试,甚至离经叛道,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断突破当时的伦理认知,甚至冲破政治和宗教的藩篱,有时候也因此在被质疑中更新人们的伦理观念;他们不断通过缜密的逻辑推断所有的可行与不可行,在茫然无措和叠次的牺牲中,终于催生出现代医学、循证医学体系,催生出现代公共卫生系统。
人类也绝不是天生了悟,总是会沉湎于各种形式的族群纷争,不堪回首的故事,凝成了历史,信仰亦从世俗社会的统治中,退居到心灵寄托和道德影响的适当位置。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经历了民族复兴浪潮,终结帝制,走向共和,建立民族国家,又走过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扭曲和纠结。
这些纪念柱,美器之上承载的可能恰恰与美丽相反;远视的美丽可能恰恰以近视的苦难构成。
我们以为已经镌刻在历史记忆中的故事,其实从未离我们远去,就在身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
一座一座矗立在中欧地区各个旧城区广场上的鼠疫纪念柱,以生命为起点,混合着信仰、荣耀、权利,也将以生命为尽头。
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现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的圣母柱的重建,是不是体现了这种新的反思精神?
韩葵(作家,捷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布拉格中国作家居住地的联合创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