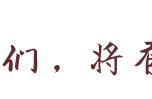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沈卫荣
本文系作者2022年7月14日在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线上讲座,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水木学者”博士后侯浩然整理。全文分两部分刊出,这是上篇。
今天我想和朋友们分享和交流我自己近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学术主题,即对汉、藏佛教传统中的观音菩萨崇拜和修法的比较研究。在此我有必要先对讲座题目里的“汉藏佛教视域”做一个简单的界定和说明。“汉藏佛学”是我于2006年海归以来一直在积极倡导和践行的一个学术理念和学术领域,近二十年来我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的重点就是汉藏佛学,十余年来我所指导和培养的学生也基本上都在从事汉藏佛学研究。
其实,汉藏佛学研究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有人做了,例如流亡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 1877-1937)先生于1927年在北京建立了一个“汉印研究所”(Sino-Indian Institute),身边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中西方优秀佛教研究学者,如陈寅恪(1890-1969)、于道泉(1901-1992)、林藜光(1902-1945)、雷兴(Ferdinand Lessing, 1882-1961)、李华徳(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等人,他们所从事的梵、藏、汉佛教文献对勘和研究,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汉藏佛学研究。1940年代,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佛教学者吕澂(1896-1989)先生得到了一部自清宫廷流出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集成——《大乘要道密集》,准确地发现它与元代宫廷所传藏传密教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于是他也开始倡导和率先开展汉藏佛学研究,用他找到的相应的藏文文本来解读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那些类似于天书的藏传密教仪轨文献。可惜钢和泰和吕澂先生开创的这种研究传统长期以来无人为继,以致早已被人遗忘。真正在中外学界大张旗鼓地倡导“汉藏佛学”研究,并努力要把“汉藏佛学”建设成为一个于世界佛教研究领域内可与“印藏佛学”对应的新学科,则应该是从2007年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建立“汉藏佛教研究中心”开始的。
如果今天借此机会来对这十几年来我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汉藏佛学研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话,我不无感慨地发现至今我们已经走过了三个前后相继,但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借用藏传佛教的说法,或可以把我们迄今所做的汉藏佛学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道次第(lam rim):
第一个阶段,我们在中外佛教学界率先提出了“汉藏佛学”这个学术概念,表明了构建一个与印藏佛学相对应的汉藏佛学学科的学术雄心,并对这个学科的学术内涵和学术方法(佛教语文学)做了基础的设计和界定。在这个初始阶段,我们在汉藏佛学这个学术架构下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则主要集中在汉藏佛教交流史、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史,或者说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研究,以及汉藏佛教文献的对勘和比较研究,提倡以传统语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汉藏佛教。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我们对作为一种独立的、创新的佛教传统,即汉藏佛教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佛教之身份认同的认知。当我们在汉藏佛学这个主题下,充分发掘和利用汉、藏、西夏、古回鹘、蒙古等多语种佛教文献,对汉藏佛教进行比较研究,并细致地研究和建构西夏、回鹘和蒙古佛教的历史时,蓦然回首,突然发现我们一直在研究、讨论和苦苦寻找的“汉藏佛学”原来早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我们所研究的敦煌佛教、西夏佛教、回鹘佛教、蒙古佛教和清代的佛教,其实都是一种汉藏、显密圆融的“汉藏佛教”,从此对它们的研究必须放在一个更加甚深和广大的汉藏佛学背景下进行,不能偏堕于汉藏的任何一方。
第三阶段,也是我今天这个讲座想要尝试做出的一种学术努力,即是要打破印度、汉传和藏传佛教之间早已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种种界定和壁垒,重新把印度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视作一个整体的、连续的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宗教传统,从而尝试从整体的、内在的和历史的视角出发,来开展汉藏佛教比较研究。具体来说,我想尝试从对汉藏、显密佛教之义理和修持传统本身的探究和比较,来考察它们的共通和不共之处,并观察和建构显密佛教之思想和实践是如何从同一源头出发,进而不断变化发展,最终形成各种不同传统的历史轨迹。
我今天的这个讲座就是想从前述汉藏佛学研究第三阶段这个学术设计和学术框架下,来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对观音菩萨崇拜和修法的理解,并想通过对观音菩萨信仰在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种不同传统中的表现形式和特点进行分析和研究,尝试向大家表明我所说的汉藏佛学研究的第三个道次第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佛学研究的新进路。观音崇拜是我最近特别感兴趣、特别想花力气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学术题目。我发现如果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传统中的观音菩萨信仰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弄明白很多与整个佛教历史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观音崇拜无疑是汉藏佛学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通过它,我们可以弄清楚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中观音崇拜在哪些地方是一致的,哪些地方它们又是不一样的,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们之间会出现这样的异同。然后,我们再来考虑同样是观音菩萨信仰,为什么汉传和藏传之间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特点和形式。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了,我们就不会再在印度、汉传、藏传、显教和密教等诸多传统之间人为地设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彼此之间产生那么多的误解,产生那么多的矛盾和冲突,换句话说,我们或可期待汉藏、显密佛教从此能够走上一条相互间更加理解、更加圆融的美美与共和健康发展的道路。
讲汉藏佛教中的观音信仰和观音崇拜,我想我们最好先从汉藏佛教中的两个最流行的咒语开始说起。汉传佛教信众念诵最多的一条咒语,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是一条礼敬词或者祈愿词,应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而在藏传佛教里信众念诵得最多的一条咒语无疑是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这两个咒语听起来完全不一样,但实际上殊途同归,它们的意义基本一样,都是为了呼唤观音菩萨、祈求观音菩萨救度,能让信众最后都能往生于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中!汉地的佛教信徒念“南无阿弥陀佛”,字面意思是“顶礼阿弥陀佛”,而其深层意义则是祈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的救度。大家知道,阿弥陀佛是报身佛,住在他的净土西方极乐世界里,而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心子,也是他的化身,是他派来人间救度众生的。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作为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菩萨,负责接引得道的众生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藏传佛教里,“唵嘛呢叭咪吽”是呼唤观音菩萨显灵的最常用的咒语。由此可见,无论是汉传佛教里赞诵“南无阿弥陀佛”,还是藏传佛教里念诵“唵嘛呢叭咪吽”,它们的目的都一样的,都是为了召唤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在大乘佛教信仰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与伦比,他是整个东亚佛教系统里面众多佛菩萨中最重要的一个,甚至可以说,他比阿弥陀佛、比释迦摩尼佛更为重要。曾有人说《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是整个东亚地区的“圣经”,而《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观音菩萨信仰的主要依据和来源,这个文本非常重要,它也曾以《观音经》的名称单独行世。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了观世音菩萨对整个东亚文化和生活习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我们常常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譬如,我自己每次坐飞机,当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我都会在心里默念“唵嘛呢叭咪吽”( Oṃ maṇi padme hūṃ),祈祷观音菩萨护佑飞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因为我是学习藏传佛教的,所以,在很多特殊的时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念诵这六字真言的习惯。如果别人更熟悉汉传佛教的话,大概就会念“南无阿弥陀佛”(Namo Amitābhāya Buddhāya)。二者在我们的心理上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消除飞行的紧张感,使人内心会得到宽慰。当然,很多人或许会说这是一种迷信,但我更倾向于说这反映出来的是东亚地区人们相当普遍的一种文化心理。今天,人们去浙江舟山朝圣普陀山,或去拜谒南海观音,或去布达拉宫转经、五体投地,其实其意义都是一样的,都是观音菩萨崇拜。“普陀山”,旧译作“补陀洛迦山”,汉语这两种译法和藏语“布达拉”(Photala)一样,都是梵语potalaka的音译,意指的都是观音菩萨的道场。记得当我于1988年秋天第一次去西藏时,汽车一进入拉萨,我远远地望见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我的眼泪就忍不住簌簌地掉落下来了,内心之中当即升起了一种殊胜的信仰!我到普陀山朝圣和去三亚拜谒南海观音都比较晚,但也深切地感受到普陀山香火的旺盛,不光有中国内地、港澳和台湾地区的香客,也有很多日本、韩国的来客,这说明观音菩萨的信仰今天在整个东亚地区依然很盛。当然,今天布达拉宫的热度与过去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佛教的角度看,普陀山和布达拉宫实际上是一回事,而今天从中国佛教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它们无疑都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布达拉宫
我们先来谈汉传佛教中的观音崇拜。在此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来体会一下观音菩萨在汉地的宗教信仰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我曾经遇见过一位华人教授,她的大名叫于君方,应该是全世界研究汉传佛教中的观音菩萨崇拜和《观音宝卷》最重要的学者,原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是德高望重的“圣严讲席教授”。她出过一本书,名字叫Kuan 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śvar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专门研究观音信仰在汉地民间的传播、发展和演变。有一年,我们在台湾一起参加一个有关观音菩萨的国际佛教学术会议,由她来做主题报告。她讲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故事,告诉听众她自己是怎么开始信仰和研究观音菩萨的。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一家人要从武汉坐船回家,据说当时船票非常紧张,一家人苦苦等待了整整三个月才好不容易拿到了船票。当一家人在码头上等着要上船时,她的外婆突然毫无征兆地拒绝上船,并且坚持不让家人上船。她的母亲,按照于教授的话说——一位接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新青年——不以为意,坚持要上船,因为如果这次放弃登船,则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会再有船票了。然而,他们终究无法违忤老人十分坚定的意志,最后一家人都没有登上这艘轮船。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那艘轮船在离港不久就进入了日本人部署的雷区,它被不幸炸沉了,船上的人全部遇难,无一幸免,唯有他们一家却逃过了这场劫难。后来,他们问外婆,当时为什么坚持不让大家上船呢?她的外婆——一位虔诚的观世音菩萨的信徒——解释说,她当时看见观音菩萨显现在长江之中,示意她不要上船。这件事情给于君方幼小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从此她就对观音菩萨生起了坚定不移的敬信,以至于后来她一辈子专心研究观音菩萨。她搜集了中国民间所藏的各种《观音宝卷》,对它们进行十分深入的研究,最后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观音研究专家。她的专著也已被翻译成汉语出版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一读。因为她有这样一个十分特别的经历,所以对观音菩萨产生了坚定不移的信仰,而且这种信仰伴随其一生。今天,很多人谈起他/她为什么对佛教生起信仰时,都会讲出一些特殊的因缘,但是作为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能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把与她学术生涯密切相关的个人经历讲出来,这还是不多见的。在西方学术界,一般说来,作为一个佛教研究者,多半不应该是一位佛教的信徒,学者应该和他研究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客观和中立。所以,你不应该把自己的信仰公然地告诉别人,于君方教授在学术会议上非常坦然地说了这件事情,我当时听了之后深受触动,觉得她这辈子是幸福的,不但一家人因为观音菩萨而得救了,而且,她一辈子研究观音,把个人根深蒂固的信仰和作为职业的学术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何等的幸运!

于君方著《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
那么,为什么观音菩萨会如此受欢迎呢?不管在汉传或者藏传佛教里面,观音崇拜为何都如此流行呢?其实,这和我们整个大乘佛教的根本信仰是密切相关的。大乘是相对于小乘而言的,小乘法门,是以自我完善与自我解脱为宗旨的,其最高果位为阿罗汉果及辟支佛果。笼统地说,小乘就是强调人人都能经过修道而进入涅槃,你自己修行、自己觉悟,不一定要关心他人的利益和成就;而大乘则认为有情都具佛性,只要虔诚地信仰佛教,人人皆可成佛,而且你既可以智慧自解脱,也可以方便他解脱,即身成佛。大乘佛教同时还主张不仅要自度、自利,还要利他,要兼度他人。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把一些乐于助人、乐善好施的人称为“活菩萨”,言下之意就是说他们就像是大乘佛教中所说的菩萨一样,慈悲为怀、利益他者。菩萨思想和菩萨理想是大乘佛教思想和修行的最重要的特色。那么,在大乘佛教中,究竟又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菩萨呢?
菩萨或菩提萨埵,梵文作bodhisattva;bodhi意为“开悟”或 “觉醒”,而sattva 则指“存在”,连起来就是指“开悟了的存在”。大乘佛教中,菩萨指的是生发了菩提心的人,而菩提心(bodhicitta)指的是一种自发的要求觉悟和利他的愿望和慈悲心,即发心愿为利益一切有情众生和佛法而觉悟成佛。大乘佛教的万神殿里有很多菩萨,而观世音菩萨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一位体现诸佛慈悲的菩萨,为了利益众生,轮回不空,誓不成佛,就是说只要轮回里还有众生在受苦受难,他就一定留下来救度他们。在藏传佛教中,行者要修本尊禅定也好,或者其他各种上师瑜伽和护法求修也好,首先要发菩提心,简称发心。今天人们常说要发心如何如何,这发心是指起意要做什么事情,显然早已经忘记“发心”这个词本来是一个佛教里面来的概念,专指发菩提心。我曾在黑水城出土汉文佛教文献中见到一个“持诵心经要门”,其中有一个发心偈:“諸佛正法菩薩僧,直至菩提我歸依,我以施等諸善根,爲有情故願成佛。”后来我发现原来这是最早由阿底侠所传,以后于藏传佛教各教派都通用的一个几乎是最著名的发心偈颂,不敢相信它这么早就已经传到了汉地的佛教信众手中。
按照大乘佛教的说法,菩萨无处不在,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或许我们每个人身边就有众多菩萨,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根器不够利,所以没能发现他们、认识他们。菩萨是可以随机应变的,所谓“随机”是指“随化机”,“化机”指的是一切有情众生,即我们这些可以被调伏、被救度的众生。菩萨随着“化机”的需求,化现到我们这个世界来,这就是“随机应变”,这不是投机取巧,而是一种善巧方便,其目的是对我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度。如果一名女孩子希望得到爱情,希望有个丈夫来保护她,菩萨可以化现为她的丈夫;如果有人特别希望做生意挣大钱,菩萨可以化现为“商主”来帮你做生意;有的村子上老是有各种各样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也可以祈请菩萨化现为村长来救度受苦的村民。这就是菩萨的随机应变。每一个菩萨都有自己的特点、擅长和神通,比如观音菩萨是慈悲的化身,文殊菩萨是智慧的化身,金刚手菩萨是力量的化身——我们以前讲到过印藏佛教中的大成道者,其中很多也是菩萨化身,他们各自显现诸多不同的神通,神通越大,救度有情的能力也随之增大。大家知道观音菩萨是慈悲的化身,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与其他菩萨一样,观音菩萨已经达到了菩萨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法云地阶位,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佛的果位——其智慧、神通与解脱均已达究竟,成为一切解脱智慧的源泉,一切想要求得解脱之法的众生的守护者,以及六道众生的救怙主。
那么,与其他菩萨相比,观音菩萨为什么特别著名、特别受欢迎呢?这主要是因为他/她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特质,因发愿利乐有情而具足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Mahākārunikacitta-dhāranī)中说:“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身生千手、千眼具足。”信众祈请观世音菩萨救度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一心称颂观世音菩萨名号,当你身处任何危难之中,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都可以通过呼唤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祈求其显现,并得其救助。所以,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是汉传观音菩萨信仰的最基本的方法。
说起观世音的名字,梵文作Avalokiteśvara,最早出现在《金光明经》(Suvarṇaprabhāsa-sūtra)中,历史上出现过几种不同的译法,竺法护(Dharmarakṣa)把它译成“光世音”(Ābhālokita-svara),鸠摩罗什(Kumārajīva ,343-413)译作“观世音”“观音”,而玄奘(602-644)在《大唐西域记》中批评了这两种译法,说“旧译为‘光世音’或云‘观世音’,或‘观世自在’,皆讹谬也”,他提出正确的译法应该是“观自在”。从现今常见的梵文形式Avalokiteśvara来看,我们很容易理解玄奘的译法:Ava-动词前缀 “下”,-lokita-:动词-lok-的过去分词,即“注意、看、观察”的意思,而-īśvara-,即 “领主”“统治者”或 “主人”的意思。根据梵语音变规则,-lokita-和-īśvara-组合时,a和ī发生元音二合,于是变成-eśvara。因此,Avalokiteśvara的意思是“俯视(世界)的主宰”,于是便有了“观自在”的称号 。显然,人们很早就被这多种不同的译法所困扰。唐代清凉澄观法师(738-839)指出“观自在菩萨”和“观音菩萨”是不同的译法,因为在梵文古本中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名称。他的这一说法在1927年新疆出土的古抄本中得以证实,其中观音菩萨的名字的书写形式为 Avalokitasvara,其中“娑伐罗”(svara),意思为“声音”,因此Ava-lokita-svara 可意译为“观音”。鸠摩罗什出生在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一带),可以想见,他当时看到的“观音菩萨”的名号很可能就出自这个版本的《金光明经》。“Avalokiteśvara”的藏文名字作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这种理解和玄奘的相同,sPyan是“眼睛”的意思,gzigs是“观”,dbang phyug是“自在”,在书面语和口语中常常省略dbang phyug,仅说sPyan ras gzigs,或即可与“观音”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