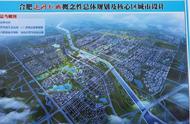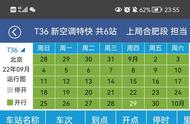初看凌贤长的照片,很难把他和教授这个身份联系在一起:他个头不高,一身棕色的西装,一副扁平的黑框眼镜,眼睛总眯着,头顶上剪出了两个四方的棱角——有人说他像个厨师,也有人说他像个土老板。
身边人公认的,是凌贤长总神出鬼没:前一天还在眼前,第二天就到了中国的另一头。他有一个小行李箱,在家里总是摊开着放,装几件日常的衣服,方便他接到工程电话后,拎起箱子就往机场赶。他半数时间都不在家,从一个工地奔向另一个工地。
他在国际上率先开辟寒区轨道交通动力学这一新的学科方向,目的在于研究寒区铁路路基振动反应与稳定性问题。他发明的高性能矿物基类胶凝材料与应用技术,解决了我国最北高铁站——伊春西站地基冻害防控的国际难题,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高纬度极端寒冷区高铁建设难度之最。
熟悉凌贤长的人,都觉得他太过低调。有老朋友说,这些年几乎没有媒体采访过他,他也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媒体喜欢有故事的人,不喜欢他这样的人,他这个人说来说去都只有学问。”
凌贤长的成就很多,“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出版著作10部,发表论文293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60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软件著作权25项与国际专利4项,牵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4项。”但在采访中他很少提及这些,只说自己是个解决土木工程问题的工程师,也是位教书的老师。

9月13日,凌贤长在家中整理学术资料。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摄
最北高铁站
伊春西站总工程师王文剑记得,今年八月,凌贤长第一次到伊春西站建设现场的那天,拄着拐杖,穿着一双不合脚的大号拖鞋,一双脚肿胀着,能清晰看见手术后的刀疤。王文剑一问才知,凌贤长刚做完痛风结石手术不久,术后康复还没做完,就来了现场。那天,凌贤长为了考察铁力-伊春高铁建设沿线工程地质情况,又行车几百公里。
此时,伊春西站的建设项目已经经历了三四个月的调研。这是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北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上铁伊段的终点站,位于黑龙江省中部,也是我国目前在建纬度最高、所处地区全年温差最大、首个在高寒岛状多年冻土区施工的高铁站房。哈伊高铁全线建成后,哈尔滨至伊春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以内。
然而,最棘手的施工难题摆在了眼前:在东北,到了春融季节,冻土融化,许多建筑物的地基开始凹陷,室外地面高度比室内往往高出二三十厘米。走进室内,就像走进一个大坑,地板松动,台阶也时常开裂。由于不同含水量的土质没有经过处理,土里的冰融化后,地基出现了不均匀沉降,外表看上去就像一层层高低不平的波浪。
而伊春西站地处小兴安岭腹地,属世界两大黑土带之一,黑土的孔隙性大、压缩性强,给施工带来极大难度。且当地冬夏季的温差达80摄氏度,地下有深达2.9米的冻土,地下水丰富,土的水含量极高。这意味着,地下水会经历反复冻融,导致周围土壤不断经历膨胀收缩的过程,入冬后,地基最高可隆起20厘米。因此,若不对土进行处理,路基的稳定性将受到影响,最终导致地面开裂、台阶断裂等问题,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建筑物倒塌。
此前,尽管国际上在寒区修建铁路已有100多年历史,但是路基或地基冻害问题尚未长期有效解决。王文剑说,过去常规的做法是控制土质的含水量或采用级配砂石等粗粒料。但目前的这些做法往往治标不治本:能短时间阻止地表水下渗、控制冻害问题,却无法阻止地下水通过土质的毛细孔向上迁移,地基或路基在两三年后仍会遭到破坏。
王文剑记得,经过前后多次线上会议,凌贤长又到当地考察后,提出了解决办法:使用团队研发的防冻害材料——高性能矿物基类胶凝材料。凌贤长将这种胶凝材料带到现场,掺入土中且拌合均匀、压实成型,仅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原本松软的土质变得坚硬起来。
之后,凌贤长和团队成员又从现场取回了代表性的土样,在实验室里做了数月的实验,针对土样改善了胶凝材料的配方,实验结果显示,该胶凝材料能对伊春西站地下的软土实施固化密实加固,阻断土的毛细孔,成功防止了地表水入渗、地下水毛细上升。“如此一来,高铁站地基土壤含水量能长期控制在一个很低的稳定范围,能成功实现高寒地区的地基或路基冻害防控。”
王文剑说,这种材料不仅可以长期有效解决地基冻害防控问题,而且能够降低工程建设成本、维护费用。
8月24日,在哈伊高铁铁伊段伊春市乌翠区站房施工现场,随着首根桩基顺利开钻,我国最北端高铁站伊春西站正式开工,再一次刷新了我国高铁建设的纬度。
转折
事实上,早在二十多年前,刚从博士后毕业的凌贤长,就开始了对软土加固的研究——用他的话说,就是把土变成“石头”。历史上,全世界各地的楼房都出现过地基沉降的问题。在国外,意大利的比萨斜塔,便是最出名的地基沉降建筑。
在过去,人们往往用土壤固化剂加强土的性能,或是通过水泥注浆的方式加固土壤,但时间一长,加上不同地域的地质条件复杂,效果有限,潜在危害仍旧不断。凌贤长思考,如果能把土壤变成石头那么坚硬密实,让土壤拥有完整结构石头的抗冻性和防渗性,再注入到地基里,不就不沉降了吗?
1998年,还是讲师的凌贤长把包括广西南宁、辽宁盘锦、山东东营、河南信阳等地的不同土壤,如湿陷性黄土、黏土、膨胀土、滩涂土等,通过绿皮火车拉回实验室。要使这些土壤实现固化,得反复进行化学分析、计算。凌贤长先通过仪器分析土壤的化学、矿物、颗粒等成分,再不断进行化学反应分析且调整胶凝材料的配比方案,继而反复做化学分析计算、配比实验。
实验过程艰难而又漫长,过程却并不顺利:化学反应方程式推导出来是一个样,做起实验来结果却又不理想。
由于矿物材料的运输、检测、活化等过程需要大量费用,凌贤长用完了有限的科研经费,一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好在坚持了下来。凌贤长记得,实验进行了两年后,第一次成功实现了土壤加固,同校的老师惊讶于实验结果,换了七八个压力机检测,才最终证明了实验的成功:加了研发新材料的土壤达到了8个兆帕以上的强度,约等于一块红砖的强度。
如今,凌贤长研发的高性能矿物基类胶凝材料技术通过不断的改良,形成了不同的原材料配比方案,能适用于二十多种土壤的防渗加固、冻害防控,而这项技术也获得了14项国家发明专利。
与地质和土木结缘,是自小时起,凌贤长的家乡在安徽合肥的一个农村,他总见到地质队的人,背着地质包四处跑。他觉得,地质这份工作不错,“拿工资还能到处游山玩水。”
后来,他便报考了长春地质学院的矿产普查专业,在地质学领域从本科一直念到博士。1998年,36岁的他决定转行跨入岩土工程领域。
这是颇有难度的一次尝试。凌贤长说,硕士、博士专业均为理学,而岩土工程是工学,两者无论在思维模式还是涉及的知识领域都相差甚远,此前几乎没有人敢在这两个专业之间跨行。凌贤长则看到了土木工程领域的巨大潜质。他觉得,当时国家正逐步迈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不论是建筑、公路还是桥梁的建设,都离不开岩土工程。自己有很好的地质基础,在岩土工程上一定能有所成就。
转专业后,凌贤长从土木工程的入门学科开始读起。彼时学校正修图书馆,为积累实践经验,他每天到图书馆去,认项目总工程师为老师,比对着建筑现场与书上的名词,问“这是不是构造柱?那个是不是挑梁?”此后,他又自学了包括材料力学、固体力学、弹塑性力学等等的力学的所有课程,且兼修了计算机编程。
凌贤长回忆,那会儿家中空间不大,他抱着一摞摞书去阳台,在地面铺上塑料泡沫板,就地学习,“按现在的流行话,我那时候就是5 2、白加黑。”由于压力过大,他一度胖到了194斤,衣服和裤子都只能穿加大号的。但他坚持了下来,最终,只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土木工程博士后的研究课题。

8月底,凌贤长在伊春西站建设现场。受访者供图
治理土木工程疑难杂症的“大夫”
博士后出站后,凌贤长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当老师,“到了学以致用的阶段。”
他开始频繁地跑各个工程项目现场,一接到电话求助,他拎着行李箱就赶往现场。一年里的半数时间,他都在工地上。“工科的研究一定要做到工程现场,工程现场就是你的研究基地。到现场必须能够解决工程问题,教授到现场什么都不会,就坏了招牌。”他总这么和学生说。
做工程这些年,最让凌贤长觉得骄傲的,是广西龙州金龙水库大坝的防渗加固工程。
原先,水库的水资源能满足周边两个县的全部用水需求。但由于水库大坝水大量渗漏,在雨水充沛的夏天,水库的水线竟日渐下沉。水留不住,当地的水稻就长不高,工业和农业用水都受到影响,老百姓也总缺生活用水。
在现场考察过土质和地形后,凌贤长花了一个月时间,现场就地取土且掺入高性能矿物基类胶凝材料制备浆液,对大坝实施注浆堵漏,成功解决了水库漏水的问题。
他的高性能矿物基类胶凝材料还应用于北京北二环一处地铁站的建设。他说,由于该地铁站的地基是回填土,具有高孔隙率、高压缩性的特点,在人工地下开挖不久后便开始出现地面沉降。眼见着沉降程度已经到了红线,北京城建集团找到他,他带着几袋胶凝材料从沈阳开车赶到北京。现场就地采取粘性土且掺入一定量胶凝材料制备浆液,对回填土地基进行注浆,注浆结束8小时后,便控制住地面沉降,施工得以继续进行。
后来,凌贤长又将高性能矿物基类胶凝材料及其原理用于研究工业固废资源化无害化综合利用问题。他举例,通过他研制的胶凝材料对工业用尾矿砂进行固化,再将固化后的尾矿砂回用充填采空区,既能保证地面不下陷、采矿活动照常进行,又能保证尾矿砂不到处堆放污染环境,“让这些尾矿砂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
凌贤长自称是治理土木工程中源自岩土疑难杂症的“大夫”,只要是关乎岩土工程的,不论大小,他什么“病”都看。他认为工程无小事。“一项工程拖一天就是巨大的成本,农民工也都在工地上等着项目收工。”
中铁十七局集团董事长陈宏伟和凌贤长是多年好友,起初因工程项目结缘。十几年的交往下来,陈宏伟常说,凌贤长真实低调、表里如一,在工地上能和农民工打成一片。
在陈宏伟的观察中,一旦发现某个工程难题,凌贤长立马来了兴趣。“不问项目对他有没有用,要投入多少精力,投入多少劳动,有什么回报。一旦发现是非常有价值的课题,啥都不说,咱们就来研究怎么把这个事搞成。”

凌贤长在接受采访。受访者供图
师者与传承
工程师的身份之外,凌贤长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土木工程学院授课。他依然爱给学生上课,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课他都接,他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
他爱提哈工大的校训:“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觉得这句校训全世界“最土”,对工科的科研却最有价值。“人才的培养和科研的工作都讲究过程,过程比结果重要。做任何事永远要按照最高规格去做,最后的结果才能功夫到家。”他讲了几十年的课,上课前仍要打开课件从头到尾过一遍。
在学生们眼中,凌贤长是“严格”的,他对各类文件排版也有严谨要求。
学生杨忠年记得,一次,自己带着项目成果展示的PPT到凌贤长办公室和他核对,凌贤长坐在电脑前开始一字一句地重新检查。不光是字句,PPT里每个矩形框彼此之间的上下左右都要对齐,且行与行、字与字的间距必须一致。一份五十几页的PPT,凌贤长在办公室花了六个小时仔细打磨。
杨忠年说,这与他印象中的工科教授不同:大部分工科教授在工程上认真,在文本上并不讲究,但老师凌贤长却细致到了文本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错误。凌贤长曾向杨忠年解释,这个做法是对每个专家的尊重。“你自己都不认真,专家凭什么认真?”
多年下来,凌贤长的学生们都形成了这种自觉:在交项目书之前,即便已经十拿九稳,仍要细致地再重新看上几遍。“有时感觉已经无可挑剔,再发给他,他还能给你找出很多毛病。”
早年读书留下的习惯,凌贤长每天凌晨两点才入睡,早上八点又起来。一天的时间多围着书桌转——他用一张黑色中式翘头木桌做书桌,一台电脑、两张硬盘、一个烟灰缸、一个手机支架和一个茶盘是桌上所有的摆设。
在学生眼里,老师凌贤长既是自己学术路上的灯塔,又是人生路上的导师。
凌贤长带出的学生,有的在高校当上了教授、博士生导师甚至校长,有的成了高级工程师。学生苏雷记得,早年自己还是博士生时,老师凌贤长自己掏钱供他完成了美国一年的访学课程。如今,苏雷已经是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凌贤长时常回忆起早年,还在做地质学研究的他到一处高山上做地质勘探,因为路途险峻,同行的一位年轻研究生折返,只留他一个人沿着确定好的线路继续向前。在一处峭壁上,他踩空滑落,所幸被一块凸出的石壁接住,吓得一身冷汗。而后他坐在悬挂着的壁沿上抽了一根烟,把烟头一扔,又继续向上攀爬。“地质学有条行规,一旦布完了一条线,一整天都必须沿着这条线走下去,遇山过山,遇水过水。”
如今,凌贤长仍在“遇山过山,遇水过水”,在科研这条道路上缓慢而坚定地前行着。
他六十岁了,长期痛风使他走路缓慢,上下楼梯前,左脚踩着楼梯沿,右脚顺着放,一步一跛。他希望自己“再活六十年”,继续解决工程上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填补那些学术领域尚存的空白。
和岩土打了几十年交道,凌贤长觉得,自己好似也活成了岩土的模样:像岩石一样坚硬,磕开一个个难题,又像黏土一样缠着问题不放。
同题问答:
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守的?
生活上,我一直坚持我自己的生活规律。工作上,我坚守着一个做事原则:无论是自己的事还是别人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去认真对待。少一些承诺,多一些兑现。
什么时候是你认为最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我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我转行做岩土工程博士后的时期。
我这人有个性格:当我决定要做一件事,我想到的不是困难,而是不断寻找解决办法。困难肯定有,但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远远比困难多。
你希望未来还取得怎样的成就,对于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我希望能多培养出几个优秀的接班人,最好是做事不怕吃苦、踏踏实实的接班人。同时希望能和学生一起研究解决岩土工程中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你感觉你获得的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最大的快乐是,这么多年我经历了数个岩土工程难题,我都能给它解决了。
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