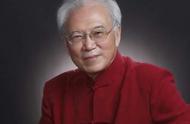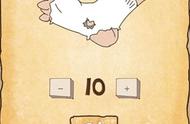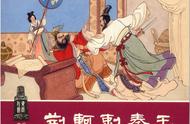《陈子昂登幽州台图》,许多画作将陈子昂画成站在一个高台或山峰之上,但事实上,陈子昂当时是站在蓟北城楼上。见他的好友卢藏用为他撰写的《陈氏别传》。
事实上,燕昭王黄金台的传说,在先秦典籍与《史记》中皆无记载。晋代鲍照《放歌行》中,才第一次出现“黄金台”之名,指的还不是燕昭王的黄金台,而是燕国末代太子丹的金台。直到隋代《上谷郡图经》中,才莫名其妙地首次出现“黄金台,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的记载,但对生活在初唐时代的陈子昂来说,黄金台已经由一个东拼西凑的传说,变成了一个信而有证的历史记载。那么他怆然泣下的所在,便不再是一个建筑在虚构传说之上的当下建筑,而是一段令人慨叹追念的真切历史,而这段历史,对身处此地的陈子昂来说,更扣紧了他此时此刻的心弦。
696年,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及其契丹部众,因对营州都督赵文翙奴役暴政不满,在突厥默啜可汗的支持下,起兵反叛。武则天派出子侄武攸宜前往平叛,陈子昂作为参谋随军同行,前往幽州。但这场战争开局不利,前军相次战败陷没,武攸宜大为震动。陈子昂相信自己建功立业时机已至,因此主动进谏,请缨带兵。但在主帅眼中,他不过是个体弱多疾的书生,因此不仅拒绝了他的请战要求,更因为反感他的喋喋不休,将其改署军曹闲职,掌管文书。因此,他登上蓟北楼,自伤身世,而泫然流涕,放声高歌这首《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并非一位刻意追寻历史记忆的旅行者,但历史记忆却会主动找上他。当他站在蓟北楼上流泪咏唱《登幽州台歌》时,已经道破了历史旅行的个中三昧——历史之所以能与旅行连臂而行,正是因为历史具有一种穿越时空俘获心灵的魔力,它能让旅行者的脚步跨入另一个时空,让现实行走踏下的足印与历史留下的印记在某一个时空交汇点上相合,从而让旅行者当下的心灵与过去发生共振。
纵然是陈子昂含泪感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但他内心中分明清楚,他所向往的,正是那已经不见的古人史事。他分明站在这段历史发生的地点,但历史却没有在他的身上重演。他想寄望于来者,但来者又非他所能逆料。他只能孤独地站在现实之中,为历史的逝去,为将来的未来而怆然泣下。
历史旅行,正如走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左边是历史的幽谷,右边是未来的深渊,而自己正走在现实的山脊上,时时左顾右盼。
史与文
前可见故人
马第伯正在山路上跋涉,但“上山骑行,往往道峻峭”,于是他只好“下骑步牵马,乍步乍骑”。直到上到半山腰,马无法再向上攀爬,他只得将马留下,继续步行攀登。此时,他已经距离平地二十里之高,向南极目眺望,无所不睹:
“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峰。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如无道径。遥望其人,端端如杆升,或以为白石,或以为冰雪。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
山的雄浑高峻,人自身的渺小,以及轻度恐高症患者自下而上仰望时的那种眩晕感,都被马第伯一一状写描述。考虑到这是中国现存于世的第一篇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真实旅行记录(如果排除《穆天子传》这样充斥着怪力乱神的半真半假的游记,马第伯的游记也是第一篇真人真事的真实旅行游记),不得不承认其写物状景的笔法之圆熟,使人如临其境。
但马第伯的这场旅行,也并非简单的游山玩水,而是负有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如这篇旅行记录的标题《封禅仪记》,他所记述的,乃是东汉光武帝在公元56年封禅泰山时,他作为先行官登泰山进行准备的过程——他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历史时刻的参与者。为了筹备这场有汉一代最重要的历史盛典之一,他必然也要留心前人举行封禅大典的历史,作为如今举办仪式典礼的历史借鉴。虽然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都举行过封禅仪式,但它们毕竟太过久远,以至于久远到不知是否真实存在。能够从真实历史中取材的,就只有前朝秦始皇与本朝汉武帝所举行的两次封禅。

秦始皇封泰山碑,北宋拓片
尽管从汉武帝时代到马第伯所处的光武帝时代,中间经历了王莽新朝的中断和兵连祸结的天下大乱,距离秦始皇时代的封禅,更增加了一重秦末大乱的破坏性因素,但马第伯还是找到了当年武帝封禅时留存的一些古迹,包括一块祭坛上的石头,“状博平,圆九尺”,因为“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从泰山天门郭东上一百余里,马第伯又找到一个木质乌龟,“木甲”——“木甲者,武帝时神也”。又向东北方行百余步,终于抵达封禅之所,“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在正式封禅的祭坛上,马第伯看见“酢、梨、酸枣狼藉,散钱处数百,币帛具”,这些混乱狼藉地铺在祭坛上的钱物,也被说成是“帝封禅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为先上跪拜,置梨枣钱于道,以求福”用的物品。
传说与遗迹构成的历史记录,与亲身体验所描摹的文学叙述,两者同时存在于马第伯的这篇旅行记录中。尽管它纯属公务出差的记录,但作为游记,它同时兼具文学与历史两个面向。而这两个面向,也成为了后世中国旅行文学的两条道路。文学用以状写景物,抒发心情,驰骋想象,展现的是遣词用句的才华;历史则着眼于精准地记录,以及对蕴藏在路途与景观之中的幽微史事的钩沉汲隐,它所彰显的是博览群书的学识。
公元四世纪东晋高僧慧远的名作《庐山记》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开篇一节:“山在江州浔阳南,南滨宫亭,北对九江。九江之南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余。左挟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障’,彭泽也,山在其西,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有匡续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续受道於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描述地理形势以定位其所在,引经据典考证其来由,记述传说以论证庐山得名之来源。精准、明晰,几乎可以说完全是史家笔法,足显慧远的采摭书传,博闻广识。
接下来,慧远却笔锋一转:“风雨之所摅,江山之所带。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穿崖,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抟,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其声骇人,此其化不可测者矣”——庐山气势撼人的雄浑气象,跃然笔端,精心构筑的辞章,如泄水排云般连贯而出,即使是听到文言文就昏昏欲睡的今天读者,如果能够舌头不打结地通读一遍,也能感受到那种一吐胸襟的勃勃气势。这也是慧远的《庐山记》千载之下,得以列名经典的原因。

《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作者:(美) 何瞻,译者:冯乃希,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史与文的交汇,让旅行文学兼具博学与辞章两者之长。慧远的《庐山记》还在不经意间点出了游记与历史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讲到庐山第三岭时,他写道:
“昔太史公东游,登其峰而遐观,南眺五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登天庭焉。”
被奉为中国史学鼻祖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曾是一位旅行爱好者。一如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坦陈的那样: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司马迁曾以史家笔法写过游记,但他本身足迹踏遍天下,旅行中自然也会访求故老,探听传说,记录下来,成为撰写史书的材料。就像他在《孟尝君传》的最末所写的那样:“吾尝过薛,其俗间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司马迁笔下的孟尝君事迹,自然也有不少是他游历当年孟尝君封国薛地时探访所得——他的目的明确,是为搜集史料,他访问当地故老土人的方法,几乎相当于今天口述史的方法。司马迁虽然没有写下一篇历史旅行的游记,但他本身已经为未来的历史旅行写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是需要像马第伯这样的人,以他采择史料,探访故实的方法,完成这样一篇游记,作为开山之作,历史旅行书写,就以这种方式,在烘焙许久之后,新鲜出炉了。
到慧远撰写《庐山记》的魏晋六朝时代,旅行文学的史与文两种形式,几乎已经定型。五世纪谢灵运的《游名山志》虽然仅存三十余条,但也足以看出旅行文学的发展态势:“泉山顶有大湖,中有孤岩独立,皆露密房。《汉史》朱买臣上书云:‘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
其中既有精心雕琢的辞句“孤岩独立”,也有引经据典的史料“《汉史》朱买臣上书云”,这些几乎都成了未来游记的标准范本。前人的作品成为后世模范的典范,后世的作品中,也常常能看到前人的痕迹。就像陈子昂怆然泣下的《登幽州台歌》,谙熟典籍的人,也会发现他是在“化”《楚辞》中的《远游》一篇:“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两者对读,几乎会误以为陈子昂流泪的原因不是自伤身世的怆然,而是洗稿太过的羞愧。但“化用”前人本就是诗文创作灵感来源的公开秘密。诗文如此,游记自然也如此。因此,在阅读明代游记时,经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徐世溥《游洪崖记》中“瀑奔流至此,则复冲激上山,左右喷薄,洗石壁,逆流同下矣”,就是在暗中学习慧远《庐山记》的韵律与措辞,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虽然最优秀的旅行文学是文史兼备的作品。但在书写游记时,指针是向文偏一些,还是向史偏一些,却是个值得忖思的问题。文史之间的旅行者,就像是在大漠中行走,前后左右,四面茫然似乎到处是路,也似乎无路可走,只能凭借直觉向前走去。
记与访
后可见来者
沙海之中,四顾茫茫,但就在迷惘不知该往何处前行之时,远处一座闪光的崖壁,却像烈日下的灯塔一样,指引旅行者在沙海中投奔而去。热浪渐渐被视线中的青葱绿色拨开,崖壁上的闪光也凝聚成一尊实像,那是一尊在崖壁上开凿的巨大佛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旅行者长出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到了梵衍那国。

刘拓拍摄的巴米扬大佛石窟,出自他所撰写的《阿富汗访古行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踏上了前往西方天竺的求法之旅。梵衍那国是他西行途中的一站。在他的西行旅行记录《大唐西域记》中,他如此描述这个国家:
“梵衍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势邑居。国大都城据崖跨谷,长六七里,北背高岩。有宿麦,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马。气序寒烈。风俗刚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睹货逻国,语言少异,仪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邻国。上自三宝,下至百神,莫不输诚,竭心宗敬。商估往来者,天神现征祥,示祟变,求福德。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宗学小乘说出世部。”
玄奘对梵衍那国的记述毫不拖泥带水,用词精准,几乎没有任何文学上的修饰。提到那尊崖壁上的著名巨佛,也仅在必要时才加上“金色晃曜,宝饰焕烂”这样浅白得毫不夸张的描述。考虑到玄奘所看到的这尊巨佛,就是在2001年被塔利班武装组织毁灭的那尊巴米扬大佛,今天的读者也许会抱怨玄奘为何不能多花些笔墨,更细致地描述这尊大佛外观的衣着纹饰和细节,以至于单凭他笔下的寥寥几句,都无法确定这尊佛像究竟塑造的是哪一位神佛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