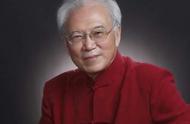《阿富汗访古行记》,作者:刘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
但玄奘不会在意今天读者的看法,就像他不会在意游记中这些细节的描述。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完成一部游记,其目的也不是为了给读者带来心驰神往的异域体验,他是在撰写一部西域的地理志书,就像史书中常见的《舆地志》《地理志》一样。他追求的是历史的简约与精准,而不是华丽的辞藻与抒发个人感受——那样带不来任何信息上的增量。
信息的增量,这是历史与文学之间最大的区别。历史可以使用文学笔法来讲述故事,但关键还是提供真实有效的历史信息,而文学则不然,它可以用尽各种华美繁复的辞藻来描述一件事物,但这些文辞本身抒发情感,给人增加阅读的快感与欢愉之外,并不能为故事素材本身提供更多的增量。游记一旦使用历史的笔法,就会尽可能地将文学色彩或是作为渣滓剔除出去,或者高度浓缩提炼,只留下最精准的一两个字的描述。游记越是偏向文的一方,就越是辞藻华丽,踵事增华;越是偏向史的一方,就越是不加点染,精炼提纯。
那么,什么样的游记适合用文的方法,什么样的游记又适合用史的方法呢?对短途旅行的作者来说,他要状写山川秀美,河海泱泱,他完全不需要穷究历史,只要用四五百字的华丽辞藻撑起这个短篇游记就足够了。他们的旅行是无目的也无计划的,只是为了抒发身心。游记对他们来说是文辞炫技的饰品,靓丽闪耀但徒有其表。然而,对那些预先设定了目标,并且需要长途跋涉来达成这一目标的旅行者来说,他们一路上要搜集资料,记录见闻,他们要保证自己的记述真实可信,而不是虚有其名的夸夸其谈。
那些浮夸华丽的辞句就像海绵中的水分,在沙漠真实烈日的炙烤下迅速脱水,只剩下真实本身。但真实也自有其力量,特别是当这种真实以一种残酷的坦诚方式书写出来时,尤为令人感同身受。玄奘的前辈法显的《佛国记》就是这样一部真实到令人痛苦的旅行著作。法显对自己的写作目的毫不讳饰,“将竹帛疏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所见”,因此这部行记即使作为历史文献来读,也毫无夸大之嫌。在写到自己亲历的戈壁沙漠的环境时,他描述道: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这段描述极富戏剧性,但也相当直白,正因为直白,因此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法显叙述的是沙河中真实的、不掺杂一丝幻想的鸦片,但其中绝望与希望之间天人交战的缠斗,却足以超越那些浮夸绚烂的文辞。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正是法显《佛国记》忠实的追随者。他也记述了可怖程度不亚于“沙河”的“大流沙”,其笔法与法显如出一辙:
“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
法显与玄奘的旅行记录,可以说是历史旅行文学的典范之作:精准、充实、真实而毫不夸张,但却因其真实而带给人感同身受的强烈震撼。

刘拓前往巴米扬路途中拍摄的村庄,他经常会在中途停下,去拍摄那些古老的村庄与生活在那里的人。他认为这些生活在古老而艰困环境中的人,比旅游者趋之若鹜打卡的名胜古迹更值得尊敬。图片出自《阿富汗访古行记》。
这种震撼不是堆砌辞藻营造出的幻象,而是言简意赅却信息量巨大的真实的冲撞。这种真实感十足的历史旅行记录的风格,当然不会随着玄奘、法显的逝去而随之消逝。但这种文字对写作者提出的要求更高,它要求摒弃那种游山玩水式的亵玩心态,全身心地投入到观察、搜集和探访的领域之中。
古与今
念天地之悠悠
虬枝如蟹爪般的参天古木下,耸立着古老的碑碣。碑座的赑屃龟甲犹存,但碑刻的文字,却已漫漶不清。然而,这并未妨碍骑驴的旅人在它面前驻足凝望,试图从残存的文字中,读出被岁月风尘湮没的那段历史。

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读碑窠石图》个中寓意众说纷纭,或以为讲述的是汉末名士蔡邕观赏曹娥碑的故事,或以为是描绘唐代诗人贾岛“古寺读碑不下驴”的典故。但画的作者李成与王晓,都曾经历过残唐五代的离乱岁月。生活在那个时代,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不亚于法显与玄奘西行的历险。半个世纪刀兵战火的反复洗劫,让现实与历史都变得伤痕累累。而李唐本是李唐宗室之后,遭逢亡国之痛,回首大唐盛世,一如画中古木下的古碑一样,孤独地矗立在那里,被岁月剥蚀,无言地诉说着早已不再的荣光。
岁月蹉跎,过往成尘,记录历史的碑碣埋没古木荒草之中,但幸好有旅行者发现了它,并且愿意驻足停留,端详记录碑上被湮没的历史,没准儿还会把它记录下来,让它重返世人眼前。李成虽然最终谢世于宋初,但他如果知道自己在《读碑窠石图》中描绘的骑驴访碑的光景,在他身后的宋代会形成一股热潮,想必会倍感欣慰。
刘敞就是宋代热衷旅行访碑的诸多文士之一。1061年,他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所长安正是汉唐故都,历史古远,因此常有古碑残碣出土。刘敞对此特别加以留心,时时发掘有所获,他“悉购而藏之”,也时常实地踏访碑刻,撰成《先秦古器图》。他的好友欧阳修,同样有读碑的癖好,“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欧阳修作为历史学者,更着眼用古碑中的记载来纠正文字史料的错漏。《隋书》中记载郎茂“卒于京师”,但欧阳修发现的《隋郎茂碑》上却刻着郎茂“从幸江都而卒”,故而“史氏之谬,当以碑为正”。他主持编修的《新唐书》中的《孔颖达传》,曾因袭前人史*载,将孔颖达的字记作“仲达”,但他后来访查到唐代的《孔颖达碑》,虽“其文摩灭,然尚可读”,从中,他不仅发现孔颖达的字不是“仲达”,而是“冲远”,更找到了史书中未曾记载过的历史,如孔颖达的生卒年月,以及他与魏征奉敕共修《隋书》的史实。“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谬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
宋代才女李清照与他的丈夫赵明诚,可以说是欧阳修访碑考史的忠实拥趸。在他的《金石录》自序中,赵明诚坦言自己对金石碑铭的爱好,就发端于欧阳修的《集古录》。待其成年仕宦后,他便“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上自三代,下讫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绝域夷狄所传,仓史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钟鼎簠簋尊敦甗盘杅之铭,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叙记之文章,名卿贤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凡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磨灭仅存者,略无遗矣”。

光绪刊本《金石录》书影。
他的妻子李清照在多年后,回忆起当年丈夫在京师太学里当一个穷学生,那年他才二十一岁,就对金石碑刻有着深深的迷恋,每每到当铺里把衣服当掉,换得五百余钱,到大相国寺前的市场上去购买碑文拓片,“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两年后,他们又出京到外地做官,虽然身处穷遐绝域的荒僻之地,仍不辍“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最终整理出两千卷金石铭文,又特意编纂了三十卷《金石录》:
“呜呼!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耳。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二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
他猜得一点不错。1127年,北宋在金人铁蹄下沦亡,他与妻子李清照也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昔日精心搜罗的碑铭拓片渐次佚散,故居积藏的金石古籍,也被金兵烧劫一空。唯有三十卷《金石录》流传后世。但这一劫火遗存,一如李成笔下的《读碑窠石图》一样,足以激发起后来者的步追踵继的向往之心。五百年后的明末学者赵崡就是《金石录》的忠实读者,他自己踏访碑刻的行止,宛如一幅活脱脱的《读碑窠石图》:
“深心嗜古,博求远购,时跨一蹇(即瘸腿的毛驴),挂偏提,注浓醖,童子负锦囊,拓工携楮墨从,周畿汉甸,足迹迨遍。每得一碑,亲为拭洗,椎拓精致,内之行簏。”
在他之后的清代金石学名家黄易,则将自己在嵩洛之间访碑的经历,绘成《嵩洛访碑图》,淡淡数笔墨痕,勾勒出两三个米粒大小的人物,站在一方古碑前,细细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