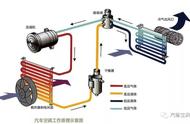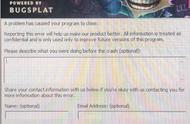作者:黎荔

在这个悠长无尽的假期里,睡了很多长长的觉,做了很多沉沉浮浮的梦。梦中,已过完半生。睁开眼睛,人还在原地。发现在地球上生活,其实花费并不多,譬如,梦境从不收入场费。
梦中,在绿草连天、野花开遍的旷野上策马狂奔,不知道要去往何方。
梦中,一不留神回到了童年,找到了儿时遗落在路上的那只鞋子。
梦中,孤独地穿过南方的长街窄巷,拐进一个街角,又拐进一个街角,再拐进一个街角,四周是弯曲的暗调。
梦中,一副雪橇飞快冲下山坡,耳边风声呼啸。

梦中,回到高中时的课堂,课桌边熟睡的女孩,安静得像一只猫。教室的窗外,高大的凤凰木自顾自花开花落。
梦见自己和一行人在一片冰面上行走,其他的人有说有笑,不慌不忙,而我走得小心翼翼,怕冰面破碎,怕猛然跌倒,一望无际的冰面,厚实的蓝冰,珠串似的气泡冰清晰可见,层层裂纹在冰面绽放。
梦见自己是海底费力爬行的海洋生物。好黑,好冷,环绕我的只有黑暗。但突然间头顶隐约有光在微微闪烁,于是努力向上蹬脚,试图触摸到上面轻轻掠过的点点微光——水波起舞,光影变幻,多想冲破水面,奈何却做不到。
梦见自己是一棵会唱歌的树,心情好了,就繁殖成了一座花园。就带着花园唱起歌,上路了。前方的路程长又长。花园里来了孩子,少女,母亲们,还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洛尔迦,卡夫卡,木心,麦田里飞来的乌鸦,善良的白蛇娘娘。

你说说,梦境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可以体验各种稀奇古怪的未曾经历的生活。人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个身体残疾的人会梦见撒丫子尽情奔跑,担心失去一个人,会梦见他的离开并且在梦中哭泣。可我觉得,并不完全是这样。我认为人的身体本身,天然有产梦的机能。一副健全的身体,必有梦的诞生。在生理健康、精神完善、想象力未曾丧失的身体里,梦的源泉不会枯竭,就像孩子可以对着天空,吹出一群群晶莹剔透的肥皂泡泡。
梦中的我们,宛如一撮被泡得舒展开来的茶叶缓缓沉于杯底,透过狭窄的透明张望这疯狂世界。梦境在现实的彼端,那是一个不可解释的广袤世界,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超越时间、跨越空间,与层层叠叠的无限境界相连结。梦境的世界,与我们这个真实世界是相通的,那些在梦境中存在过的态度,反应,角度,目光,表情,印象,心情,信念,幻想……不一定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能还将暗暗生长,扩展着地下的庞大根系,无声无息地,潜入我的似水流年。

在梦境的朦胧小路上,我去寻找我前生的爱。
他的房子是在冷静的街尾。
在晚风中,他养的小狗在庭前打盹,鸽子在自己的角落里沉默着。
他把灯放在门边,站在我的面前。
他抬起一双深眸望着我的脸,无言地问道:“你好么,我的朋友?”
我想回答,但是我们的语言迷失而又忘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