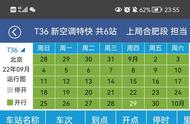豆沫,是沂蒙山区特有的一种菜,做法极简单,主料无论是山野寻的、田里种的统统以豆面熬煮,便成了。这个过程当地人叫“馇”(cha),我一直以为这是个方言,后来查了字典才知道,竟是标准读音,边拌边煮之意。
过去那些年,日子艰苦,粮食紧缺,菜更是奢想。但贤淑的主妇们总能想出办法, 开春,去山野里寻来的苦菜、婆婆丁等野菜,热水焯烫,去除苦味,便是馇豆沫的上佳食材;秋天,地里的地瓜秧、萝卜秧子等晒干储存,这也都能馇豆沫用。节省点能吃一冬。
母亲总是竭力满足着全家人的果腹需求,冬天的最后一场雪刚融化,大地上需要仔细看才能找出一丝绿意,母亲便挎着筐头寻菜去了,那时的山野不像现在野菜多的都抽薹开花,寻菜的人也多,需要走出很远很远。当夕阳为母亲娇小的身躯镶上一抹金黄时,也是我们姊妹最快乐的时候,几个人抬水、洗菜、拉风箱生火烧水,叽叽喳喳一团乱。母亲则疲惫地倚在低矮的院墙上,用头巾掸去身上的尘土,看着我们这三个一溜挨肩要吃要喝要上学的姊妹们,眼里充满了疼爱与期盼。我也是过了多年,为人父后才理解了母亲当时的眼神。
帮忙也好,添乱也罢,最后母亲总会出手把一切理整得有井有条,等野菜烫洗干净,剁碎下了锅,老人家便会郑重的从柜子里捧出一个瓷坛,试探着倒出一小把豆面,匀和的洒在锅里,随着热气的升起,馋人的豆香弥漫开来,瘫在床上的奶奶闻着香味,含混不清的嘟囔起来:豆面又搁多了,省着点防贱年,豆子能揽菜。沂蒙山区的主食是煎饼,难咬得很,特别是放陈了的,能拱的太阳穴疼,但卷上豆沫,立时就大有改善,既中和了菜的苦味,又使得坚硬的煎饼松软许多,这也许是一物降一物的一种吧。
地瓜秧则要在白露节气前,还没长出硬筋时采集晾晒,萝卜秧却需要在立冬以后去帮种菜户出窖子、拔萝卜来换得。母亲总是辛劳的操持着,一家人清贫而又恬静,就像这用野生的、畦种的,抑或是捡拾的各种食材馇豆沫一样,只要加上豆面,就有了灵魂,滋养了我的人生。母亲就像这能揽菜的豆面。
我上初中时,还是招冬季生,每天带的饭便是一包卷了豆沫的煎饼,豆沫是母亲用油葱花犒炒了的,尽量干嗦些,方便保管,一次,母亲把给我们准备的油炒豆沫给爷爷盛了一碗,爷爷却只尝了一口,便到给了我最小的妹妹。转头叮嘱母亲:这菜只能学生娃吃,大人吃这得多搭上好几个煎饼,糟蹋粮食。这时的我,已初涉世事,我知道,爷爷不是小气,更不是疼这碗豆沫,还是穷呀。
豆制品极易变质,开学不久,天就热了起来,早上带来的饭,晌午就馊酸了。吃学校的食堂是要交小麦这样的细粮来换馍票的,沂蒙山区本身就山多地少,春田居多,小麦是极稀罕的,瘫在床上的奶奶都很难吃上几回,还要人情往来换馍馍出门和待客。爷爷得照看奶奶,母亲便担起了中午给我送饭的活,从家到乡里,单趟五里路,要步撵一个小时,我上了四年初高中,娘亲风雨无阻送了四个春夏秋。豆沫用搪瓷缸子盛着,外面总是要用包袱仔细包裹着。每当我走出教室,看到娘亲矗立在骄阳下或和风里的身影,总是鼻腔发酸,娘亲捧在手里的不仅仅是一碗可以充饥的豆沫,而是一个母亲的期望和疼爱。
母亲从来不善言语,我也总是默默咀嚼着,但我知道我嚼碎咽下的是娘亲的心。
带着母亲的牵挂,我在外匆匆上了两年大专,便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来任教,依当时的安置政策,大专毕业生是留在县城的,但我毅然申请回了家乡,因为离家近,离含辛茹苦养育我的娘亲也近。
上班的第一天晌午,下课铃响起,当我走出教室,眼前的一幕让我潸然泪下:母亲一脸微笑地站在秋日的阳光里,还是原来的地方,手里还端着一碗豆沫、拿着两个煎饼。这就是我的母亲,无声却又满心里都装着儿女的娘亲。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母亲今年85岁了,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认知能力非常差,不认路也不认人,我退休后在家陪护,老人每天都要重复好几遍的话就是:今晌馇豆沫,多放点豆面,儿女们喜好。这!母亲真的没忘下。
这碗豆沫,端起的既是昔日艰辛岁月,更是对母爱永远的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