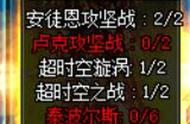董卿的个人特点一直在不断放大。精妙而细节化,在一个个或热闹或简淡的采访、晚会中跳出来,渐渐形成她风格化的语言。带一点思想性,开放式,使人施展想象力,她的语言能带人翱翔很远。采访录音自连成文,有意隔绝了“水词”。“我希望能够达到干净、漂亮到几乎可以书面化的语言,但是又不让人有隔阂感。”
主笔/葛维樱
当描述一个人时,她的一切都在说话:微微倾斜的姿势,能瞬间泪目又能含住眼泪的眼睛,好像总也言之不尽的嘴唇。“所有的风格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天天一年年的累积也不明确,甚至很多时候,经历了很多黑暗和迷茫,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条路上走了,才慢慢地看到一个光亮,才找到了那个方向。”
大时代里的朗读者们“我看重的人,他偏偏不看重电视,不愿做热点。”这一季《朗读者》现场朗读的嘉宾有143位,而真正接受董卿采访的嘉宾是60位。从1月份录到最后一个在长城上走路的镜头,董卿始终惦记着采访对象。她惟妙惟肖地学张弥曼温柔地拒绝自己,这位不久前在世界女科学家颁奖典礼上,用法、俄、瑞典语和中文致辞的82岁的古脊椎动物学家说:“董卿啊,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欢你,但是我们不会来录节目的,我要带福睿斯去野外考察。”

董卿(黄宇 摄)
董卿追一个电话,再追一个,终于发现对方有点动心了。说服贾平凹也是她今年最得意的事之一。先是在文联大会,贾平凹说:“我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朗读是丢人现眼。”她给他女儿打电话,再通过出版社出书的编辑,找出版界的领导,想尽了一切办法。贾平凹依然硬气,来了只谈书,董卿心想“上了台就听我的了,哈哈!”,于是聊了两个多小时。她聊起自己的采访对象一脸的得意、倾慕,热爱着与他们交锋的每一分钟,尤其是那些让她“为难”的人,但“我喜欢的就是他这一点”。
越来越难以取悦的还有观众。“这个时代自制视频已经泛滥,传播没有门槛,一打开手机,鸡汤、励志,文字千千万,我们读什么?”董卿说,站在推荐者的角度,她从一开始就觉得恐慌。浙大数学系的蔡天新读过一篇蒙田的《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我们知道的知识,跟我们的无知相比,仅是沧海一粟”。这让她不断审视自己,“你有没有找到真正好的东西?”。
“我对语言非常非常热爱。主持人被称作吃开口饭的,我已经做了24年。你可以说一些很流利但却完全不会被记住的话。一开始不会察觉,慢慢地就有一个觉醒的过程了。”她做这一行做到很后来,才发现把话说好听,是一件没底的事。“那个话还能说得更好,能瞬间让人泪目,或者瞬间热血沸腾。刚开始我也只认为语言是工具,后来才知道语言是艺术。”

董卿主持《朗读者》
无论《中国诗词大会》还是《朗读者》,都出现在真人秀、歌舞节目被观众看腻了的时机里。董卿对此非常清醒,“正好是知识需求、阅读需求的机会,我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直到现在,她每采访一个嘉宾,上台之前还是紧张得手心出汗。“深呼吸。”作为制片人她前一秒还在疲劳和焦虑里,下一秒就要云淡风轻面带微笑,她说:“我不是机器,一换频道脸就变了,我还是个比较真实的人,我希望笑容是真实的。”别人不理解她,20多年主持人生涯里,董卿本人就是“大场面”的代名词,而且《朗读者》又不是直播节目。但她确实累到对团队说:“我觉得我上不了台了,我怕我显得不够美好……”
文化电视节目一度进入低谷,2016年以后恰恰迎来一个小高潮。虽然电视始终被认为是快餐文化,到今天已经鲜有新奇了。“传统媒体里必须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传递最精髓的文化。”文学、电影,靠的都是一个人文的内核。可是到她手中“人文”到底要表达什么?她要的不是访谈录,不是纪录片,也不是艺术人生。尽管听董卿讲故事是一件极其有画面感的事。她给我讲了一个住在云南巴拉格宗大山深处的普通人修路的故事,他10岁时因为被铁水溅到眼睛,走了五天山路才出去,虽然瞎了一只眼,却看到了电、灯、汽车。“他的一生都改变了。”董卿讲他如何拼命挣钱,如何忍受乡亲的唾骂,如何想象父亲坐在副驾上一起在这条路行进。然而父亲却在公路修到最后一公里时离世了。
董卿选择了一种看起来危险的方式,用带着一点狂热的情感讲述,我想她本人应该比其他人更受这种激情的席卷。采访这一天,我早上6点半收到了她的*“熬了个大通宵,采访改在1点好吗?”她的泪点非常低,这一天是《朗读者》第二季收官之夜。从去年7月到今年8月,又是一年的不安和焦虑。特别是后期制作阶段,“在别人的美梦中,我看着机房的玻璃天花板渐渐透出天光,又一天生命流逝了”。
活的语言,人与文本的桥梁做《朗读者》第二季之前她很犹豫。“怕没有第一季那么好。”盛名之下,她承认“做这一行,总希望被认可、被赞美”。直到她采访94岁的肝脏外科大夫吴孟超。“他86岁的时候接到一个谁都不愿意开的病人,肝部肿瘤重达9斤,女孩20岁出头。吴孟超看了愿意亲自动手术,护士长拦着:他万一开坏了,这晚节不保。‘我的名誉算什么啊?我不过就是个吴孟超,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董卿在采访时眼泪直砸。
她保留着专业领域所能容纳的感受力的最大化,“这个特质挺好的,虽然我小时候为自己的‘易感’难为情”。她描述自己小时候看到电视里一个受冤枉的黑人被施以电刑时,依然惊恐。“职业总是磨灭很多个人的东西。尤其主持人这个行业很消耗,不仅体力,还有情感的消耗。”
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在划定界限,把自己能量的一部分用来框定自己。勤奋、毅力和对自己能力的持久信心,使她不停地想出一系列情节、细节和画面。今天的视觉要求已经随科技进步,“阅读”的形式感开始被看重,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对文学作品的表达上,而不是放在文学作品本身。在和她一起工作的人看来,她就像罗马士兵一样,每次停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挖战壕。“我看事物就是一条抛物线,规则就是达到顶峰,下滑。”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场景,每一段讲述中,她都带着一种确定和持续的决心,从不左右踟蹰。毫不留情的胆量,在电视和镜头语言已经成熟到今天这个程度时,仍可以开辟新空间。“画面为什么暗,停顿一秒还是一秒半,音乐不行。”她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工作里:对于美感的需要,精微的道理,和对自身越来越高的风格的要求。 “起初形态也不清楚,是先读再聊,还是先聊再读,还是边读边聊?”摸索的过程中,她的导演讲了个自己的故事,说小时候家里养了一只大狗,特别喜欢,后来那只狗老死了,她弟弟自己去埋那只狗,弟弟很瘦弱,穿得很单薄,雪花飘在他小小的肩膀上,那个肩膀在抽泣。讲完了所有的人都掉了眼泪,然后她读了一篇小男孩养狗的故事。《朗读者》的模式,在这样每天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里的演练里,逐渐清晰。
帮观众度过生命中宁静的时刻的,是故事和人之间的空隙。在其中,形成了人与人、人与作品之间的交流,发展出了另一个倾向,进行更持久的延续。特殊经历和天赋异禀综合在过去的文学作品当中,一个当代的诠释者,提供的空间显得非常明确。每个词,都有一个新的意义。加诸每一个个体的故事,这样一直叠加,直到语言停止。每一个主题词都分了四五个不同的层面由不同人诠释。
“把那部分东西唤醒。”戏剧性的架构,真实的人物性格,洋溢着感性的对话场景,没有表演的表演。今年最触动她的是余华。余华对于“故乡”的理解,和他对想象力的运用,在细节、风格、架构和图像、隐喻的光辉里使用。尽管只在忠实描绘世界的一个短短的篇幅里,将事物的本真状态,真实呈现。
“他引用了马尔克斯的一句话来形容他和故乡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最后一期节目主题词是故乡。他说,父母神奇在哪里?伟大的马尔克斯告诉你,父母健在,我们和死亡之间隔着一层垫子。父母不在了,我们就直接坐在了死亡上面。”
主流的文学虽然存在,却过于遥远,缺少了和谐、普适的表达方式,现代的传播中,缺乏有表达力的声音,人的内心世界,理智膨胀,内心迷茫,缺少适合那些天才们的诠释者。
谁有能力用寥寥数语,抓住事物的整体?第一季里翻译家许渊冲念着情诗,用过往的丰盈,古老岁月和原始的文学,以叙述的语言进入了一种安详的平静之中,让丰盈的情感细水长流。这也是董卿说“我爱这些老人”的原因,许渊冲面对镜头瞬间的热泪盈眶,让她被击中,“还拥有那样动人的光华”。
她给第二季加入儿童侵犯、器官捐献、生态保护这样的话题,加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海明威的《真实的高贵》这样的文本。“可能不那么讨喜,不能一下子被传播。”她花了很大力气让文本和人的结合度更高,依然觉得自己有“没遇上”的遗憾。
选择文本,是她的文学组的工作。有时最后一刻她还在挑剔有没有更好的读本,“心里会想看老天给不给吧”。“大家已经觉得谈情怀很虚无的时候,你还去挖掘一些真的情怀。因为这世界一定有那样一些人值得我们相信。”戏剧性描述的天分,是在文学上使观众崇敬和欣赏的能力,也是朗读时不断给读者希望的能力。
确信语言中存有真正的美感,董卿才敢诉诸简朴的风格。贾樟柯讲到故乡这个主题时,已经有了隔岸观火的柔软,不再有被人猜中内心痛苦的生硬,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在45岁那年又回汾阳去。“当初哭着喊着从汾阳逃出来的一个孩子。2006年他父亲去世了,北京的合伙人陪他一起回老家去料理后事。虽然关系很好,可他能感觉那种生疏,合伙人有点害怕。他就说乡俗太多让对方回北京吧。在守灵的一个又一个很冷的夜里,那些他曾经觉得最不重要、失去联系的儿时的小伙伴全都来了,有话没话地聊着,那么自然从容,陪着他面对生死。”
一个导演的日常想法,来自于他们的自我审视。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成长、成功、失败、失望和痛苦的秘密。把语言自然而人性化,实际上非常困难,常见的问题是,一旦触及哪怕是当下的名人和名著,语言就变得残酷无情、相信宿命。而董卿在这些人物遇到的真实感情面前从未退缩,她毫无顾忌地表达它们,探寻语言叙述中人的意味。有时隐藏起来的秘密经历更深刻,更真实。当它时而远去,影响更大,让读者相信了它的存在。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讲完故事,语言就是自然流露的,有血有肉。文本的容纳能力更强,因为语言而变得有机了。
不断跳出舒适区带着对文本的热情和真实表述的需要,她这几年被“知性”的评价包裹。在生活里,纤细、柔弱、女性化这些特征被她刻意摒弃,更愿意在团队面前树立“绝对理性”。董卿并不刻意追求新奇,她让朗读者们,带着一种新的魅力,温柔的泪,抚摸早就熟悉的思绪。
从浙江省艺术学院到上海戏剧学院,从话剧团到电视台,从杭州到上海,这期间她在不停更换自己的职业和学业的跑道。她内心深处曾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失去。“话剧团演员,一个月100来块钱,我毕业是90年代初,正是全国话剧最不景气的时候。”几乎在30岁之前,她在为自己果断做出判断和选择,从不惧怕从零开始。
“每一次的改变,都很痛苦,但我的判断又告诉我,可以去做。”她的每一次转变和跳跃,往回看都是冒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都是后知后觉。“如果真的能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掌控,生命本身的魅力也会减弱的。”
但是在40岁到来的时候,她却困在一种僵局之中。她形容那是一座山峰的顶端,而自己要选择,下来,重新攀爬另一座山。“其实每一次都是一次艰难的巨大的考验,我知道放弃了什么,可是不知道能得到什么。”这句话她说得有些唏嘘。
2016年2月份,董卿以制作人身份提交了《朗读者》的节目企划。她可以只做主持人,当时的《中国诗词大会》正是董卿从综艺主持向文化节目主持转型的成功之作。她的语言,透露出的阅读量和表达力,受到了非同以往的关注。她把《朗读者》比喻成自己的孩子,守着它从孕育到出生,不舍得交到别人手里。
“单打独斗”是她过去的习惯,做主持人允许她工作的纯粹。“准备好,上台,说完,接受掌声。”但一个社会化合作项目的制作人需要把控整个制作链。“过去20多年里我没这么舍下脸去求人。”她形容自己最初的状态是“一个念头,两页策划,三个散兵,四处磕头。”
从主持《诗词大会》到转型文化类节目的制作人。“我并不擅长台下的沟通和联络,可能内心还是比较骄傲的。之前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拿命换来的,吭哧吭哧一台台地做,最多的时候一年做了132场节目。不同地方,不同主题。所以那段时间不是在台上讲话,就是在台下准备讲话。除了刻苦我不会用其他方法去获取机会。”为了《朗读者》,一年里她几乎见了几十家“有意”赞助的资方,每每自己说得口沫横飞,却只在结束时换来一句“我们合个影吧”。
现在她觉得人生进入了下半场,“才知道每一步都不白走”。话剧演员“声台形表”的训练,让她对站在台上有了笃定。
“从上场口出来虽然是侧面,但是你的头要留多少角度,让所有人知道你看到了他们,几步之后你转过来,那一刻就是站定。一个好的主持人,是敢于站定的。好的演员和主持人,可以不开口,空白是最考验一个人的,台上的几秒钟,你的身体,你的表情,你的眼睛都在告诉大家‘我有话对你说’。”
她气定神闲,不需要更多“抓手”。“语言节奏不是遣词造句的问题,而是用停顿来表达。”演员要说台词演人物,但主持人要的是主动的自我的表达。2004年,“选秀”才刚刚开始,真人秀节目还没起来,青歌赛是中国最严肃、最高级别的歌唱比赛舞台,本来没有给主持人留下太多空间。“就是报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然后在余秋雨和徐沛东那个文化素质考试的环节里说,请听题。”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董卿主持的青歌赛这样的“常规”作品,却给人留下了非常规的印象。她每天下午1点进场,听彩排,采访歌手。“为什么要和你聊?晚上要用吗?”选手常常质疑。“我说可能会用。直播中我会酌情附加一点背景信息,他从哪里来、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性化的东西。”准备几个小时,出镜用到的不过几分钟,她得取舍。“是要看着美美的,还是要顶着个黑眼圈?”
晚会主持人可以用的“空间”很小,但是董卿有她的笨办法,“能先采访一定先去采,采两个小时说几句话,和直接说几句,这个效果肯定不一样”。她记得公安部的晚会,每个英模有几万字的资料,全看完也就一人提两个问题,就那几分钟。她的提问点自然不一样。“用唾沫星子,一点点搭一个燕子巢”,她这么形容自己得到了导演们的信任。“有些人说春晚的本子不能改,但是导演跟我说,‘这个人物怎么放,你去了解一下’。等于给了一点角色给我。”
去美国做访学是她为自己人生做出的最大的转变。她已经站在中间太久,“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觉得应该这样”。但她很明确自己的不满足。“如果我还在台里,没有出国,那么我还在不停重复。”办好了手续猛学英语的几个月里,她其实一点也没有自己设想的那么淡然。“经历了心里的跌宕起伏,一种失去的痛苦,积累了20年的东西,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不知道能得到什么。”她平时电话也不多,但当时真的没有电话打扰她了。
虽然对于出国她已经做了最大限度的心理预设,但当最后发现自己的优势被击得粉碎时依然恐慌。“我是靠说话吃饭的,语言是我最擅长的东西。但是这里,没有人知道我表达得多好,相反语言障碍使我成了一个不敢表达的人。”周围是比她小一半的年轻人在飞快地打字记笔记,等自己打好腹稿,这个问题早就过了。
“素面朝天抱着书本去图书馆”这种幸福的设想,变成了现实里的艰难时刻。原以为海外游学的日子可以过得比国内悠闲一些,没想到还要沿袭熬夜的习惯,才能对付教授的问题。当然也有收获,有很多和好莱坞制作人交流的机会。
那段时间,最痛苦的不仅仅是学业带来的压力,她觉得自己失去了自己最引以为豪的工具——语言。她对语言的热爱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天赋,另一方面则是“这个东西没有底”。
董卿说,语言和任何艺术一样,追求的是走向人心。“我去看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天鹅湖,当白天鹅出场时,为了表现纤细和善良,她连脚指头、背影都是颤抖的,我一瞬间就泪目了。”她欣赏陈道明和何冰的话剧《喜剧的忧伤》,“每句话的节奏都带快了观众的呼吸,而后面的叹息又让人跟着感叹命运”。一旦把语言视为终身的目标和追求,董卿的努力不再以环境为限制。
笨功夫董卿的家教是网上热议的“虎爸”标准。复旦大学毕业的父亲和母亲,一起分配到安徽濉溪县“五七干校”,“在那儿有的我”。安徽条件太苦,董卿一出生就被送回上海条件较好的外公家寄养。现在她看到父母帮自己带孩子,才体会了那种隔辈的爱。“就是他怎么做都对,怎么爱都爱不够。”她从小和20来岁的舅舅们一起玩,小萝卜头的童年过得自由畅快。现在网上很多关于董家父亲严苛的故事。看到母亲读书的样子觉得美,是她儿时对文字的初始感受。
“必须看这个诗,必须抄这个成语,父母当年的教育没有这么温婉。”她的“小鸭脖子”台灯下面每天贴10个小纸条,是父亲要来检查的功课。“当时孩子的信息接触面很窄,电视网络一概没有,信息的获取,只能而且完全靠书。”她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写到了“回维也纳”,以为这也是一个成语,于是抄了下来。
董卿却很直接。“当年父亲的严苛确实塑造了我,但一定程度上我的不自信,也来源于那个时候。”她说,自己长得像和爸爸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是言谈举止,甚至和爱人相处的方式,都会越来越像妈妈。
她觉得自己不属于“侃侃而谈”的类型。很多年前就有人不断找她出书,说她可以说的事情太多。虽然《朗读者》的电视文本书销量达到了150万册,但董卿一直拒绝给自己写。“对文字我有敬畏感,不敢轻易做。”书在她眼里实在太神圣。每天阅读一个小时是她不焦躁的根源,做起节目来的几个月,这种阅读被强制挤占。
“下意识里,我被父母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我很少听到表扬,都是应该这样。”她说,儿时对文字的亲近感来自于毕业于复旦新闻系的父亲,而父亲感兴趣的是历史,她真正喜欢的是母亲喜欢的西方文学。
“条件很有限,没有专门的书房,但是却有包书皮的习惯。这是一件挺严肃的事,也是一个很愉悦的事。”大学以前把经典大部头都看了一遍,中学时代“自我教育就是在读书里完成的,现在这种阅读变得有了功利性的作用了”。大学开始看很杂的书了。知性是这几年开始慢慢地附加在她身上的形容词。“我也不是突然就变得知性,而是慢慢把一些好的习惯放大。”读书在董卿看来“不是事儿”,更不值得炫耀,只因为自己从事抛头露面的工作,容易得到鼓舞和激励,“有了一个绽放的舞台”。读书对于需要表达的人,真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比起更多喜欢看书但从事一般行业的人,她觉得自己只是“容易被看见,影响很多人”。
她要找一个与自己相契合的形态,如果没有就自己创造一个。
每一期《朗读者》,她写的“札记”在网上流传成了“范文”。她并无幽深的表达,属于现实的美感,洋溢趣味,回应人的诉求。这些词句包含了她思考的愉悦,温和又带着轻微的古典气息。
“长久以来的学习给我带来判断力。知识也好学问也好,人怎么样更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和外界相处,怎么和自己相处,我阅读、观察、思考的东西,都在帮我达成这个目的。”
我说文学是黯淡的,董卿不同意,她说它“不夺目”,“但其实真的有光,我自己一次次被感召、被照耀过”。她说起某篇文章还会起鸡皮疙瘩,聊到采访对象会激动。“文化本来就不是热点,以后我还敢不敢舍了命去做?”她倒自言自语起来,“我与文学互相借力。只要我自己能被打动,这个东西就能感染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