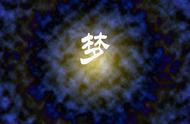◇ 曹婕妤
我生在水陆南方的一座小城,喜欢打量来往熙攘的人群。
出生那天,正是年前。公鸡的鸣叫划破清晨的宁静,护士从妈妈的大肚子里熟稔地掏出我这个胖娃娃,外婆戏谑道:马上是除夕,小家伙这时辰着急出来凑热闹呢。她不紧不慢地帮我计算出生辰八字,不料第一下就两难了,我的生肖按农历推是属鸡,按阳历算又是属狗,当然,五行先生都参考农历。
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妈妈发现外婆的玩笑话就像一场预言,我就是个四处蹿腾、既有公鸡的骄傲又有小狗的柔软的胖姑娘。想到这里的瞬间,她不禁为我的体重黯然神伤,埋怨爸爸为什么要在她*的时候爱上炖鸡。没多久,她就下定决心弄根腰带回来,天天给我束在腰腹处,曾一度严苛到不准吃糖,甚至甜甜的水煮玉米也不行,妈妈美名其曰帮我减肥。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初具对胖的模糊概念和对瘦的无奈,小姑娘的童年丧失了糖果的清甜,一如必须在酷暑穿着长长的衣裤那样难受。
两三岁的夏,妈妈是不会让小孩子吹空调的,主要怕凉了骨头。于是,每个中午我耳边都回响着老风扇拼命转动的声音,机械小马达拖着边缘沾满灰尘的旧扇叶,像十字路口老妇人蹒跚踌躇的步履,吱呀吱呀,细碎而绵长。我常常一觉醒来背上湿哒哒的一片,手心还攥着揉得皱巴巴的零花钱,迷糊中爬起来走出小房间,茶几上是新鲜的刚切好的西瓜,妈妈起身把我的毛巾打湿,拧干,我便只觉眼前一黑,紧接着是毛孔受刺激后扩张的凉意,而用力抿紧口鼻是因为脸颊被擦得生疼。实在受不了了,便快速挣脱妈妈湿热的手,撒开脚丫跑到外面去。能在常去的商店偷偷买到最馋的冰棒成为我每天孤独仰望又近在咫尺的事,撕开包装纸后会有几丝袅袅的白气上升,我手忙脚乱地凑上去吸两口,坐在泛黄的冰柜边,避开刺眼的白太阳,像小痞子一样瞅着街道寥寥的行人经过,习惯眯缝着眼,直到全部吃完才心满意足地挪回家。
因为这种类似男孩子的不羁与洒脱,我妈再次下决心给我那头齐耳的小丸子发型剪成利落的短发,索性放任孩童的天性。
时至今日,我仍然怀念这些糅杂在热风里尘土飞扬的汗水味,混着香甜的奶油和化掉的汁水,却再也回不到那种仅仅站在冰柜旁都觉得快乐的单纯。比起商场里泛着金光的牛排和镶满碎钻的鸡蛋,似乎这些逝去在长河里落满尘埃的小事更令人心安。
我家住在一条深巷中,挨家挨户的小朋友几乎都是男生,他们常常成群结队,一起坐在废弃的水泥乒乓球台上,叽叽喳喳地品尝各自带来的麻辣和汽水;去掏路边的花泥做成泥珠,放在弹弓上到处搞破坏;爬上很久没人住的矮房子,在那块平整的水泥屋顶蹦来蹦去;嘻嘻哈哈地打着赤脚在小路上肆无忌惮地疯跑……其中一个小男孩的父母租住在我家一楼,一般晚饭后我都慵懒地把身体埋进沙发里昏昏欲睡,电视上播放的新闻联播像一剂枯燥无味的催眠针,落日的余晖悄悄覆上我流着口水的侧脸,轻轻染过一层黄昏的房间看上去更加昏黄,一切宛若油画般的美好却不及一声猝不及防的哭闹,大概是又有什么人跑来跟他父母告状吧——一楼那个小男孩挨打了。
邻居们都很羡慕我爸妈生的是女孩,乖巧柔顺不说,最重要的是不必让大人担惊受怕。当小孩最悲哀的,是无法意识到性别的双重属性,男孩们的顽劣更多的是对英雄主义的盲目崇拜,女孩们则徘徊在心底的秘密花园,幻想能无所顾忌地勇敢任性一回,而现实是,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在这种彼此遥望的弱小里匆忙长大,平淡如水,没有屏幕里的怪诞夸张。
小孩子都喜欢往人群里钻,不想永远只跟洋娃娃和小熊说话的我也渴望人群。幼儿园中班快结束的时候,像突然有了勇气,推着我大胆走近那群男孩,紧张地拿出刚买的冰果冻。一楼那个小男孩歪着头问:你是不是住楼上的小姑娘?大人们说你可听话了,老师说好孩子不会喜欢坏朋友,所以你从不跟我们玩对吗?我卖力地摇摇头,晃得耳朵有点麻,他上前一步用稚嫩的脏手揪住我的衣袖,吸着鼻涕说:我告诉你,你的果冻太少了,明天再多带一点,知道了吗!旁边块头稍大点的小胖墩从我手中一把夺过塑料袋,他的胳膊上借着袖子藏着几条伤痕,我看得有些心慌,想起小男孩的爸爸曾经也是这么恐吓他: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惹事我们就生小姑娘去,不要你了,知道了吗!
大人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对我们说过的每句话,好听的都会变成露水,润泽爬满丘壑的心田,难听的最后成为鲨鱼,在心里偷偷长牙,直到未来有一天我们无意识地把它带给另一拨人,继续着曾经的伤害。男孩们的背影在我眼中渐行渐远,小胖墩身上已经结痂的伤却像带刺的枯藤,在我的神经元上逐渐蜿蜒明晰。
第二天上午,我扳手指做计算题的时候特别认真。因为爸爸说过,全对奖励一元,错了就只有五毛钱。尽管再用心地扳手指头,可爸爸检查完还是发现有个题目算错了,他往我的手中塞了五毛钱,我感觉心脏都空了,急得直跺脚,眼眶噙满泪水,喘着粗气把钱不够买果冻的事一下全说出来。爸爸捂着胸口狂笑,五官搓成一团,我几乎担心他的鼻子被挤得还能不能呼吸。他一脸宠溺地伸出手,我泪花闪烁地接过崭新的一元钞票,觉得心脏又不空了,开心地在心里默想:妈妈你快叫我吃午饭睡午觉呀,要是我下午能拿出十颗冰冻的果冻,男孩们一定会很兴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当朋友了,啊,世界多么美妙。其实那个中午我早就乐得合不上眼,躺在吱呀吱呀的老风扇下,一点一点等着时间慢慢捱。
下午可算盼来了,十颗冰果冻在塑料袋里冒着凉凉的冷气,我蹦蹦跳跳地来到昨天的地方。烈日炙烤着大地,知了在枝桠间鸣唱,阳光透过树枝洒下斑驳的碎影,闪闪亮亮的,晃得人眼花缭乱。我在路边站了很久,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慢慢焦灼起来,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止不住地滑过脸蛋、往脖子里钻。果冻们开始融化,塑料外壳上已经涔出一层细密的水汽,我拿起一颗化得最快的撕开往嘴里塞,坐在路旁的树荫里边等边把它吃掉。我尽量咬得很慢,鼻尖上挂满汗珠,虽然不时起身到处看看,好在果冻的冰凉和清香让我的心情渐趋平静。
他们终于出现了!我一把抓起装满果冻的塑料袋跟上,楼下那个小男孩一眼认出我,冲小胖墩打了个招呼,他们就像一只只灵活的老鼠一样四下里逃窜,有个人还回头冲我吐舌头。这些奇怪的动作让我瞬间明白了他们的捉弄。这种感觉像是你掏出一颗鲜活饱满的心脏,高举过头顶,任阳光曝晒雨水冲刷,执意要向一群不可能接纳你的人们奉献出真心和诚意。愤怒与羞辱齐齐涌上心头,我气得只好哭哭啼啼地把剩下的快散尽冷气的果冻一口气吃完,快走到家的时候,牙齿都疼了。
窝着一肚子无处释放的敌意,我告别了四岁的稚气,备受打击地进入了大班。而这一年,我的生活掀起了一场海啸。印象中都是老师跟妈妈在控诉,而且专挑家长们来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把我在学校犯下的罪行如数家珍地例举,最常见的是在班上打男同学。别家小孩的父母在旁边听得直砸嘴,有些家长跟我们住在一条巷子里,回头就是他们憋着笑问妈妈你家小孩以前不挺乖的吗。妈妈脸上赔着笑,和老师反复说着不好意思麻烦老师之类的客套话,转身便绷着脸,连拖带拉地把我拎回去,一到家便抽出藏在门后的树条。那是一种从捆满枯树枝的扫把上拔下来做成的专门打我的利器,回想起一路上妈妈正努力压抑着的怒气,我哇地一声吓哭了。奇怪的是,妈妈每次抽我抽到好不容易气消的时候,她都会用颤抖的手把那把树条扔得远远的,等到下次要揍我时,爸爸又帮她重新捆一小把新的。三番五次之后,阳台的枯树枝扫把逐渐消瘦,已经失去原本作为扫把扫地的功能,变得像外婆的小院里收起来的那摊当柴火用的枯枝燥叶了,而我埋在心底像小种子一样慢慢破土发芽的小仇恨,从戏弄我的小男孩们身上转移到老师这里愈演愈烈。
在幼儿园里,我们班和邻班都是共用男厕和女厕,午睡前大家都要由老师带着一队队轮流上厕所,不然一个班总有那么几个傻大个儿会尿床。在大家排队上厕所时,我灵机一动偷偷躲在小床底下,然而悲剧的是,在这点不够用的智商领导下,我没排尿导致那天中午急性尿床,老师用眼神恶狠狠地盯着我,气得浑身颤抖,连声音也变了调:这周你的点心全部没收!
碰巧的是那天的前一晚,我又被妈妈打了,小腿还残留着几条纹路杂乱的小毛毛虫一样的痕迹,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简直濒临窒息,伸手朝老师脸上打了一下,周围的小朋友迅速聚拢来惊呆了,女生们用手捂着嘴尖叫,男生们屏住呼吸望着我,老师愤怒地跑去办公间翻我家的电话号码,隔壁班的老师也闻讯赶来,一时间大人小孩都慌了。
我被一群乱糟糟的小孩用谴责或崇拜的眼神围着,神经元上的每一颗细胞都在自动回播老师给全班发点心的情节:大家被一阵急促的声音叫醒,一骨碌穿好鞋子走下床,迷迷糊糊找到写有自己名字的小板凳一声不吭地坐好,调皮点的小男生就在你后面扯你头发。只有当老师从柜子里拿出一大袋小花片、数字或动物饼干和小糖果时,才是全天大家最安静的时候,我们躲在心里悄悄告诉自己:不能讲话哦,吞口水也不能发出声音,只要好好表现就能多分得一些。老师提着食物袋从每个对点心充满期待的孩子面前走过,每人分发到手的也刚好是一手握的样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眼巴巴地看到那些一直都很听话、家长打过招呼或是本身长得漂亮的都会多拿一些,像我这种老师的眼中钉则只能仰天长叹,从来都没有很多只有更少的份儿,用她的话解释就是你们这种平时表现不怎么样的,关键时刻还想装乖讨巧我能看出来,少给你们发点是对你们的警告,那多出来的奖给表现好的小朋友。即便如此,我依旧在每次老师经过我身旁时,默默祈祷她能够善心大发多给点,中午做梦都是女巫给我送了瓶可以让老师的手,在只给我发点心时悄悄变大的魔法药水,而无力改变的现实还是令我止不住的悲伤失望。没开玩笑,小孩也是有情绪的,该难过的地方,忧伤的情绪一点儿也不比成年人少。
这次冒犯老师的风波过后,结局以我转到别的班惨淡收场。走的时候,我看到老师的眼神里闪烁着十万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妈妈拽着我的手紧急逃离事故现场。
初到新的班级,新老师是妈妈的老朋友,她温柔地把我搂在怀里,往我的口袋里塞小饼干,还轻轻伏在我的耳边,说我穿小红裙的样子真好看。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妈妈开始给我套上齐整的白衣小裙子,她希望服装能束缚我正值孩提时代的顽劣,让我至少看上去不再像只没头没脑的小豹子上蹿下跳。我在眼前的新老师,面前渐渐放松了警惕,甚至有点儿谈得上喜欢她了。那一整天我安安静静地坐在讲台边,她身上散发出好闻的肥皂水的香味,像外婆身上熟悉的味道,她还给我讲好孩子的行为守则,也是我第一次完整地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多么粗鲁无礼。放学时分,妈妈早早地出现在教室窗台边,用猫一样锐利的目光追寻我,我十分羞愧地低下头,捏着脏兮兮的衣角,蹲在讲台下面空落落的角落里,直到她呼唤我的名字,才腆着脸爬出来。
一路上,我们默契得没说一句话。回到家后,妈妈一如往常钻进厨房,哗哗的流水声听得我恨不得跟它们一起被冲掉。我红着眼睛走到妈妈跟前,掏出口袋里馋了一天的饼干放到她手上,我记不清她的表情是怎样的,只记得自己背着她把口袋里的饼干渣抠出来舔一舔,而那晚妈妈把我抱得很紧,但我犹豫很久,迟迟无法跟她说句妈妈你辛苦了。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如今,我的脸庞早已没了当初的婴儿肥,深深浅浅地走过二十多年,正如很早以前就懂的,我是个小姑娘,也知道不久以后我将不再是,失去年少的轻狂,失去无数艳羡的目光,沉沉地遁入呼啸的流年里。而记忆中那个一如白纸天真的小姑娘,她梳着利落短发,光着脚丫慌张走过生命最初几年的率性已经永恒。
(作者系岳阳市作协会员,湘阴县柳潭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