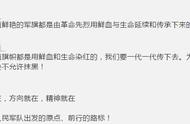火力配置既要考虑到正面阻击的需要,又要对反击的火力支援有充分的准备,要实行固定火力与机动火力、正面火力与侧翼火力互补,防御前沿和纵深要成梯次,构成曲直相辅、远近交错、正侧结合的浓密火力网;反敌坦克手段要多样,构筑反坦克壕、设置反坦克雷场、组织反坦克小组等。
在战术上则强调攻守结合,要以积极的攻势行动来达成阻击的目的。可以说,正是有了战斗之前这种结合地区、敌我双方特点的科学合理的防御部署,使得我军的战力发挥到了极致。10天之中,邱李兵团以死伤1万多人、损失坦克34辆、消耗炮弹12万发的代价只前进了10多公里,眼睁睁看着黄百韬兵团被全歼。
二、灵活机动、实事求是的战术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如果不顾战场上的实际变化,把作战计划当作一个不能改变的东西去执行,这是极为可怕的,很有可能导致失败。在三大阻击战中,一线指挥员能够根据战场变化实施灵活机动、实事求是的战术,发扬军事民主,听取多方意见,从而确保了阻击战的胜利。
塔山阻击战中,鉴于塔山无险可守,三十五团参谋长李益孟观察地形后提出建议,可将塔山沿线铁轨、枕木拆卸下来做核心工事和指挥所构筑掩体。另外,纵队还采纳了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的建议,构筑“壁里藏身”的防御工事。所谓“壁里藏身”,就是把防御阵地的散兵坑筑在村庄围墙脚下,每个掩体的半圈在墙脚内、半圈在墙脚外,作为架设机枪、单人掩体和掷弹处。敌人炮击时,战士和武器可退入墙内半圈掩体内,炮火打不着,当敌人炮火延伸、步兵冲锋时,我方可携带武器钻出到墙外半圈掩体,进行反击。这样,既可保护自己,又能及时反击,在阻击战斗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2日下午,纵队得到情报,第二天投入战斗的敌军主力将是蒋介石十万火急从华北调来的“王牌”部队——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九十五师。这支部队的特点是,全部美式装备,冲锋凶猛,不怕炮火与机枪射击,战斗力很强,但很傲慢,怕白刃战。对此,纵队连夜进行兵力调整,加强纵深配置,阵地前移,并且部署战士上好刺刀,准备以白刃战坚决*败敌人。事实证明,13日这一天是敌人投入兵力最多、火力最猛、进攻最凶的一天,我军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在正确有效的战术指导下,阵地还是牢牢地掌握在了我方手中。
黑山阻击战期间,10月25日是战况最惨烈的一天,廖耀湘投入了5个师以及全部炮兵的力量,发射的大口径炮弹将近1万发,营团规模的集团冲锋数10次,给我军造成了极大伤亡。面对疲惫到了极点的部队,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提出部队需要稍加整顿,待天黑后再组织反击。对此梁兴初坚决反对,严令必须立即反击。看似不通情理,但若等天黑后敌人站稳脚跟,工事也会得以加固,再施以反击势必徒增困难。为了保证反击的效果,梁兴初集中了全纵队所有的火炮,并调八十九团二营全力增援二十八师。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二十八师夺回92高地和101高地,合上了黑山这道闸门。

在徐东阻击战开始之前,华野最初制定的是打一场诱敌深入的阻击战,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部署上提出了不仅要“阻援”还要“打援”的设想,包含有将邱李兵团诱入包围圈进行围歼的计划。但阻击战打响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特别是1月18日华野在碾庄一带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事迟迟没有最后突破。如果此时与邱李兵团也呈现出胶着状态,形势发展将很难预测。对这一形势的报告经粟裕上报后,总前委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调整作战方案“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建议。19日,根据总前委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全力加快对黄百韬兵团的作战。11月22日,碾庄一带的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而此时邱李兵团的东援部队却仍然没能越过华野的大许家防线。这虽然与开始的作战设想有差距,但根据战场变化进行切合实际的调整,显然是真正的战场艺术。

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死守不退”的英雄气概
以单纯的军事观点看,阻击战是极为残酷的,是需要付出极大牺牲和奉献的。但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新中国”的解放战争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指引下,我军展现了令对手、令世人惊叹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