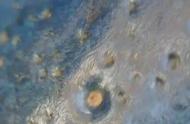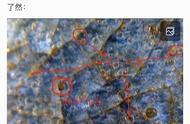曾经的“赵店‘洼’”——“耕地之‘洼’”
文/乔玉璞(山东阳谷)

在运河古镇——阿城向南至张秋镇分界处的这一片广袤原野就是阳谷县少有的“万亩‘大方’”,其南半部则是鼎鼎大名的“赵店‘洼’”。这稀奇古怪的名字是几十年前的叫法。前几年修通的金堤扶贫大道就在这“万亩大方”内穿行。夏秋时节,如果你在此间通行,就如同钻进一条长长的绿色走廊,两侧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满目葱绿,遮蔽双眼;微风掠过,将这一大片“绿色地毯”吹皱起的微微涟漪向远处“滚动”;你也如同进入一个天然“氧吧”,定会情不自禁地来个“深呼吸”,感受其中无限的“惬意”,也会顿生一种在城市久居的人所不曾有的“清新感”。
现如今,我村或附近村的80后、90后、00后们,对“万亩‘大方’”、“赵店‘洼’”这样的名称已很陌生,更不知其意,在此有必要“科普”一下。“大方”,是指一大片耕地,茫茫四野,非常开阔,其间没有任何村落。“洼”,是指地垫低洼,下雨易涝成灾。当年,我村人对“赵店‘洼’”三字很是“反感”,这其中缘由很有必要做一解释。这“万亩‘大方’”四周地势高,整个像一口“大锅”,而“赵店‘洼’”则是这“大锅”的“锅底”,是“洼”中之最“洼”者。在“三中全会”前,下同样的“雨”,周边村耕地一片寂静,而“赵店‘洼’”则“蛙声一片”。这蛙声不是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寄寓丰收的“蛙声”,而是寓示着涝灾来临,歉收、挨饿“将近”的“蛙声”,我村人听了这“蛙声”会倍感扎心与悲凉。当着我村人的面不能说“赵店‘洼’”,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那样也会犯我村的“大忌”,正如“守着瘸子不能说‘短话’”,“当着小秃不能说没毛”,“当着阿Q不能说‘光’”一样。有人戏谑我村“蛤蟆撒尿也成涝”,有夸大成分,但也不很“离谱”。若故意拿我村的“洼”开涮,我村性子暴烈者会忍不住“怒目圆睁”,甚至“拳脚相向”。因为这“洼”等同于“涝”、“淹”,等同于荒年、挨饿,等同于村上小伙寻不上媳妇。若在“洼”前加一“大”字,说成“赵店‘大洼’”定然没事儿,“大洼”是说我村田野开阔,广袤无垠,在十里八乡无出其右者,我村人听了自会有几分“快意”与“骄傲”。
“三中全会”后,我村和全国农村一样,实行了土地生产承包责任制,农田水利建设快速发展,与周边村实现了沟渠成网,排灌系统配套,下再大的雨,不再淹了,所有农田旱能浇、涝能排,丰收有保障。周边村的人渐渐地“感觉”不到“赵店‘洼’”了,也没人说“赵店‘洼’”了,这正如一个人“混”出点儿“名堂”,没人再喊原来的“诨号”,而要呼其大名一样,以示尊重。

下面,咱先说说这“赵店‘洼’”的事儿。
“三中全会”前,我村地势洼,十年九涝,一年只收一季小麦,秋季能不能“收”全看老天爷给不给面子。高粱抗淹,洼土适合种植。有谚:“高粱扛了枪,不怕水汪汪,高粱不没(mò)头,就能获丰收。”高粱收获时节,地里常有半尺深的水,车子进不去,只好将高粱头(穗)扦下来,捆成捆儿,或扛出,或用洗衣盆拴绳拖出,到高地儿装车子,再运回家。高粱很难吃,当饱就行,那年月高粱就是救命粮。小时候,我没少吃高粱窝窝,吃一口,光在嘴里打转转儿,就是咽不下。现在,有些人热衷于吃高粱窝窝,为“减肥、保健”赶时髦,而我不感兴趣,吃“伤”了。其实,高粱只是造酒的好原料,电影《红高粱》里一片片高粱就是为造酒而种,现在我村偶有种者,也是卖给酒厂造酒。
我村人苦于“洼”者,久也,可没少与这“洼”做坚决“抗争”。在人民公社时期,为“治洼”、抗涝,勤劳智慧的社员们想出的高招是“挖沟渠、造台田,保丰收”。在大地块里,划出一小方形地块儿,四周挖出壕沟,挖出的土再平铺到整个方形地块儿里,地面抬高,雨水排到台田周边的壕沟里,此地块儿谓之台田面,此沟儿谓之台田沟儿。台田沟儿除排水,还能引水灌溉。据村上老人们讲,实行了人民公社,土地公有才有可能挖成台田,在此之前,土地是一家一户的,挖台田根本不可能。那时,村上男女老少齐上阵,红旗飘飘,铁锨闪闪,起早贪黑,一车车、一锨锨,挖出了道道水沟,垫出了块块棋盘式的“方格子”——台田。为挖台田,社员们个个手有老茧、有血泡,压弯了脊背、累弯了腰,他们是苦*一代、是富于“愚公移山”精神的一代。这些台田为抗涝发挥了不小作用,但,雨再大就不大管用,会沟满壕平,漫入田间,庄稼被淹,高粱地里逮鱼捉虾,是常事儿。在那个很少吃肉的年代,社员们几乎年年能吃上这高粱地里的“鱼”,但也吃不出好“滋味”来,因为吃上了“鱼”却吃不上“粮”,吃鱼的“兴致”“排遣”不了庄稼被淹、“家无隔夜粮”的忧愁。
台田沟儿是我小时候与伙伴“刮鱼(将沟里水刮干,逮鱼)”的好地方,台田沟儿一年四季不干,饵料丰富,一到秋后,出很多鱼虾,肥美鲜嫩,刮干所剩无几的水,就能逮半筲鱼,炖上半锅,自是解馋。“刮鱼”也是很费力气的活儿。将一台田沟截成几小段,将最外一段的水刮到外沟,拾干鱼,尔后,再将相邻一段的水,放入刚刚刮干、逮过鱼的这一段儿,等此两段水平,再堵上口子,将未逮鱼的一段的水,刮入已逮过鱼的这一段,依此类推。一气下来,逮鱼不少,却弄的耳朵上、脸上、身上净泥,像个泥猴儿,浑身紫泥味儿,好几天下不去,但心里却乐开了花,因为有鱼吃,能“拉馋”。现在,水质变差,就别想这好事了。除在台田沟里逮鱼,还能捞“杂菜”(草本,长一长秧,叶上长刺儿,鲜嫩)喂猪,这也是上小学时的“勤工俭学”项目。

我村因为“洼”没少与邻村“闹乱子”。“赵店‘洼’”中部有一条纵贯南北的沟子叫“赵店沟”,南端与王营村东头金堤脚下的苇壕相连,王营与我村排水、用水共用此沟。王营地势高于我村,灌溉用水由王营一端流向我村一端。有一年,久旱不雨,地里裂指儿八宽的缝儿,机井少,只能靠陶城铺虹吸放黄河水灌溉,在汛期又不让放,眼看着棒子旱得叶子卷筒儿。 “天气预报”说,近期“没雨”、“没雨”、还是“没雨”,于是,阿城、张秋两公社积极协调虹吸放水,放水了,我村沟满壕平,而王营那一端沟里水不足一半。为让王营更多地用此水浇地,阿城、张秋两公社商议,在“赵店沟”一端打上一拦水坝,以提高王营一端水位,便于抽水浇地。可那该说实话的“天气预报”说是“没雨”,但在我村地盘上突降暴雨,我村迅即由旱变涝,田里存脚脖子深的水,不几天,棒子苗淹得焦黄,太阳毒晒,烫死不少。我村则屡屡要求将此坝挖开、放水,王营则不同意。老天不公,王营与我村一步之遥,只下了个地皮湿,照样大旱,棒子叶照样卷筒儿,仍需此沟水浇地,坚决阻挠我村拆坝放水,且让民兵把守。上级则要让我村顾全大局,做点儿“奉献”,我村社员不肯,仍强行拆坝,于是两村青壮年赤膊上阵,拿铁锨对峙,差点儿发生械斗。公社里为教育我村社员,免费放了好几场《龙江颂》电影,以教育我村社员发扬“龙江风格”,顾全大局,而那个时候的社员,只知道吃饱肚子,不管别的。“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没能拆坝放水,我村受了“窝囊气”,忍气吞声,接受了“屈辱”。从此,两村结怨较深,好几年不能和好如初。
我村“地洼”,下雨易涝,适合长草,红淤土壤,草特茂盛,几场雨下来,大沟子崖、小沟子边、田间地头、斜坡、路边,只要有潮乎汽(水分)地儿,草就疯长,五六天长一拃多高,没人知道草为啥长得比庄稼快又旺。草与庄稼“争”养分,庄稼不是草的对手,即使不绝产,收回的粮食比种子多不了哪儿去,草是大敌,必须铲掉。年年铲草是村上人头痛的事儿。在生产队时期,社员干活积极性不高,也“勉强”“晨兴理荒秽”,却出工不出力,田里仍是“草长豆苗稀”,那豆苗、棒子苗懒洋洋地被“淹没”在草丛里。“三中全会”后,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村民迸发出空前的积极性。那个时候,还没有如今天这样的农业机械,全靠人工干活,还是“战胜”了“不可一世”“狂”草。
与草之“战”是一场“争夺战”,若贻误“战机”,草胜人败,千万不能低估草的坚韧与顽强,草的生命力极其强大。割过麦子,雨季来临,套种的棒子(玉米)苗还没麦栅(音,割过麦子剩下的半拃高的麦秸杆儿)高,晃晃悠悠,半死不活,这个时候,第一个要紧的活儿就是将草消灭在萌芽状态。先用“霍子(人或牲口拉的、松土除草用的大耘锄)”将麦栅“霍掉”。那个时候,不是家家有头牯(牛、驴等),靠人拉“霍子”,红淤土壤,下雨时粘,稍干,就硬,拉“霍子”比沙土地儿“沉”多了,能累死人,通常三四人才拉动,还不能“霍”很深,深了拉不动。这“活”目的是松土透气,将草的萌芽“渴死”、晒死,此谓之“霍地”。可这“霍”下的麦栅连同泥块,相互支撑,透光、透风,容易干透,需踩实,还需另一个工序,即用挠钩子(一端有一钩或两钩,另一端是一小铲子),在一垄棒子苗间可劲儿将挠钩的“钩子”深扎下土里,狠狠地耧几下,也是为松土,将草幼苗“渴死”、晒死,也将“霍起”的大坷垃踩实,防地晒干,此谓之“横地”。这“横地”,有三分三解,若轻轻地“划拉”一道也可,那就是糊弄“地”,真使劲“横”,一天下来,不是腰酸腿疼、胳膊疼,就是半边膀子疼、半边胯骨酸溜溜,这“活”很考验一个人的体力和耐力。
割麦后的那十几天是将草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最佳时机。而上午顶上(中午)又是一天之内灭草的最佳时段。那个时段,太阳毒,铲下的草会很快晒死,下雨也反省(复活)不过来,所以“霍地”“横地”这“活”是越热越干(gàn)。为抢抓时机,我本家哥哥嫂子,孩子多、年龄小,吃饭的多、干活的少,自家又没有头牯(牛、驴等),年年一到这个时候,两口会就手忙脚乱、“瞎抓胡挠”、“心急上火”。好歹借了头毛驴儿,快快地将自己的地“霍”一遍,又“横”一遍。本想轻松一下,歇歇脚,可天不作美,突然来了场大雨,那半死不活的草又反省(苏醒)过来,三两天草芽泛“绿”了。这“活”又白干了,力白出了,汗白流了,我本家嫂子气得直哭:“俺咋整倒霉唉”,其实“倒霉”的不光是她一家。人还是别(biè)不过天,没法儿,还得将草芽铲掉。于是,两口子还得硬着头皮,耐着性子,带着干粮,提一大塑料桶水,天不明下地,中午不回来,饿了啃干粮,渴了喝那带来的凉水,一气干到黑,出了满天星,实在看不见地才返回,吃过晚饭十一点。如此,一气又干了三四天,这就是多出的“冤力”。两口子晒得黢黑,哥哥脱掉背心,一个黑白分明的背心“轮廓”“印”在上身,清晰可见,晒的膀子上、胳膊上满是踡曲的、皱起的层层“白皮儿”似掉非掉,嫂子那被污渍浸染的花袿衩,已看不见一点儿布色儿,只见泛起的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碱哥拉(音,汗的盐分沉淀后的污渍痕迹)十分“耀眼”,邻居们戏称她“晒地图”。这一气下来得十来天,两口子累得都瘦了好几斤,与平时判若两人。
如此,与草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庄稼长稍高点儿,还有一些漏掉的、零星的“抓地秧子(草名,爬秧,根多根深)”在肆无忌惮地疯长。这个时候,就不能用挠钩铲了,而用手薅,防伤庄稼。蹲着薅,抓住一绺猛使劲往后来,不大会儿小手指会红肿起来,生疼,手指甲缝里塞满泥,“撑”得生疼,指甲上端会磨出很多“倒刺儿”,生疼。而那长长的棒子叶表层肉眼看不到的、白白的一层“绒毛”蹭着手、胳膊会很痒,叶子两侧则像薄薄的刀片儿,在手上、胳膊上划出一道道微微凸起的“梗子”来,这是轻的,再狠点就是道道儿“血印”。这是图凉快而穿褂衩子或背心造成的,若穿长袖褂子,可免除此种“苦痛”,但又不透风,不一会儿捂出满身大汗,褂子溻透,紧紧地贴在身上,布鞋也会湿透,热得“炸痱子”、起疙瘩子,因为这,不愿穿褂子薅草。薅草也很费手力,手指会酸溜溜的。当然,懒惰点儿的人家也可能就把这草“放一码”,不出这“冤力”了。
如此与草之间的“战斗”,沙土地就不大有。据说,那个时候,沙土地的姑娘不愿嫁我村,就是嫌我村这“治地”、“治草”累。

夏秋时节,我村草状、草肥、草多在周边村出名。南边邻村王营,村子大、人多、地少、活少,很多劳力就到“赵店‘洼’”割草。尤其到了“立秋百草结籽”,来我村割草者甚众,傍晚时分,割草回家的人比我村收工回家的人都多,回家路过我村,晚上八九点了还有动静。割草可喂牛羊、可晒草卖钱,那时没有别的收入,这点草也得看眼里。我村人也会在农闲缝隙割草,或交生产队里挣工分,或晒干卖俩钱儿花花。
我村有地不能“撂荒”的“传统”,若地里“草盛豆苗稀”会让人“笑话(被人指责做的不对)”“不务正业”。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村上有些人家去城里做买卖,不再重视种地了,但每年也得把草“治住”,不能荒地,就是怕人“笑话”。
我村还有因“洼”出更多“冤力”的时候。实行生产责任制前,有一年,霜降过后还秋雨绵绵,下成了“秋拉拉(下好几天)”,地里存了水。下同样的雨,我村西部三里地远的沙土地的村早耩上麦子了,没事了,我村地里还有水,到立冬才下去,地仍很湿,不宜犁地。按季节说,霜降就是耩麦子最后期限,立冬耩麦子已经晚了,能耩麦子,出芽也只有“一杆枪”,分蘖少,得多费麦种。如此,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犁地种麦子,不抢种明年吃啥?于是,大队干部“舍脸”请来了公社东方红拖拉机,其自重大,地块湿,将地碾压得很实,再加那锃亮的犁铧子的挤压、摩擦,翻出了闪亮发光如门板大小的泥块块,掀起了高高的滚滚泥浪,后拖一耙,上蹲两人,蹲踞上面如海里冲浪,在大坷垃块上起伏,要将这大泥块耙成小泥块、耙平,也很不容易,稍干后会坚硬如石。之后,这耙过的地仍有一块块大坷垃。坷垃多了,土壤易干,种子易裸露、易压种子,发了牙也难以拱出。没好法,社员只好用三齿镢一块一块砸烂,很费人工。当然,牲口犁地,也出坷垃,但肯定比拖拉机犁出的坷垃小。我村祖祖辈辈都少不了这砸坷垃的经历。
不过,这“洼地”也不全是“坏处”,虽容易出坷垃,但肥力厚。刚出土的麦苗,艰难地从坷垃缝里钻出,如一杆枪,稀稀落落,半拃远一棵,远不如沙土地的苗整齐旺盛,但来年产量肯定比沙土地高。这就叫“沙地里看苗,淤地里吃饭”。
说完了我村人最不喜欢的“赵店‘洼’”,咱再说说我村人引以为豪的“赵店‘大洼’”。
一般说,一个村的耕地得是分布在村落周围,下地干活离家近,便于看护庄稼,而我村西、南、东毗邻的都是别村耕地,我村耕地都集中在村子东北方向,没人知道为什么。我村最远的地块六七里,这也是赵店‘大洼’”成其“大”的主要原因,但苦其路远者也,亦久也。生产队时期,自行车、拖拉机、农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小轿车统统地没有,要么赶着牛车子、要么人拉地排车,一趟五六里,干一天活,要往返二十多里地,耗费两个多小时。农忙时节,为争得更多干活时间,小鸡一叫就下地,出星星才下晌(干活结束)。干一天活,再走着回家,累得腿肚子朝前,一步也不愿意挪动。为节省吃饭往返的时间,要么送饭,要么在地里埋锅造饭,馇稠糊涂、熬疙瘩汤,自带干粮、咸菜,真正风餐露宿,“野营拉练”。有的劳力为了省下自己的干粮,光喝稠糊涂或白面疙瘩,一喝好几碗。那个时候,缺少粮食,算计得很到位。现在各式交通工具多了,农业机械化程度高了,再也不用送饭或田间造饭野炊了。
“赵店‘大洼’”“大”而“远”,生产队时期,容易没(被人偷)庄稼,最远的地块豆子、棒子不大很熟,就被外村偷个差不多。所以,在田间或路口搭窝棚、搭看台,看庄稼,轮值看守,记工分。为防“内鬼(偷庄稼的社员)”,在进入村的路口设置检查哨,检查散工回家的社员背着的草篓子里或身上是否夹带棒子、豆子、棉花等,俨然国家口岸的检查站。若查出来,不是游街,就是批斗。那个时候,我是红小兵,还与大队里的民兵一块“把守”过主要通道上的大桥,对上下晌的社会员“搜身”,想来有几分滑稽可笑。在高高的看台上(用檩条子搭起三四米高)面“放哨”,俨然空中瞭望哨上的哨兵,夜晚,在上面向四周喊话,吓唬吓唬偷庄稼的小偷,其实也为自己壮胆。80后、90后、00后们可能不知窝棚、看台为何物了。
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八十年代末,除草剂普遍使用,再也不用与草做“殊死搏斗”了,“霍地”、“横地”的事儿就免了。这得少出多少力?现如今用上了先进的旋耕犁,将坷垃连同秸秆绞得粉碎,既省人工,又增加肥力,再也不用为“砸坷垃”犯愁了。现在我村排灌条件得天独厚,地力肥厚,粮食产量高,年亩产1.5吨以上。河南、吉林是种粮大省,我村则是种粮大村。我村人历来秉持“农民种粮”是本分的“执念”,经商办企业者甚少,主要从事种粮种菜的传统农业,以实际行动响应*提出的“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号召,每年都为国家贡献很多粮食。近些年,从事大棚蔬菜生产,一片片的塑料大棚,阳光照耀,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我村的菜销往全国各地,村民日子富裕起来。

“赵店‘洼’”是一块风水宝地,养育着世世代代的赵店人,祖祖辈的赵店人辈辈都深深地爱着这块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洼地”、“坷垃地”。“我也爱这土地”、“也爱得这般深沉”。我也愿所有在金堤扶贫大道穿越“赵店‘洼’”的朋友们停下来,徜徉在“赵店‘大洼’”里,也在这免费的“氧吧”里做一个“深深的呼吸”,也能静心观览我村这片茫茫无际的绿野,您定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作者简介】乔玉璞,山东省阳谷县作家协会会员,公开发表教育专业论文30余篇,主编校本培训教材4部,与他人合作出版论著5部,现喜爱散文写作。
壹点号文峰山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