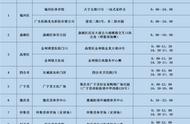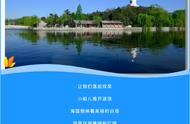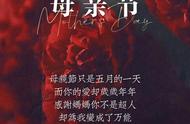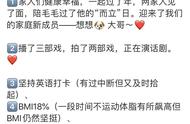《寻龙诀》剧照
盗墓小说是由语言写就,虽然这采用了似乎离“直接看到”最远的方式,但无论是在语言风格,还是内容刻画上都直接地给人以电影般的视觉体验。一是文字上倾向于口语化,盗墓者因大多是社会“黑道中人”,对话中出现粗口也是有的,直接的情绪表达对于社会化较好的读者来说可谓是一次“情绪释放”;二是网络文学给予的互动性优势,网络小说更新速度快,语言文字上虽然降低了要求,但与读者互动性上显然加强,拉近观众的体验距离。日本动漫《海贼王》的作者经常会阅读读者们揣测的剧情,转而在情节中“制造惊喜”。另外,较好的互动性,也正是“众口能调”的原因。
但小说能引诱人,在于它让读者轻易置入小说时空的那套发生机制。这一方面是它内容上的“相似性”。无论是《盗墓笔记》还是《鬼吹灯》,总有写让人觉得熟悉的“真实”在里面,比如《鬼吹灯》历史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刚改革开放不久,开篇提到潘家裕古玩市场,邓丽君磁带是那个年代对应的“真实”,而像是云南、湘西等,相应地设置了多虫(虫谷)、赶尸等与现实地点相符的自然人文要素。另外,墓穴呈现的历史朝代也不是完全架空,朝代的特点会显示在碑文、墓葬习俗等方面。
另一方面是“陌生化”。上述提到的“粽子”等整套“盗墓”概念体系,对于读者而言都是远离生活的。“坟墓”“宝藏”本身虽不陌生,但它们大部分时候都“沉睡”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中。小说通过细致的描绘,将这一黑暗空间暴露在大脑的想象中,每个人跟随小说都下去自己脑海中构建的“墓地”中取宝,遭遇“奇异”而“恐怖”的事件。

《怒晴湘西》海报
类型化小说的“难堪”
盗墓小说“不入流”“不高级”?
对“熟悉与陌生”,或“真实与虚构”的交织运用,盗墓题材的确在抓牢了读者和观众,在矫情于男欢女爱的言情、宫斗、仙侠等题材作品中独树一帜。但是盗墓文学,与大部分“网络小说”一样,依托的“真实历史”过于碎片化,所涉人文历史知识显得单薄。它们并不是故事探宝揭秘的重要线索或者背景,就这一点可以对比早年同样受大众喜爱的《木乃伊》系列,电影基本上紧扣埃及文化和法老王墓葬习俗。盗墓文学作为刺激的“辣条”吃吃可以,但读者和观众会不会觉得“吃不饱”,或觉得“吃得不够高级”呢?
小说类型化,其实一定程度上说明它发展已然成熟。小说自古以来就是大众喜欢的阅读对象。它不像“正史”一般严肃,在“教育”功能上与正史不同,手段也不同,语言形式更是多样。但要成为一个“类型”需要一定数量同质的东西出现。“盗墓”小说通过网络写手的“跟风”和网络传播达到了这个要求。不过,这些跟风的小说大抵跟住了“盗墓”这个套子,却无法复制《鬼吹灯》《盗墓笔记》的“荣光”。
并且,即便像是《鬼吹灯》《盗墓笔记》这样的大流量作品与所谓“严肃文学”碰撞时,双方都有些“难堪”。2011年,中国作协启动第八届矛盾文学奖申报工作,“持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重点文学网站”上的文学作品可以申报。但被媒体热议的是,最终获奖的并不是我们时下所谓的“网络小说”。2017年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暨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网络文学新人奖”颁奖终于对网络文学创作者予以肯定,似乎是“严肃文学”的一次“屈尊”。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陶东风先生曾在多篇文章讨论网络文学,指出小说在艺术价值、人文精神上的匮乏,并且即便使用了奇特的想象力,但也只是为了奇特效果而故弄玄虚,本末倒置,在内涵上难免有“贫血症”和“败血症”。不过,这种“严肃而严厉”的分析似乎并未给予网络创作者们太多的困扰,就好比据称是“被迫申报茅盾文学奖”而铩羽而归的南派三叔,解释自己的作品只不过是追求大众肯定的通俗小说,与小圈子的严肃小说并不相同。
背景资料
(1)网络文学与茅盾文学奖

南派三叔
2011年,茅盾文学奖申报阶段向网络文学开放。但在初评阶段,大部分网络文学落选,包括《盗墓笔记》和《杜拉拉升职记》。有记者向中国作协创研部胡平提问《盗墓笔记》为何出局,胡平回答因为《盗墓笔记》还未完结,而从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开始,只有线下完结出版的系列作品才能参评。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南派三叔说茅盾文学奖对他来说不算荣誉,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严肃文学,而他写的是通俗小说。
(2)文化研究学者看盗墓小说

学者陶东风博客截图
2006年,盗墓题材小说刚刚兴起。陶东风在《中华读书报》和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一文。文中提及80后的玄幻文学中的“装神弄鬼”是想象力受阻之后畸形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价值世界混乱和颠倒的表征。80后生活在价值真空的世界里,浸泡在电子游戏里,想象力再惊叹,也是缺乏人文深度的。在现实溃烂、未来渺茫的时代,犬儒主义以“装神弄鬼”的形态表现出来。
2008年,陶东风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发表文章《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后写作”举要》,文中写到盗墓小说继承自玄幻小说,核心仍然是装神弄鬼,它的奇观化写作更能吸引读者,但是缺点也很明显:艺术价值值得怀疑、人文精神稀薄、远离现实。
“不入流”这三个字,一直会给自身存在性带来质疑。在南派三叔上述的解答中,似乎较为合理地划清了网络小说和严肃小说各自的界限和空间,甚至是目标取向。但这种矛盾碰撞并不会就此一劳永逸地解决,或许“争执”与“妥协”会交替出现。严肃小说被迫“屈尊”的背后是在迎合市场,走向“大多数”,但也是在适应“大众文化与阅读的新局面”。通俗小说(网络小说)想要“入流”恰巧是因为它想要“正名”。二者在这个历史时代为了赢得“名利双收”的局面而各自努力。
无论是通俗还是严肃小说,以受众来评判高下,并不是最优的。何况,“小众”本就是“大众”的一个部分。形成小众取向可以是“偏好原因”,但无论是大众还是小众,对于文学的审美力却是一直处于可塑和被塑的状态。这就像钱穆所言,“文心即人心”。电影《料理仙姬》里有一集,一个名叫“小亮”的男孩,作为吃惯了薯条汉堡的年轻一代,会往一切食物中添加番茄酱,并且反问料理人是不是没有味觉。
当下的流行或许就是未来的传统。对于网络文学这种通俗作品而言,现在的问题恰巧是,它并不单是因为它出现的空间是互联网和种种新媒体就可称“存在即合理”。网络文学自身的“价值负载”问题不可逃避。它是满足现状,还是走向“价值升级”?在当今“受众广”“经济利益”助推它登上王座的同时,一直会有再造什么样的新传统、再创什么样的“社会效益”的反身性问题跟在身后。
作者:高佩
编辑:榕小崧、沈河西 校对: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