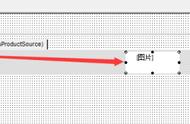在我的书房里,有一本我十分珍惜的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不过,更令我珍惜的是《莎士比亚全集》里一直夹放着的几张发黄的纸,抬头印着“南京大学外文系课程教案”几个字,内容则是打字机打印的一些思考题和文学术语解释。这是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导师陈嘉先生为我们开设《莎士比亚戏剧选读》时发的材料。看到这本《莎士比亚全集》和这几张材料,往事历历在目,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陈嘉先生的音容笑貌。

书房里的陈嘉先生
白驹过隙,一晃陈先生去世已经三十五年了,现在知道他的年轻人估计也不多。近来陆续读到一些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不禁又想起陈先生,想到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坎坷之路。按照陈先生之子陈凯先的说法,陈先生乃书香门第出身。陈先生的父亲陈世第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有译著《英国宪政史谭》(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陈先生的大伯陈汉第(字仲恕)诗词古文、金石书画均有颇深造诣,前段时间读柯律格(Craig Clunas)所著《谁在看中国画》,其中专门提到了陈汉第:“丁巳(1917年)十二月一日,叶玉甫、金巩北、陈仲恕诸君集京师收藏家之所有于中央公园展览七日,每日更换,共六七百种,取来观者之费以振京畿水灾,因图其时之景以记盛事。……我们能够在画面中看到二十位人物,他们在三位北京文艺界领袖(叶恭绰,1881-1968;金城,1878-1926;陈汉第,1874-1949)的号召下前来参观义展,为1917年国内发生的水灾筹款。”(《谁在看中国画》,[英]柯律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222页)从中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不仅艺术造诣高超,且颇有怜悯爱人之心。陈汉第还参与创办了“求是学院”(浙江大学前身),深受人们爱戴。陈汉第的胞弟陈敬第(字叔通)不仅是实业家、学者,也是社会活动家,钱学森回国一事,陈叔通就曾参与运作。那一代人报效国家的决心之强烈,真乃楷模。

表姐吴贻芳与陈嘉先生夫妇
陈嘉先生家族名人很多,但家人很少对外披露,我读书时知之甚少,现在也不敢说了解很多。陈先生的堂兄陈植是著名建筑师,与梁思成一道在宾大读建筑,毕业后回国,留下不少建筑设计作品。表姐吴贻芳是金陵女大校长,代表政府签署《联合国宪章》。师母黄友葵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当年被誉为“四大女高音”之首。师母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南京艺术学院,桃李满天下,1987年师母八十大寿的时候,魏启贤、臧玉琰、刘淑芳、孙家馨、刘明义等全国各地的弟子云集南京为她祝寿,有的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同台献歌,那场面令人感动,无形中也让我立下了日后做教师的心愿。

年轻时的陈嘉先生
陈嘉先生1928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赴美读书,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英文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陈先生在耶鲁的成绩是全A,撰写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中国人在耶鲁获得英文博士相当不易,另两位获耶鲁英文博士的华人学者柳无忌和夏志清都留在了美国,回国的只有陈嘉先生。1996年,美国学者Florence S. Boos在美国刊物ARTHURIANA6.3(October. 3, 1996)发表的论文William Morris, Robert Bulwer-Lytton, and the Arthurian Poetry of the 1850s里就提及了陈先生早年的博士论文(Chen, Karl Chia,A Study of the Sources and Influences Upon William Morris’s The Defence of Guenevere and Other Poems' Diss, Yale University, 1934)。

陈嘉先生博士论文
陈先生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教书。西南联大条件艰苦,陈先生之女陈励先曾经说过,父亲在西南联大教书,头顶上还不时响着飞机,条件颇为艰苦,为了赚取弟弟的奶粉钱,母亲只好到重庆去唱歌,只留陈先生在昆明。李赋宁先生和刘海平先生都曾提到陈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之余还创作过剧本,可惜遭日军飞机轰炸,手稿遗失。陈先生确实喜欢戏剧,抗战期间曾为美国杂志撰稿,介绍战况和中国的新戏剧。洪长泰在《战争与通俗文化》(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中提到了陈嘉先生的论文《不宣而战的战争与中国新剧》(Karl Chia Chen, "The Undeclared War and China's New Drama,"Theatre Arts23.12, December 1939)。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刘思远教授和韦特莫尔教授(Siyuan Liu and Kevin J. Wetmore Jr.)编著的《英语中国戏剧精选书目》(Modern Chinese Drama in English: A Selective Bibliography,Asian Theatre Journal, vol.26, no.2 [Fall 2009]:320-351)也提及了陈嘉先生抗战期间在美国发表的三篇论文,除了上述《不宣而战的战争与中国新剧》,还有“New Opera in China”(Theatre Arts26 [1942]: 661-663)和“Opera Defeats Spoken Drama”(Theatre Arts31 [1947]: 48-52)两篇。
这样一位忠贞的爱国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却遭到了始料未及的厄运。1964年,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陈先生带领南大师生表演《哈姆雷特》等作品,成为中国莎剧演出第一人。这样一个纯粹的文学活动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两年之后,《新华日报》刊发由南大两位年轻老师主笔的文章,对陈先生大加揭发批判。杨苡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里专门提到陈嘉先生对她的影响,说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让她远离政治。没想到,陈先生这位不愿意跟政治搭边的学者,最终还是难免卷入其中。而陈先生以英文撰写的皇皇四卷本巨著《英国文学史》也面临种种无奈。商务印书馆前副总编辑徐式谷先生曾回忆说,因为书中有些提法跟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说法不一样,编辑部的几位领导感到没有把握,于是他随身携带书稿(可见重视程度)赶赴南京,与陈先生面谈,陈先生态度坚决,说一个字也不改,出了事他负责(徐式谷,《迎接120周年馆庆时怀念作译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陈嘉先生复出,当时的南大也是百废待兴,他不计前嫌,也不提当年的是是非非,而是青山不老,设法将一些学生从连云港、南通等地调回南大工作。
我是1984年成为陈先生的硕士生的。由于本科也在南大,因此,与陈先生及外文系名教授如范存忠、郭斌龢等先生虽未见面,但已耳熟,后来通过和刘海平、王希苏老师的交流,我对陈先生的了解也多了一些,知道他先后拿过几个美国名校的学位。我对笔试之后的面试感到十分紧张,因为笔试是在考场,那么多年考下来了,已经习惯了,和陈先生这样一位知名学者面对面,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面试时,陈嘉先生仿佛看穿了这一点,满面笑容,十分慈祥,问我读了些什么书,本科论文写的什么,知不知道印度有个著名诗人叫泰戈尔,等等,主要问些知识方面的问题,并不深入提问,但是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陈先生对知识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后来他也跟我们说,希望我们知识面要广,能做jack of all trades,大量涉猎,广泛阅读,不能只盯住某个点。多年后,当我带着学生读伯林的《刺猬与狐狸》时,脑中不由自主地就会冒现陈先生当年的要求。
南大当时有个惯例,对知名教授,学校都会派车上门去接,同时派一名学生跟车。我也不知道学校何以选中了我,不过感到十分开心,这让我多了一个接触先生的机会。记得每个星期上课前,我都会准时赶到南大在汉口路、青岛路口的车队,跟着开车的师傅一起到陈先生在沈举人巷的家里,将他接到学校。学校车队当时的车子也有限,接陈先生的是一辆上海牌轿车,开车的师傅对陈先生也充满敬意。可能是每次都由我去接陈先生的缘故,陈先生布置作业时,都将打印好的思考题和术语解释材料交给我,由我转发给其他两位同学(后来给我们上课的毛敏诸老师也是这样)。我倒也没有想太多,只是感觉这些材料十分难得,那时的外文资料还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再加上纸也很薄,所以上完课后就将它们夹在书里。没想到,多年之后,这些纸张却成了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
陈先生亲自给我们开设《莎士比亚戏剧选读》,我记得是在南大图书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他给我们讲解《哈姆雷特》等四大悲剧和《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亨利四世》《暴风雨》《约翰王》《驯悍记》等。他讲解的时候仿佛演员在表演,使我们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年他带领师生表演《哈姆雷特》时,自己扮演的就是哈姆雷特。
陈先生上课和蔼可亲,语调也比较平缓,也许是上了岁数的缘故。相比之下,毛敏诸老师的要求就要高一些,她讲起英语来抑扬顿挫,十分有特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毛老师当时给陈先生做助手,所以我们接触的机会也较多。回想起来,当时的导师制度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地方。陈先生德高望重,岁数也大,但还亲自给我们上课,而且为了保证质量,他还指定毛敏诸和张子清两位老师给他当助手,再由毛老师辅导我们。记得陈先生指导我们学了十几部莎士比亚的剧本,又特别强调文本的细读,抽段给我们讲解分析。我们那个年代,小学、中学基本没学多少英文,读的书也不多,一个学期一下子读五部莎剧,而且剧本里的英语单词、典故等等又与我们的生活相去甚远,感到苦不堪言,但我们确实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查着词典啃莎剧,只苦于无法完全理解。陈先生的标准并没有因此而放松,他出的期末试题非常难,几乎要求我们对读过的莎剧了然于心。我的书房里有一本没有注解的《莎士比亚全集》,是当年美国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书已发黄,扉页里还夹着陈先生考我们的题目:
1. Name the speaker, give the context in the play, and explain the underlined parts:
For they shall yet belie thy happy years
That say thou art a man.
Diana’s lip
Is not more smooth and rubious; thy small pipe
Is as the maiden’s organ, shrill and sound,
And all is semblative a woman’s part.
I know thy constellation is right apt
For this affair.
2. Paraphras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 such a way as to explain it fully:
Things growing are not ripe until their season,
So I, being young, till now ripe not to reason.
And, touching now the point of human skill,
Reason becomes the marshal to my will,
3. State the connection of the following passages with the play. (Note: name the speaker, the person addressed, and connection with the text. Do not attempt to explain them.)
a) The lunatic, the lover, and the poet
Are of imagination all compact.
b) I am a tainted wether of the flock,
Meetest for death; the weakest kind of fruit.
c) And so from hour to hour, we ripe and ripe,
And then from hour to hour, we rot and rot,
And thereby hangs a tale.’
d) The poor world is almost six thousand years old, and in all this time there was not any man died in his own person, videlicet, in a love-cause.
e) for I never knew so young a body with so old a head.

南京大学外文系课程教案
这样的题目考得我们颇为痛苦,到了第二学期,我们向陈先生提出能否通融一下,陈先生倒也通脱,说:那你们就写文章吧,不要以为写文章容易,写好文章,要有自己的观点,恐怕比考试还要苦,不过,这也是你们需要锻炼的地方。我记得我写的文章是莎士比亚悲剧里的丑角(clown)形象,具体写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写作的过程对我是个很好的锻炼。当时听说有几位教授将写文章看得很重,我们也曾问陈先生,作业和论文是否可以用中文写,这样发表起来相对容易些。陈先生并不同意,他讲了两点理由:你们学的是英语专业,英语非母语,如果你们现在不用英语写作,英语综合能力就无法得到提高;中国要走向世界,就需要精通英语和中国文化的人,这样才能跟世界打交道,也就是说,英语成了你们的饭碗,现在的英语基础打不好,未来的饭碗就未必牢。当然,还有一点我们后来才知道:陈先生怕我们基础不扎实,发表的文章缺乏深度和思想。
关于陈先生的通脱,还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一件事情是,1985年,王宽诚基金会成立,资助全国在校学生到美国攻读博士。我是事后才得知的,看到英国文学试卷似乎和陈先生的出题风格相近,大着胆子去问他,考卷是否为他所出。他说:是啊,你们报了吗?我说没有。他问为什么,我说:事先不知道……另一件事情是,我曾申请赴美国宾州大学读博士,而自己当时正在跟陈先生读书,还没拿到硕士,因此十分犹豫,生怕陈先生不高兴。后来硬着头皮到陈先生家,请他为我写推荐信,没想到陈先生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很快就把推荐信写好了。记得他的桌上放了本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新批评主将克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沃伦主编的《美国文学:创造者与创造》(American Literature: The Makers and the Making),是杨仁敬先生访美回来带给他的。我翻了一下,感到很喜欢,他看到之后,兴致一下子上来了,向我介绍不久前他回母校耶鲁大学讲学的经历,并解释美国的scholarship与fellowship之间的差别,说希望我最好能够拿到奖学金,以解生活之忧。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最终并未成行,对陈先生的帮助,却一直铭记在心。

《美国文学:创造者与创造》书影
陈先生偌大年龄,还时常代表南大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每当我和他谈起此事,他就说这是为了学校的发展和年轻人的培养。有一次,我送他到南京机场,当时他已年近八十。我想送他到候机室,他说机场管得很严,不让送行者进去。说话时精神之矍铄,仿佛是个年轻小伙子。他从我手上拿过他的公文包,又对我说:回去吧,你等在这儿也没用,早点回去吧。我看着他前往机场的背影,不知怎么的,想起了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先生当时的神态,至今仍留在我的心头。
也许正因为我觉得陈先生的身体十分健康,所以从未料到他会突然得病,大概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刚刚住进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时候,还比较乐观,说不会有大问题,过两天就出来了。四五天过去,他也开始觉得有些不妙。当时他的肝腹水比较严重,每天医生都要给他抽水,我在旁陪护,心情很不好受,陈先生自己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也感到内心不安。我的爱人(当时还是女友)正好在省院实习,她每天过来看我,也看看陈先生,陈先生对她渐渐熟悉起来,看到她时,心里似乎也安定了些。陈先生住院期间,《英国文学史》第四册出版,送到了他的手上,他非常开心,说这是他一直期盼的。此书他很早就开始构思,书稿送到出版社之后,又校对多次,还请了国内专家专门开过论证会。英文书稿排印时难免会出错,为了对读者负责,他校对清样十分仔细,出版过程也就拖得很长。他随手拿过一本书,对我说:这本送给你吧。我说,陈先生,您就写个字吧。于是,他拿起笔,在书上写了“欣赠”二字。这本书,我一直珍藏至今。
在病房待得久了,我同医生也熟悉了。医生私下告诉我,你们老师大概是出不了院了,我却依然抱着幻想。有一天,陈先生对我说:“你不用陪我了,有她(指我的爱人)看着就行了,你赶紧到北京去查资料,把论文写出来,论文写不出来,你待在这儿有什么用?”我也是少不更事,经不住他的再三催促,于是去了北京。没有想到,正当我在北京查资料的时候,先生驾鹤西去了。得到消息后,我赶紧返回南京,心中的悔恨真是无以言表。后来我才知道,陈先生本就患有肝炎,由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迫住在地下室,还有不懂事的孩子朝着地下室扔砖块,健康大受影响,这次住进医院,已是肝癌晚期。陈先生病发,是黄友葵师母打电话给南大,正好钱佼汝老师那天没课,便赶到陈先生家里,叫了一辆三轮车,将陈先生送到南大医务室。医生说最好留院观察一下,便把陈先生送进了病房,谁知这次离家之后,陈先生就再也没有踏进过家门。年届八十的陈先生转到省院那个三人间普通病房时,天气炎热,病房里却没有空调,医生每天还要给他抽肝腹水,备受折磨。记得有个晚上,病房还住进了另一位南大的教授,来了很多人抢救,使得陈先生没能好好休息。他对儿子凯先说,见最后一面没什么意义。这其实是他的一贯想法,他常引用法语“Après moi, le deluge”(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家属原本向南大申请了空调,但空调运到之时,陈先生已然陷入昏迷,第二天就去世了。酷暑是老人的*手,南大的沈同洽先生也是被一个奇热的夏天夺走生命的。陈先生一代名师,晚景如此凄凉,令人不胜唏嘘。
1987年5月的一天,毕业离开南京之前,我去陈先生家里向师母辞别。师母独自一人在家,正在循环播放一段音乐,哀而不伤,令我想起《前赤壁赋》所述:“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我心想,这或许是陈先生喜欢的音乐,师母怀念先生,借着音乐继续与先生交流。当时没敢多问是什么曲子,现在想想,有些后悔。希腊人称音乐为一切艺术之源泉,可谓至理。Music, muse, museum,诉诸感觉,似乎胜过plastic art,难怪尼采等西方哲学家、评论家钟情于音乐。
陈先生去世后,我曾想写点纪念文字,转而一想,先生学界地位崇高,门人弟子五湖四海,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好像还轮不到我这个后生小子。三十多年过去,如今我已不再是当年的年轻人,而自己给学生上课时,出差时,读书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起陈先生,想起书架上的那本《莎士比亚全集》,想起夹在书里那些已经发黄了的材料,想起他慈祥的微笑,想起他期盼学生成才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