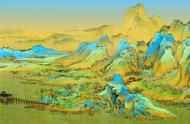陶渊明让人无从下手,言不及义地通过文献和历史的途径接近他,只能得到或寡淡、或牵强的结果。我们必须回归语言本身,全心投入诗之流中,以接引禅机或体验密契的态度面对他。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16日专题《风景不殊——魏晋时代的文学与抒情》的B04-05版。
「主题」B01丨风景不殊——魏晋时代的文学与抒情
「主题」B02-B03丨从魏晋到晚明:寻找被压抑的抒情之声
「主题」B04-B05丨制造陶渊明:韵律、玄思与美酒打造的文学风度
「经济」B06-B07丨经济学仅仅是富人的学问吗?
「主题」B08丨谢灵运 一生放纵不羁爱山水
陶渊明是个相当难以评述的诗人。他不像李商隐,诗中多有晦涩之处,需要笺释以发其诗心。他也不像杜甫,可以诗史互证,揭示其中精妙的深意。他的诗明白如话,妙处也与历史无关(或无法证明),用文献或历史的进路去读陶,意义不大。比如近来有个陶诗公案,说陶渊明的“刑天舞干戚”,原本应作“形夭无千岁”,宋人以意揣度,改成了现在的样子;有人说宋人改得对,有人说宋人不该改,也有人说这代表了陶渊明形象的变化。
其实,从文学的角度看,“刑天舞干戚”和“形夭无千岁”无甚差别,改了之后诗味并未变好或变坏,陶诗的妙处原不在此。当然也有人会说,鲁迅以此句说明“静穆”不是陶渊明的全部,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作品,所以还是有考证的必要。但一来陶渊明有咏荆轲的诗,已足以说明他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不必再引此为例,就像去北京可以坐飞机或火车,不需要舍易就难,特地去找一辆没有牌照的小黑车;再来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发现原始版本才能解决,空讲道理没什么用;三来每个人的想法都在变动,通过只言片语判定其思想,不能说毫无意义,只能说极不靠谱。鲁迅此文只是在批评朱光潜绝对化的论断,说明“倘有取舍,即非全人,更加抑扬,更离真实”的道理,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需要“死于句下”。何况陶渊明是个诗人,魅力全在文字上,只关注其思想,无异于买椟还珠。

北宋李公麟《渊明归隐图》(局部)。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陶诗的另一重著名公案。我们耳熟能详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选》作“悠然望南山”,苏东坡说作“见”好,“望”字没有余味,“见”字说明陶渊明本来无意望山,采菊的间隙偶尔抬头,不经意间见到了南山,与“悠然”的心境相合。这个公案比前一个公案有意思些,因为它关系到文字的高下,现在的教材都用“见”的版本,说明东坡这一改深入人心。
从文献上看,做“望”字更有依据,但东坡改“见”的道理十分充足,“见”字确实更妙。但微妙之处在于,文学的标准不仅有“妙”,还有浑成和自然。我以前也认为“见”字好,现在却觉得“见”字为妙而妙、略嫌做作。当代诗人洛夫有一首新诗《边界望乡》,其中写道:“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也是说山撞入诗人的视野,与“悠然见南山”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更加夸张。我少年时爱它设想新奇,现在年纪大了,口味淡了,再看此诗,便觉喜欢不起来——不能说不好,只是太刻意了。“悠然见南山”也是同理。为什么人年纪大了,往往不喜欢这种“刻意之妙”?因为经历得越多,就越感到诚意的可贵,也更能辨别诚伪。所以古人说“修辞立其诚”,文字要感人,必以诚意为先。这当然不是说东坡、洛夫有什么“伪”——东坡的人格光明伟岸,照耀千古,这是人尽皆知的。但文学上的巧思意味着某种算计,对文字的自然有所损害,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会像话剧演员那样讲话,尽管话剧演员金句不断——如果有谁开口话剧腔,难免令人侧目。苏东坡的诗文可以说无一句不妙,但正因太妙,反而难以企及陶渊明的浑成之境——陶公之高,本就不在字句之精巧上。
诗歌的本味与余韵
最高妙的文学境界是自然。它必须挽合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品质——直接和含蓄。陶渊明做到了,他的诗既直接,又含蓄,娓娓道来,余意不尽。直接意味着不做作,不算计,称心而谈,就像一个可靠的老大哥,说出来的话质朴平淡,而天然有一种令人信服的深沉。不过也正因如此,陶渊明在生前以及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诗坛地位不高——在当时的文学观念中,诗是一种脱离日常语言的文体,需要华丽的辞彩、特异的句式、精炼的对仗、讲究的音律,而这些陶渊明通通没有。坦率地说,当时的主流诗歌相当难看,往往毫无节制地滥用辞藻,就像一些质量平平的老电影,现在看来演技夸张而稚嫩——或许正是因为稚嫩,所以夸张。它们只是诗歌发展史这根链条上较初级的一环,已经基本过时了;而远离主流的陶渊明则是成熟而超越时代的,至今仍常读常新。

文征明手书《归去来兮辞》。
再说“含蓄”。有一种普遍的误解,混淆了“含蓄”和“委曲”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品质。“直接”的反义词并不是“含蓄”,而是“委曲”。《二十四诗品》作者成疑,却是一组颇有见解的诗论,其中就分设了“含蓄”和“委曲”两品,说到“含蓄”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委曲”是“似往已回,如幽匪藏。”皆极精到。“含蓄”是点到为止,语言的背后藏着难以言表之味;“委曲”却并不是“藏”(“匪藏”),而是把直率的表达变得曲折(“似往已回”)。倘若用两点间的道路打比方,“委曲”是把一条直路变成九曲弯路,路程增加了,距离却没有变化;“含蓄”的目标却在路的尽头之外,车永远开不到,只能“悠然见南山”,遥遥望见云遮雾绕的庞然大物。
李商隐的诗堪称“委曲”的典型,他会把一个意思折叠多次,读者必须在思维中层层打开,探索作者创造的“碧城十二曲栏杆”,满足一种“极繁主义”(Maximalism)的乐趣。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后来,“委曲”成了主流价值,以至于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竟把“委曲”当成了文学的基本要求!
陶渊明则是一个与“委曲”绝缘的诗人。他的诗不弯不绕,余韵十足。如果说“直接”代表了诚意,那么“含蓄”就体现了诗人把控语言的能力。诗史上不乏以“含蓄”著名的诗人,如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等,清初的诗坛盟主王渔洋更是以“含蓄”为诗之极则,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视为最高境界,在此理念下创作了大量作品。那么,陶渊明的“含蓄”有什么特点呢?答案就在“直接”上。王渔洋利用留白达到“含蓄”的效果,十分话只说三分,惜字如金,故作摇曳,就像妃嫔用矜持博得君王的欢心,可说是一种“饥饿营销”,在艺术上并非高境,极易流为俗套。王维的诗境比王渔洋高得多,却也难免这一习气。
通过遮掩达成含蓄,仍是一种作态、一种算计。真正的“含蓄”不应是可以表达而不表达,而是通过言语传达难以言表的韵味(王渔洋提倡“神韵”,可惜他在实践中把“神韵”变成了一种姿态)。它是一种语言的质感,而非结构的设计。苏东坡评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敏锐地察觉到了他语感的丰腴,就像饱满的鲜橙,足以榨出丰沛的汁水。举个例子,《饮酒》中有一段:“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直直道来,毫无矫饰,但余味无穷,读起来实在舒服,就像一个人说话,不哗众取宠,不插科打诨,诚诚恳恳,平平淡淡,而让人感觉有趣,这才是真正的有趣。拿食物打比方,他人的好未免依靠调味品,陶渊明的好则纯是本味。
“天籁”与“人籁”
那么,陶渊明的“本味”来自何处?诗是语言的艺术,它的秘密藏在韵律中。这就引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当时诗坛的主流是谢灵运这样精通音律的诗人。谢氏编写过《十四音训叙》,用反切法标记梵文,可说是那个时代一流的语音学者。他将音律的知识运用于创作中,极大地影响了强调声律的永明体,永明体的大师、同时也是史学家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后还写了一篇讨论声律的论,尽管他在文中批评谢氏并未窥破诗律的奥妙。有趣的是,同样是在《宋书》中,沈约记载陶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我们现在读他们的作品,却有个明显的感觉:“不解音律”的陶渊明语感远胜于精通音律的谢灵运,也远胜于或许更加精通音律的沈约,这是为什么呢?要探明其中的道理,必须回到中国诗歌的源头。

陶渊明《草书拟古九首帖》。
诗、歌本来是不分家的。《诗经》中的诗基本上可以视为歌词。歌词是为歌曲服务的,所以我们看到《诗经》中——尤其是《国风》中——有大量的重章叠句。以大家熟悉的《蒹葭》为例,“蒹葭苍苍”、“蒹葭萋萋”、“蒹葭采采”三段,除了韵脚,文字的变化很小。用音乐术语来说,重章叠句中只有第一章是主歌,其他都是副歌,采用这种形式主要是为了配合音乐,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章节的变换中包含了经学的隐微或文学的巧思,但那主要是配合音乐的副产品,就像蛋糕上插的蜡烛。诗、歌结合,使诗可以依靠音乐的韵律,我们常说“哼歌”,歌首先是哼出来的,然后才会想到歌词。阅读本文的读者不妨想想自己熟悉的流行歌词,比如“小船静静往返,马蒂斯的海岸”,是不是搭配音乐才能唱出来?我想很少有人会清口不配乐地念歌词吧——那样做就太尴尬了。
作为歌词的诗延续了很久,汉代开始的乐府诗就是典型。但也有诗从歌中独立出来。这样的诗有种专门的叫法——“徒诗”,也就是不入乐的诗。徒诗无法依靠音乐,作者必须探索文字本身的韵律和节奏。真正的文学就在这里生根发芽。诗人们在专研诗道时,发现可以通过调整语音的组合增强诗歌的悦耳程度,如沈约在《谢灵运传论》里所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后人由此发展出了近体诗的格律。但这又使诗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依靠音乐性的老路。套用庄子的话,音律只是“人籁”,文字本身的语感才是“天籁”。
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渊明和谢灵运之间存在着“天籁”和“人籁”之别。谢灵运将音律用于诗歌,陶渊明则弃之不顾,专注于文字的内在韵律。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谢灵运的诗在音乐性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在当时谢诗远比陶诗悦耳。但有一个要素改变了一切,那就是时间。从中古到现代,一千六百年过去了,语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现在用普通话、甚至用保留古音元素较多的南方语言,都念不出谢灵运的妙处来。而汉语的文字是延续的,虽然有文白之别,我们仍能感受到陶渊明的“天籁”。
陶渊明的继承者
陶渊明的“天籁”有没有传人?应该说,每一个真正的大诗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籁”。那么,有谁较多地受到陶渊明的影响?前面提到的韦应物是一个。他可能是历来名诗人中学陶渊明学得最像的,不过正因为太像,让人失去了探讨的兴趣。我觉得有一个大诗人值得讨论,那就是王维。
我们很容易将陶渊明和王维联系起来——两人都是隐士,都写田园诗,都很“含蓄”。但我以为,就诗论诗,他们是形似而神不似的。关键在于,王维在诗中尽量隐去自己的情感,纯以外境表达,而陶渊明从来不掩盖自己的情感,外境也从来不是主题。比如“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孤云显然是心境的投射;“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桑树显然是宗国的象征;即便是“悠然见南山”后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也显然是悠然心境的外现。所以我也不能同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作为“无我之境”的例子——王氏说“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那么陶渊明此句何尝不是以我观物呢?当然说陶诗是“有我”也不恰当,它的重点不在我与物的相对,而或可称之为“唯我”。我们不妨顺着王国维的话脉说,“唯我”其实是取消了物的独立,根本不屑于像“有我”一样把“我之色彩”投到物上——“物”本身就是我的一部分。

董其昌书陶渊明《饮酒》(局部)。
陶渊明之后的诗人,谁最配得上“唯我”的称号?李白。我认为李白才是陶渊明真正的传人。虽然李白嘲讽陶渊明“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不过这显然是他笔下常见的“尊题”手法,毕竟他连孔子都嘲笑过。陶渊明与李白也都是酒之名人,李白经常在酒的话题上致意陶公。虽然他们的性格是如此不同,在诗上却有令人兴奋的相似。翻开《李太白全集》,迎面而来的是一首古风:“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显然仿自陶渊明《饮酒》之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连“狂秦”这个词都一样。说到“唯我”,怎么能不举李白那首著名的五律呢?“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青天无片云的情景,枫叶落纷纷的意象,都是直笔白描,却又是心境本身,天地间除了诗人的情感与意志,更无其他。他和陶渊明一样,得到了“唯我”的心髓。
“千载如晤”
文学的发展和生活的发展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在尽量减少功能的部分,增加效果的部分。农业时代生产一件产品需要一百个人、一百道工序,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文学追求的是让读者享受高光时刻(这里的“享受”是广义的,看悲剧也是一种享受),为此必须要把前戏做足。如何减少前戏,或增加前戏的趣味——借用禅宗的话,“斩断葛藤,一超直入”——是文学家们努力的方向。在这一点上,陶渊明展露出极高的天赋。他寥寥数笔就能会心一击,比如写春天的田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在同时代的诗人还沉浸于描摹形状光影时(其中大多数描写已被摄影淘汰),他写出了一种只有文字才能表现的神韵。苏东坡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此论至确。
陶公诗中不少词下得不俗,经常搔着读者如我的痒处,比如“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意思很寻常,但“摆落”一词放在这里,就让人读了说不出得快活。说起来我的书架上一直摆着本陶公的诗集,不知翻了几百遍,现在仍时不时抽出来,在夏日的午后,就着窗外的绿色,靠在沙发上,随手翻到一页,心中默念,有时念着念着就睡着了,诚如陶公所说,“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今年从四月的第一天开始,我宅在家里做了两个月的羲皇上人,又翻了十七八遍陶集。陶公和我相隔一千六百年,他在浔阳,我在沪上,却常常心有戚戚焉。两个月里,种菜师傅没法上门(按照古法,我应该称之为“荷蓧丈人”),院子里的菜园杂草丛生。有一天我拍了张照片上传到朋友圈,至少有五六个朋友用陶公的名句“草盛豆苗稀”评价了我的菜圃。陶渊明像南山一样,不经意间,又一次悠然进入了我的视野。
作者/程羽黑
编辑/朱天元 张进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