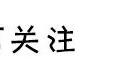老家的灶
文/朱克俭
1
老家官庄,最美的,是水。
父母亲各自的祖屋之间,隔一个大水库,青山环抱,碧汪汪的一片。
父亲家门口,一曲石阶下去,旁边便有一井。井出奇的浅,透明,看得见底,挽袖伸手,摸得到底。不像城里的井,还有我后来下放的乡里的井,黑咕隆咚,两只吊桶由缠在滚筒上一圈又一圈的绳子扯着,一上一下,转三五圈才听到桶底打着水响。老家的井水,是蹲下来,俯身就可以双手捧起来喝。奇怪的是,水清井浅,却取之不尽。
父亲家背后,是用来洗衣洗菜洗脸的山泉水。山里的大竹,一劈两开,敲破竹节中隔,便成水槽;再用瘦点的竹竿,三根一扎,叉起,一个叉顶着一个转折;九折悬泉,从山上不见其源的隐没处,汨汩引来,直到屋檐下。最后一截水槽,不用时一拉,水流便中断跌落,跳下山去。用时一推,又接驳过来,漱手溅足,凉浸浸的。
父亲家在水库的山岰里,母亲的娘家在水库的大坝下。出门的旷地有一眼鱼塘,朝晖、夕阳、夜月,流萤飞窜,俨然另一番水景……
但老家最使我难忘的,并不是形态各异的水,而是家家都有的土灶。
灶,才是山水间,农家的魂。
那一派清凉之中的点点温暖。
2
我想,现在的孩子,不,现在中年以降,生长在微波炉燃气炉时代,见过煤火炉的尚且不多,对于柴火土灶,恐怕已视同文物。
五十多年前,在省城读小学的我回老家度暑假,恰逢外婆家拆旧建新,便亲眼目睹了打土灶的过程。
乡下建房是全民参予,邻里乡亲都来帮忙。只有立门、上梁、建瓴之类的关键环节,须高手指点。
倒是打灶,得全程请够格的泥匠亲自动手。灶,说随意很随意,三块土砖架口锅,点几根干柴,火能噼里叭拉尽情地烧就成;说神圣又神圣,民以食为天,居家的灶,坐镇后屋,火须稳须静,旺而省柴。据说,灶台定位、灶口朝向、烟筒曲直等,都有讲究。讲究又无书无图,不事言传;中个巧妙,全在匠人心里和手上。师傅不真,就很可能火不旺烟旺。
基础是土砖砌成。腰子形,约一米高,一米宽,两米长。上开两个锅孔,夹两个瓮孔;腰身凹侧面开灶口,凸面是掌锅位。
基座垒成,再以泥饰面,泥内要伴入纤纬作筋。巩墙作筋的是棘条,打灶作筋的是干草,铡成碎段。泥不是泥浆,是润透的粘泥。太湿,干后会裂。泥不是抹上去,而是打上去。打灶打灶,不打不成灶。特别到面子,是用一种木制的手拍,隔段时间拍一遍,啪啪啪,泥越打越熟,渐打渐干,千锤百炼,直至打不动形,打出浮泛的光泽来。
我们小孩子,有事没事也允许参与其拍打之中。
3
对于小孩,灶成后的乐趣,不在掌锅的台面;而是一把小凳,坐在下面的灶口。
点火是要技巧的。
茅柴扎成小把,洋火一点,明火很可能转暗,这时需要吹,对着隐火,嘴撮圆,舌头退后,随着鼓腮吹风向前吐,轻抵圆唇,扑的一声,风骤起骤止,明火便应声腾起。
然后,把小柴把轻搁灶口。灶膛里已预伏膨松的茅柴。拿起火叉——木杆套着铁叉的架火工具——把已燃的小柴把塞至灶膛的柴下,抽出火叉,把灶膛的茅柴轻轻挑起,瞬间,便会满膛旺火。
但也有失误的时候,引火再度转暗,只剩点点火星。这时,又得吹。取专门的吹火筒——打通了关节的空竹,一米多长——伸向火星闪烁处;吸足一腔长气,由轻到重,慢慢吹。看着火星越来越红,越来越亮,面积在扩大,突然明火腾起,映得一脸通红。
这吹,急不得。若始吹过猛,可能反把火星吹灭,灰烬扑面;若后劲不足,又可能眼看着将燃未燃之际,前功尽弃;若气竭倒吸一口,则必为烟炝。
加柴也有技巧。
当年,虽在山里,树是不能砍的,烧柴多为茅柴。记得第一次跟表兄弟们上山砍柴,竟是伏地割草似的,失望至极,柴刀一丢,不砍。后来才渐成每日早课。
茅柴最大的缺点,是不耐烧。干透的,火一蓬就烧没了。但往灶膛里添柴,又不能添得太勤太多。人要真心,火要空心。灶膛塞得太满,会但见浓烟不见火,柴烧了,锅不热。所以,我们老家称加火为“架火”,即把底灰掏空,柴架起来烧。柴撩得太空也不行,火舌呼呼的一下窜出灶口,火星四溅,吓得人尖叫。锅里还来不及反应,一把柴就没了。
掌锅人遇此忽冷忽热,该旺火时熄了,该文火时疯烧,其心烦意乱,可想而知。
好在舅母是从不发脾气的,最多笑眯眯放下锅铲,从凸面转至凹面,弯腰接过火叉,示范加一灶火。同样一把柴,她塞进去,火烧得又稳又久。
我架火是玩,平常多是外婆专职。看她架火,无需舅母提示,什么时候火大点,什么时候火小点,靠里靠外,靠左靠右,可以让舅母得心应手得一声不吭。天冷,出工的劳动力回家,有时随意把手往灶口伸一下,她老人家还能及时让灶口吐出点火舌,舔到手上,那暖的,不止是手,而且是心。
如今想来,那手上的火候,简直是艺术。
最吸引孩子们亲近灶口的,是孩子们肚子里的小九九。在灶膛里厚积的火灰里,总埋着些孩子们各心照不宣的秘密。
在挖红薯的季节,可能埋着红薯。尽管老家的红薯占口粮百分之八十,一年吃到头;但火灰里煨烤出来的新鲜红薯与充满棺木气的干薯丝,是大不同的。
在挖芋头的季节,可能埋着芋头。煨烤出来的芋头,皮很厚,绽着缝。烫得两手交递地拍尽灰,掰开,一股热喷喷的香气顷刻把秘密泄露无遗。
最让人激动的是摘毛栗子的季节。毛栗子连刺壳埋进去,不知什么时候,突然一声爆响,有人惊,有人喜。取出来,或用石头砸开,或置于脚下,破鞋底踩着一揉。或躲着独用,或公开分享,其乐无穷。
这些小九九,大人们多不干预。最多是毛栗子爆响时,舅母或者外婆若无其事的喊一句:
莫炸哒眼睛哦!

4
大人们的注意力,除了灶台上正儿巴经的一日三餐外,是从梁上吊下来的挂钩。
过年的时候*了猪,或者从水库和塘里网了鱼,通常是要吃一年的。舍不得吃的,就切成条,干干净净悬挂在灶口之上,慢熏慢燎,渐成黑乎乎的腊味。
民间很多事,初始的动机与沿袭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象腊鱼腊肉,最初可能是种无奈的保存方式,结果成了一种味蕾习惯。
二十多年前,我在香港中银大厦跟王军先生吃过一次饭,听他说起他父亲对家乡腊肉的酷爱,不亚于抽烟喝酒,每年,他都要差人到浏阳老家收购一批柴火灶上经年累月的正宗腊味。
我的老家正是浏阳紧邻,想必其味相当。
挂钩上的腊鱼腊肉,看似一团漆黑,似乎还有黑绒绒的烟毛;吃时洗净切开,却是金黄油亮。吃腊肉时,必是农家盛大的节日,晚上,煤油灯映着大大小小的油嘴,幸福的笑容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腊味并不是家家都有。听父母讲,老家曾有过木鱼木肉,雕得真的一样,过年节时是真鱼真肉的代用品,也放上豆豉辣椒蒸着,也上桌高喊:吃吃吃。我不知道是否也有将之挂熏,以代腊味的。
母亲说,外婆曾教导她:家里没有米,灶上也要蒸出气。
在我们老家,灶是里子,也是面子。
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袅袅炊烟,远看一样,近观,未必相同。
我做客老家那年,梁上挂了点鱼肉。可见,不是最穷的家,或不是最苦的时候。
巧妇难为无米炊,米少也难,油盐酱醋,灶主无不操心。
我们老家,灶主是堂客——灶屋里的主,堂屋里的客。听母亲说,父亲那边,过去堂客们吃饭是不能上桌的,菜端出去后,回灶屋吃。大家族里,疼媳妇的男人往往把舍不得吃的菜藏在饭底下,借到灶屋䉕上添饭之机,偷偷塞到自己媳妇碗里。我回老家那年,已没有这样的规矩。倒是在外婆家,看到了另外的规矩。
外婆是跟湘舅家一起过。灶上,一饭䉕红薯丝里,每餐只有一小团白米饭,那是舅母专供外婆享用的。许多年如一日,舅舅家大大小小十来个孩子,从来没有谁在专供中蹭过一点。
在我的记忆中,舅母是天下第一贤惠的。在她终日微笑不语的操劳中,你几乎感觉不到生活的艰辛。以我今天的阅历,我深深的知道:当年,为着上老下小,她默默扛过的艰辛,不言而喻。
前两年,她家六姑娘——当年我们捉泥鳅时,她是专门提个小桶紧跟后面,剪男孩头穿花衣服的假小子,一笑两个细酒窝,像她妈一样——现在也是做娭毑的人了,她告诉我,她母亲是九十七岁过世的,临终毫无痛苦;上山前后大雨,就那天,阳光灿烂。
我说,那是福报。
5
老家的灶,火尽其用。
一锅蒸饭,一锅炒菜;上有熏的,下有煨的;一餐饭熟,中间瓮罈的水也开了,随用随加;菜出锅后,拨灰埋好火种,锅里顺手倒两瓢凉水,饭毕,洗碗水就有了。
火种存而灶犹热。
常言道,水火不容。在老家的灶屋里,水火是相亲的。什么时候,若有谁在火灰深处发现有只螃蟹,也不足为奇——定然是哪位小兄弟在山溪水的小石板下捉来的。
山里山外各种形态的水里,都有老家土灶上,那心心念念的美食。
永远忘不了,我们大大小小一群孩子,背负夕阳,在田港里涉水网虾捉泥鳅,然后奔回灶边,簇拥着外婆和舅母的温馨……
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家偶有电话:来吧,至少,我们现在都不愁吃了。
我早已只能做客的,记忆中的家乡,夏有水的清凉,冬有灶的温暖。
柴火土灶,不知现在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