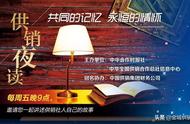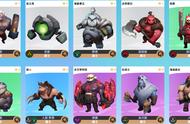“百年耻,多少合约羞成。烽火连迭,无夜无明。小命儿似飞蓬,报国心遏云行。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早听得卢沟桥上炮声隆!多少人血泪飞,向黄泉红雨凝。飘零!多少人离乡背井。枪口上挂头颅,刀丛里争性命。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呼苍穹。说什么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珠泪倾!又何叹点点流萤……”像《红楼梦》开篇就给每个角色写判词一样,热爱元曲的宗璞给每一卷小说都写了“判词”,用序曲定下小说的基调。《南渡记》描写了“七七事变”后北平明仑大学(原型是清华大学)教授孟樾一家的生活遭际,以主人公随学校南渡长江,避战乱于滇首府昆明为情节主线,写了国祸战乱中高知阶层的百态。
《南渡记》出版于1988年,彼时宗璞已年近花甲。后记中,她说,长期处于创作状态,身体吃不消,有时一歇许久。“这样,总是从‘野葫芦’中给拉出来,常感被分割之痛苦,惶惑不安。总觉得对不起那一段历史,对不起书中人物;又因专注书中人物而忽略了现实人物,疏亲慢友,心不在焉,许多事处理不当,亦感歉疚。两年间,很少有怡悦自得的时候。”

但在当时,文坛兴起的是争先恐后的现代主义文学实验,古典主义艺术趣味浓厚的《南渡记》不可避免地被文坛所冷落。直到《东藏记》出版以及文坛风向转变,该主题小说才开始备受关注。
《东藏记》写得更难,且一写就是七年。1990年冯友兰去世,接着宗璞大病一场。1993年她才开始动笔,因病魔的折磨,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在2001年出版了《东藏记》。当时,宗璞的目疾逐渐加重,做过几次手术,虽未失明,却已不能阅读,写作全凭口授。2005年宗璞凭《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东藏记》描写的是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樾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以及大学里的修学之苦,对教授间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态、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和情感,都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部小说有妙趣、有真情。到了《西征记》则重点描写明仑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历史。宗璞笔下的滇西之战别有气势,在硝烟炮火里,青年学子们为国捐躯,真是“壮哉书生”!
《西征记》成书于2008年,写作之前,宗璞访问了多位从军学子和军界人士,他们不同角度的故事和感受,让宗璞有了足够的材料和认知去写战争。宗璞说,她的胞兄、自西南联大参加远征军任翻译官的冯钟辽,也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述亲身经历,对写小说有很大帮助。

《北归记》则再现了明仑大学师生结束八年颠沛流离,返回北平后纷繁错综的现实生活。抗战胜利后,内战烽烟又起,小说把历史巨变前夜,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父一辈的担忧、子一辈的情缘,都凝聚在一起,温暖而沉重。这部小说是宗璞在和疾病的斗争中完成的。写后半部分时,她患过一次脑溢血,虽缠绵病榻,仍是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口授一会儿,每天都会创作一些。
《北归记》距离《西征记》已过去十多年,很多跟随宗璞几十年的读者,以为再也等不到这部收官之作,小说的出版让人高兴、欣慰,又很悲伤,因为故事走到了结尾,书中许多人物已逝去。
30年岁月,追寻知识分子精神之旅
《野葫芦引》四卷本涉及数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变迁与聚散,其中个性鲜明、清晰的人物角色近百位。这部长篇最大的看点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群体肖像,她用细节呈现了知识阶层在国难中的痛苦和民族气节,他们的谈吐、风貌和举止跃然纸上,呈现了“我辈书生,为先觉者”的精神追求。与此形成对照,小说也写了汉奸形象,呈现了他们苟且求生的懦弱灵魂。小说的另一个看点,是对年轻一代群体的塑造,尤其是对嵋、峨、玮、玹子、卫葑等年轻人浓墨重彩的描写,可谓“出走八年,青春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