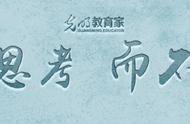第一,“天命”转化为“定命”,“汤武革命”等政治因素虚化,而“定命”也遭遇挑战,善恶的天定被打破。武王伐纣这一事件仅仅成了故事的“引子”,抑或出于“母题”而不得不有的“背景”,完全不影响后续故事的展开。政治不再是故事讲述者关注的中心。哪吒面对的是“定命”,但此种定命也没有终极的决定力量,是可以被后天的“教化”打破的。此外,善恶也不需要由“命”来保证,善恶不再具有古典的形而上学基础。
第二,女性形象不再缺失或无力。《封神演义》中的殷夫人除了爱子之心别无表现,母亲对子女的塑造不具备决定性力量,而女性自身也完全局限在“家内”。《哪吒闹海》则完全将母亲“隐退”。在各个版本的有关哪吒的影视作品中母亲具有地位的是TVB版的《封神榜》,其中的殷十娘学法于女娲,协助李靖征战沙场,同时以“母爱”守护并感化哪吒,最终塑造哪吒的不是“父”,而是“母”的牺牲。比起 TVB版的殷十娘,《哪吒》中的殷夫人则与李靖的地位更加平等,不再是辅助性角色,她披挂上阵、斩妖除魔,能力不在李靖之下;性格则突破了前版殷十娘的“柔”,更加刚柔相济,在事业上更加积极主动,对待“魔童”则又充满了柔情。此外她身上还多了事业与亲情的矛盾,为了事业,母亲不能时刻陪伴在孩子身旁,这也是以往版本所不具有的。新版中的母亲可以说是当代某种对女性形象“想象”的一次影视展现,至于这种“刻画”是否正确则有待检验。
第三,“师”的作用完全发生了变化。比起《哪吒闹海》,“师”在《哪吒》中彻底反转,甚至“弱化”。太乙真人、申公豹都被娱乐化了。太乙真人像是一个“段子手”,不停地“讨好”学生,而无丝毫“权威”。同时,师的教化在哪吒和敖丙那里都不是决定性的力量。真正改变两人命运的都不是老师,老师没有在学生心灵当中留下有效的印记,老师在孩子命运面前是“辅助性”的,而非主导性的。这与《封神演义》和《哪吒闹海》都不一样,根源上则在于叙事基调的差异,在价值基底上《哪吒》与之前版本已经分离,是彻底的“去政治化”形象。这样的老师形象已经远离了古典的“东亚世界”,也远离了革命语境,其形象更接近好莱坞娱乐片,也符合当下某些情景。

第四,朋友一伦得到了强化,但朋友的内涵却与古典发生了变化。《哪吒》中激发哪吒“魔性”的与其说是“命”,不如说是人们的“偏见”。哪吒渴求得到朋友,却得不到同龄人的理解,进而激发出他的“叛逆”。而在拥有朋友之后,哪吒则换了面孔。故事中,敖丙不再仅仅是一个反派小角色,他与哪吒成了“朋友”,成了故事的另一主角,而朋友关系也深刻影响了二人的行动选择。面对“命”的不仅有哪吒,也有敖丙,朋友共同面对命运,也一同尝试“改命”。当然,此种朋友关系依旧是现代的,是两个“孤独”个体的相互吸引造成了友谊。这种友谊不是古典的“同志曰朋”,更非革命友谊。
第五,比起前面几种变化,更为深层的差异是“敬”的消失,“爱”完全替代了“敬”。在《哪吒》中,“爱”和由爱产生的牺牲成了改变“命”的主导性力量。哪吒与父母只剩下了“爱”,而没有了“敬”,我们没有看到父亲以“敬”约束“顽童”,更看不到哪吒对父母的“敬”。而此种爱敬模式,也更符合当代家庭形态。当代核心家庭的“亲亲”性更强,爱更浓,同时“尊”的权力则无法声张。没有一个父亲可以名正言顺地诉诸“敬”而要求其家内地位,此种要求也得不到社会性的支撑,只会带来父子间的冲突。父母对子女的“规训”只能以“爱的名义”,家内秩序只能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而子女对父母也只有“爱”而非传统的“报”。由于“敬”的退场,父子关系的实质也就发生了转化,进而政治秩序与家内秩序的联系也被斩断,因此,影片不需要一种政治关系作为情节支撑。敖丙那里“敬”还有残存,当然此种残存并非以正面形象示人,反而成了一种“负担”。

由于以上种种变化,面对命运,起决定性力量的成了“亲”。此种“亲亲”的强化有着思想史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晚明思想中,由于阳明学的兴起,“亲”的地位变得突出。但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则是影片中反映出的“亲亲”压倒“尊尊”的根源性力量。
当然,亲的力量在哪吒那里是正向的,而在敖丙那里则成了负担性的“家族”。为了一个背景性的“家族”,敖丙要做出自我牺牲,进而造成自己命运的改变,而哪吒则不具有此重负担,父母对他的要求相对简单,甚至这种要求最后完全可以化约为爱。而这也是哪吒与敖丙的“一体两面”。哪吒与敖丙的一体两面,表面上与“善恶”有关,其实与原生家庭密切相关。
对哪吒来讲,对改变命运起决定性作用的“亲”不仅有母亲,更有父亲的作用。故事中的李靖以其实际行动“控诉”了当下社会中的“丧偶式抚养”。在革命中退场的父亲在“化魔”中回归。更为有趣的是,影片中最后做出牺牲的模式并非一般想象的“母爱”付出,而是父亲主动要求牺牲。但由于“敬”的缺失,此种父爱其实已经“母爱化”了。拥有性别差异的父母在“亲”面前,其对子女的爱没有实质性的差异。这其实是核心家庭的基本形态。
有学者指出,为了叙事,电影中的哪吒和敖丙均“独子化”了,而故事的逻辑也更符合此种独子化的核心家庭的人伦关系,这也是为何影片能打动很多当下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种核心家庭中,父亲重获尊严,但却不是依靠“尊”“敬”,而仅仅靠牺牲性的爱。当然,父的牺牲在哪吒与敖丙这里同样是“一体两面”的。龙王的牺牲并没有赢得尊严,而只是加重了敖丙的负担。影片似乎要求的是一种“纯粹的爱”与“纯粹的牺牲”,而不能夹杂任何多余的诉求。龙王的牺牲与敖丙的命运,其实留下了近代对家庭、家族批判的尾巴。但总的来说,在《哪吒》中礼教不再吃人了,因为礼教消失了。

作者简介:赵金刚,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宋明理学及中国古代历史观。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注:原文载于《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2期。此文有删减,感谢作者授权推送。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参考文献:
[1许仲琳.封神演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赵金刚.朱子思想中的“鬼神与祭祀”[J].世界宗教研究,2017,(6).
[3甘阳,张祥龙,吴飞.家与人伦关系[J].读书,2017,(11).
[4]张晖.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封神演义》中的忠孝与武王伐纣的合法性[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