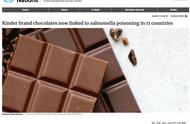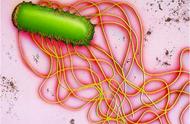笔者很久没有做梦,也几乎不再在梦中惊醒,惊醒后记梦,更是不可能了。
梦,总在解释着什么,或是往生(科学一点,千古基因的记忆表现),或是来生(基因传递的走向),或是一种自我的换位表达。
若是让三年前这个梦失于笔端,也没什么不好。但笔者偏偏就记下来了,也在时光漫漫流逝中,种种端倪似乎得到了很多印证。这种折射的证明,不可思议,又让人深感无力。

——这是之前取的标题,现在想不出这个标题的用意。我的意思不是说为什么这样取,而是这个标题,又会在未来,证明什么道理,或者根本没有道理。
家里没人,村庄里也不见人和畜生的影子。村庄的路依旧长在那里,通向该通向的地方。
我实在是穷困潦倒了,或者说,不管怎样,为了生存也好,为了挥霍也好,必须要出门借点钱。我给表姐打电话唠了半天,终于算是轻松地借到了。
莫名其妙我就踏入一家印象中并不存在的破杂货店。杂七杂八的东西摆满所有的货架,没有一件我想买的。我看见整村的人都挤在这破旧又狭小的空间里,闲谈、争吵,却难得的安静,就像葵花林中的蝉声一样(编者注:“葵花林中的蝉声”详见史铁生《务虚笔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很久很久甚至几个轮回也可能只是一会儿,所有人都忘了自己的存在,在破杂货店的各个角落安静地消失在各个角落。
我惊觉时进来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或者说,是在那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进来时我才醒来。瞧她的言谈举止像是一个小学生,而单看她的年纪,是个中年妇女无疑了。她背着破烂的粉色卡通书包,漆黑的脸不知经历了多少风尘,已看不出本来的肤色。她站在我右侧,和我交谈了几句,无关事物,也无关内容,不知谈了多久,也可能根本没谈。反正我已了解,她打算从今以后改变现状。我便同她一同拥向柜台,她伸出一根粗糙的指头朝货架点了半天,像是指点江山,把身上能换的全都换了个新。这没什么,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这真的没什么,她要多少,我也理所当然给她多少钱。最后,她觉得还需要有一个包包,别的女人都喜欢的那种刻着什么字母的皮包,就功德圆满。说这话时,她的脸上刻着一副漠然的表情。我想象不出乞丐穿戴奢侈高贵的样子,想象不出她这辈子还可以不是乞丐。但她的天真真的让人于心不忍。全村的人一直很安静,安居于自己的角落纹丝不动。
老板娘终于现身了,说,这种高档的包店里不多呐,现在没几个啦。那乞丐从书包里拿出一沓钱,一眼瞟去我就知道那是一万零五百,五百是散的,大概就是我前面给她的。老板娘取下一个挂在生锈铁钉上的带银链的白色包包,标价一万零几百几十几,摆出一副仁慈和体谅的嘴脸说道,给你们凑个整,一后面四个零!我拼命还价,又拼命让老板娘送点什么或什么。我问乞丐想要什么,她说都行,眼睛始终死盯着那个包。突然我左耳传进一个熟悉的女声,满带鄙夷地说,别再还了,跟傻子一样。说完就不见了,一说完我也让它不见了。老板娘送了电动玩具,送了绒熊,其他能送的都送了,满脸狡猾地笑着,手里把一塌钱展开成扇状。我越看越不安,越不想把那沓钱给她。内心的躁动如洪水决堤。我冲过去一巴掌拍过去,钱洒了一地。老板娘箭似的蹲下身子,双眼闪着金光,拼命地在地上抓钱,最后差不多是坐着、躺着在扒钱。我大喝一声,把那叠散钱还给我!我气极了,那可是我好不容易借来的。我夺过属于我的钱,心情遭透了,又随手抓起地上一把粘着水或者口水的钱,砸向老板娘。而那乞丐只是轻轻地抚摸着那些玩具,眼神游离,此刻世界已经与她无关了。

我从杂货铺走出来准备回家。我认得哪条路通向家门,也认得所有能通往我家前门或后门的路。我走在家附近的池塘边上,迎面碰见小叔和表姑父。姑父手里拎着几斤猪肉兴许还有猪头,口里念念有词,时不时咆哮哭喊,都是酒坏的事,要是老子不喝酒,啥事也没了。我跟着他们一起走,慌慌张张像是在逃难。好像很近,又感觉走了很久。最后我们竟然走进了某位朋友家。刚进门,姑父就开始喊,娘,你下来吧,都是我的不对,我不应该喝那么多,也不该打你骂你,我给你赔礼了。说着便把手里拎的往高处举了举。娘,别哭了,快下来吧,都是我不对,我给你赔礼了……我只听见楼上哭声凄惨,不忍闻。姑父开始边哭边喊,娘……
我和小叔两人走出来,一起回家。他说,唉,她一直在说啊,把妻子女儿带回家看看多好,她可想见见孙女和媳妇了,她一直念着要抱抱孙女,夏天坐在庭院摸摸孙女的手,想着多见见媳妇。唉,要是我把妻女都带回来,这些事都不会发生了。他说,带回来又……唉……好像所有的事都很麻烦,麻烦得再也说不清理不顺。他说完就像个智者一样笑了,笑得很豪放,在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哭喊声之上更加惊天地泣鬼神地笑了。唉,还是回家吧。
我家右边有几级台阶,也许五级,也许六级。在这台阶上上下下20多年,每一集台阶都印下我无数大大小小的脚印,我却记不清它到底有多少级。小叔刚踩到第一级,就像踏入空潭,整个人立马失重似乎要落入万丈深渊。啊——他惊呼一声,浑身战栗继而马上跳了下去,我也跟着跳下去。他用配得上他的大肚腩的大嗓门吼着,哟,这半个破台阶,都被雪盖住了,害我踩踩空,吓出魂!我才发觉大雪纷飞,四界白茫茫一片。怪不得,一派荒凉。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静下心来只想自己的事。我站在正堂中间,两扇小窗似有似无的透进天空的暗蓝,死去的黄昏的暗蓝。世界好像突然暗下来,我也像是站在海域一侧,一不留神就会被风暴或海啸吞噬。我盯着那个滑盖的夏星手机,打开手机QQ,但并不是我自己的界面,而是一部似乎密谋已久的视频。画面中,看得见我之所爱和一个旧人重归于好,看得见他们的网名亲密度超过人之本身。看着他们亲密网名不停地变换着,每一组都是绝配,而我却眼巴巴什么都做不了。一屏之隔,距离有多远。
世界真的已经全部暗了,但黑暗光明都与我无关。我站在黑暗的正中间,只盯着全世界唯一的光亮,昭示着所有不祥的光亮。那种光亮,不是真的光亮。那种不祥,却是真的不祥。我来回走动,来回走动,在黑暗的正堂来回走动,比全身爬满虱子上刀山下油锅还难受。我心里焦躁不安,疼痛难耐。我想狂奔,我想狂叫,我想让大地把大山震碎,想飓风把海洋吹干。我挣扎、挣扎,挣扎不出来。
我持续痛苦,持续焦躁不安,持续挣扎,不知持续了多久,也不知还要持续多久,没完没了,万劫不复。我继续痛苦,继续焦躁不安,继续挣扎,已不知此刻已经醒着。
现在我就醒着,痛苦,焦躁不安,挣扎。回想此梦似有可取之处,遂起而记之,以备用所有存在的时间,待后遗症慢慢褪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