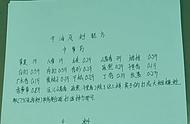——专访田聪明:一切为了履行职责
文/ 张垒
从去年至今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国记协主席田聪明先后出版了《一号工程:中国广播电视“村村通”开启记事》《中国电影业“大地震”:上世纪九十年代电影改革纪事》《我报道 报道我》三本专著。这三本专著既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也体现了田聪明同志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和党政部门管理者独到的人生思考。这些经历和思考对今天的新闻界和新闻工作者来说,同样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日前,《中国记者》专访了田聪明同志,请他和业界同仁分享做记者和从事新闻管理工作的经历、感受,以及他对当下中国新闻业如何更好地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思考。

文章刊发在《中国记者》时的版面图
中国记者:从去年至今,您先后出版了《一号工程》《中国电影业“大地震”》《我报道 报道我》三本书。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样三本书的?事先有什么规划吗?这三本书之间有什么联系?您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田聪明:严格说,我不是出书,而是将自己亲历、亲闻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记下来,留给后人。这是早有的想法。我在离开内蒙古的时候,一些同志把我在内蒙古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谈话等文稿收集起来,准备出版。当我又从西藏回到北京,他们已经把收集好的文稿交给了出版社,并送我审看。就在这时,我看到有一本老同志写的回忆录。有一个下海的同志来看我,说这位老同志出这本书,出版社有个条件:作者自己必须购买两千本。有人为此找到了他,他就把这两千本书买下了。我说,你这两千本书怎么卖?他说:“嗨!卖什么呀,就往纸堆里一扔。”我受了很大刺激:你写的内容要有东西值得人家看才行。我马上通知出版社,把文稿全部收回。出版社还是希望出,我表示感谢,但坚持以后再说。《我报道 报道我》中就有一些从中选的文章。关于电影改革,村村通广播电视,我在职时就有一些同志反复提到,希望我能写写这些事情。我到新华社工作以后又有同志建议我写书、出书。我曾说:我要写,但写些什么、什么时候写、怎么写,要考虑。我记得周总理讲过,不懂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由此讲到领导干部都有一个责任,就是把自己经历的事情真实地记下来留给后人。我理解,是要记那些有意义的事。所以,我退下来了就有点时间考虑这些事了。村村通广播电视,从我提出到离开广电,抓这项工作也就是三年多时间。其中的讲话或者不少文件,都是我自己写的。包括在候机室、飞机上写提纲,参加小组会、和大家谈话,再充实我的提纲,讲完后整理录音。正式部署“村村通”的时候,我和国家计委的负责同志一起在宜昌开会。在这个会上,一位湖北省副省长挨着我坐,他发了句感慨说,你这个领导有些不一样。第一,你从头到尾参加会。第二,你的讲话没有稿子。我是拿着笔记本、看手写的密密麻麻的提纲在讲。但他觉得讲得比较实在。因为在去之前,我又到湖北农村作了些调查,其中有一天跑了13个小时。到下面去,就是亲眼看最基层的听众、观众听广播、看电视的实际情况;参加会,就是亲耳听各方面的意见。我讲话,就是针对这些讲做什么、怎么做。1998年,我要开“村村通”现场会,当然住在县招待所了,可上下都有人说不行。我说怎么不行?听下来就是个筒子楼,房间里没有卫生间,洗澡要到另外的地方。我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我和大家都一样,只要我没有意见,大家就不会有意见。《我报道 报道我》这本书名及内容选择,我在序言里写了,完全是个突想。里面收集的一些文章我记不起来了,最典型的就是2004年俄罗斯塔斯社驻京记者对我的采访:《网络时代通讯社的作用与发展空间》。还有我组织战略组搞内蒙古的发展战略规划,都是后来“翻纸堆”发现的。除了秘书没有再让别人去找,去征集。我的想法就是,把我经历的一些有点用的东西如实地记下来,留给后人做参考。这是尽我最后一点责任。所以,我一般都附一些反映各方面意见的东西,尽可能比较完整、真实。毕竟我已经72岁了。对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先易后难,做一个算一个。十六大以后,中央领导提出要对省级以上各媒体老总进行培训,并要求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去讲一课。要我讲课,讲什么?我在2002年新华社民主生活会上有个发言:《学习、调查中思考的几个问题》。我一到新华社就说过,三年以内以调查研究为主,以谋划长远一点大一点的事。三年是宏观量化,不是具体量化。所以到2002年8月,开民主生活会的时候,我到新华社两年零两个月。因秋天要开党的十六大,十六大之后都要贯彻,这是个时间节点。新华社工作怎么做?有什么新想法?就是怎么贯彻十六大精神?于是,我就把在学习、调查中思考的一些主要问题提出来,在党组民主生活会上酝酿。先在党组讨论、修改,后又发全社各级征求意见,最后形成了共识。因为有这个基础,我马上就想到这个可以讲。不然讲什么呢?讲舆论导向,讲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事情党代会的报告和中央领导都讲清楚了,我们学习贯彻就是了。于是我就报了个题目:《关于新时期新华社改革发展中的若干思考》。因为,第一,讲我们如何把十六大精神和新华社的工作、职能结合起来,讲怎么履行好职能,怎么在履行职能中贯彻好十六大精神。有话讲,且是实话。第二,大家都是做新闻工作的,讲共同语言好。第三,各媒体都是新华社新闻信息的用户,正是与老总们沟通的好机会。所以,我第一讲新华社的职能是什么?第二讲履行新华社职能的主要形式是什么?第三讲为了履行职能,改革发展中重点抓的几项工作。讲完以后,大家反映比较好。其实我就是写实,既没用那么多新概念,也没有多少形容词。王春荣(新华出版社原社长)曾希望我出书,题目为《一切为了履行职责》。我觉得挺好,但当时顾不上,后边准备出。主要讲增强新华社影响力的一个一个实例。现在有一本,马上就要出来,是用了我在先进性教育中党性分析材料的题目:《信念、忧虑、信心、尽责、自律——我的党性分析》,把我多年来有关党的建设、党的工作这方面的文章、谈话、建议整理出来,收入其中。另外,我想将回忆往事、缅怀故人方面的文章集纳起来,以《妈妈的心——一个儿子的忆述》为题出版。还有就是目前想到的题目:《做什么 像什么》,用“忆述”加有关文章,讲如何对待组织分配的工作及如何用主要精力做好本职工作等。

中国记者:您既做过新闻事件的报道者,也做过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既当记者,又长期在领导岗位具体推动工作和改革。您怎么看当记者和从事新闻管理工作的关系?记者的经历给您在领导岗位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田聪明:我从不愿意做记者到愿意做记者,是经过一番考察体验和思考做出的选择。最后的结论是,我非常热爱新闻记者这个职业,特别是新华社记者这个职业,觉得很神圣,也大有可为。这方面,我首先是从戴邦(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那里得到很大启示。写别的东西、做别的工作,和做记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当记者可以说是半路出家,当时首先感觉到的主要是区别,甚至感觉到自己可能不适合做记者。那时我从借调开始,到新华社已经一年多了,不少稿子我觉得写清楚了,可是一到分社采编主任或老记者那里看,就有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新闻要素不全。人家一提,我也觉得确实没有交待清楚。二是特点,即够得上新闻的事抓不住。就好像一个五脏俱全的人体,真正够得上新闻的,有的只有两脏、三脏,有的只有一脏,有的甚至一脏也没有。问题是你要把新闻抓住。你把五脏面面俱到都写一番,等于没有抓到新闻。当然还有一个表现技巧问题。新闻要素一定要交待全,前因后果关系要交待清楚;把有价值的新闻一定要抓住并要放在全国视野中,从对人民有启发,对实际工作有推动促进作用出发,取舍运用采访来的材料。另外,角度也要选好。我听说,有同志认为《我报道 报道我》的书名,用新闻的话说,就是角度比较好。我当时翻资料,看到有我的报道,也有报道我的,这是任何一篇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两个关系方。我一边看一边下意识地在换位思考,是源于换位实践。这个转换在现时很自然,可在当年却是很不容易的。我从做党政工作转到做新闻工作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可以说是学艺加偷艺:学艺,是听领导怎么讲,老记者怎么讲,他们每次怎么讲。偷艺就是先自我琢磨,如一篇东西,我写会怎么写?先写什么,后写什么。然后,我再看别人是怎么写的,和我原来的想法作比较,找出差距来改进。可以说,我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信心了。是戴邦把这个事情向我讲透了,我也真信了,真做了。他一一问清我原来做什么,现在做什么,有什么感觉。他然后就说:“小田,你行。第一,你很注意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而且你是学理的,比较懂。第二,你对实际情况了解比较多。”我参加工作后每年都下乡。他说这是最重要的。要我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发现新闻,然后放在全国衡量。这样,就能掂量出一篇新闻的分量。新闻的分量,就是新闻的价值。在实际工作岗位的经历对当记者有非常大的好处。他说我有基础,两年可以“上道”。那么,这两年怎么上道的?我是相当刻苦啊,每一篇东西都是在学习、调查、思考后形成的。我当记者时每年下乡两百天以上。我和农民谈,和老干部谈,和村干部、公社和县委*都谈;接着,到地里看,这是自留地,那是集体地,进行比较;再就是查历史资料。不论谈、看、查资料,都伴随思考,有的报道是走着坐着都在思考,几个月、几年在思考。《我报道 报道我》里的“补前人之过,立千秋之业”一文,那是我几年采访和坐档案馆,反复思考的结果。《我报道 报道我》里讲到的统计数字要整顿。1979年正月初十,我到内蒙古杭锦旗采访,正碰上开“三干会”。杭锦旗的土地分三类,一是沿黄河灌区,二是沙漠,三是丘陵地。我就问一个分管农牧业的县委副*一些数字。他立刻说,统计数字啊,是三分统计,七分估计,加起来就是实际(十计)。后来,我反复琢磨这个事情,觉得有道理。在我们那个生产队,公社来电话问会计:你们耕地已经耕多少了?下种下多少了?会计把电话放下,在房间里转上两圈,然后就回话,真是统计加估计。所以后来我写了一篇记者来信:《统计数字要整顿》。《我报道 报道我》里批评的东西不少。批评报道、舆论监督报道和以正面宣传为主并不矛盾。正面宣传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全党全民贯彻落实方针政策的实践。在贯彻的实践中,总是分上中下。贯彻得好的,好在哪里?贯彻得一般的,特别是贯彻得差的,差在哪里?指出这个差就是为了把它变好。这应该是正面宣传。所以,尽管戴邦认为我对实际情况很了解了,但一涉及具体就觉不够了,还要继续调查。我经常叫做学习、调查、思考。我曾经两年多一篇稿子也没发。无所谓嘛,无非是人家说你没有发稿。你要耐得住,不要怕。第一,不要老想着人家表扬你;第二,不要惧怕批评。落后就是落后了。我两年没有发稿,就是学习调查思考。可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到1978年以后,头版头条连着拿。现在我们的记者耐不住这个,这就叫浮躁。当然还有领导上的认识。对新华社记者来说,基础就是戴邦说的两条:把党的方针政策领会透,把实际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各层次的来龙去脉及相互联系了解清楚,然后,再出稿子。我有的稿子写了一个多小时,就发出去了。发出去就是头版头条。但稿子要有点特点,能自圆其说很重要,不能怕有不同意见。当记者和做实际工作,各自履行各自的职责,但目标是一致的。所以,都要能听不同意见。我经常讲我不怕有不同意见,就怕没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我可以问,你这个意见根据是什么?可以比较,这样确定新闻或作决策,才能比较符合实际。所以,现在当记者和做实际工作要多换位考虑。我为什么理解《舞台与银幕》报道电影改革的那名记者?因为报道总的倾向是对的,基本事实差不多,只是细看起来有些不准确之处,已经不容易了。如果你对一名记者要求他每句话都准确,就有点过了。我对记者的要求是:事实不能错,认识有点错是允许的;基本事实不能错,细枝末节有点出入是允许的。我作为报道主体,是这种态度。可是我作为记者的时候,我就要努力把基本事实了解清楚,细枝末节也要尽量想办法了解,表述上同样要比较准确。可实际上每篇报道一点错误没有不可能。这就是两个位置不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对别人要宽容一点、多理解一点。无论是做实际工作,还是做记者,很重要的是应该相互尊重,共同尊重基本事实。做实际工作离不开记者,因为他做媒介工作,通过它向世界各地传播信息,有利于推动工作,也有利于得到各方理解。反过来,记者更离不开实践主体,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多站到主体的位置上想事情。我最近写了篇文章,其中讲到,我1982年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时搞过一年城镇工商企业调查。当时,我要求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下去调查,从年初到年底,人财物、产供销都要跟踪了解。我把它叫“当厂长、经理”。必须站在他的立场、他的角度上,这样才能对主体了解得比较清楚。

中国记者:您做记者时的几篇报道,如《河套的希望》,还有那篇没有发出的内部报道《“包产到户”这个禁区必须“冲破”》,都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说,一代代的中国记者都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然而,不容回避,当前也有少部分记者责任意识缺失,您怎么看这种现象?记者应该有怎样的职业精神?
田聪明:这是认识有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记者的职责精神和职业道德。如改进新闻报道中的文风怎么改?记得四川芦山地震发生后,有篇报道说:地震发生以后,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后两句话可以去掉,无非是迎合省领导。什么叫高度重视?新闻是用事实说话,不是用这类形容词说话。怎么比较第一时间和第二时间?最好是直接说:地震发生以后,省委省政府领导马上赶到现场部署救援。这就行了。而且首先应该报道事情什么时候发生?造成什么样的损失?读者更关心的是这个事情本身。现在把虚假新闻查出来,新闻敲诈查出来,这都是必要的。然而其它的呢?记者应该自问:我的职责是什么?我履行了吗?在新华社,我和老南(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经常说,记者不知道这个事情就算了,知道了就必须报。至于怎么报?用什么形式报?是社领导要考虑的。作为记者,不报就是失职。这就是我对新华社记者的要求。自己的职责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停在嘴上不行,要具体。首先得弄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做到了没有?

中国记者:您书中曾经提到自己“意识深处有个割舍不断的‘三农’情结”。如您所提到的,农村和农民中的许多事受到媒体的关注越来越少,甚至有被边缘化的趋势。那么,作为新闻从业者怎样才能和农村、农民建立更深厚的联系?怎样更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呼声?
田聪明:我的“三农”情结可以说是“习惯成了自然”。不管做什么工作,我都首先想到这个。为什么?第一,我祖祖辈辈是农民,且在农村的最底层。从最底层往上看,各个层次看得都非常清楚。第二,我学了《*选集》,那是1960年冬天。毛选四卷多数是讲到农村。我在旧社会从最底层往上看,觉得天是人家的天,地是人家的地,我们只能受穷,不被人看得起,当然不会服气。看了*的著作以后,感到很受鼓舞。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农民运动”好得很,还说最干净的还是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第三,就是我上了大学,进了城,参加工作以后,逐渐感觉到城乡差别很大。最主要的差别,一是医疗,二是教育,三是科学文化,主要根源是贫穷。第四,就是当了农牧业报道的记者。当记者更深入地了解以后,我找到了解放后农民吃不饱肚子的根源:不是农民不会种地,也不是土地不生产粮食,而是解放后一度政策不对头。我当时报道的出发点就是这三句话。城镇化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农民有局限性,比如思想比较保守、有时目光短浅,主要是缺乏文化知识所致。没有科学文化,许多现象他解释不了啊。我为什么抓“村村通广播电视”?很多农民连县城都去不了,怎么开放?可是有了电视,他就能知道外面的许多事了。中国到现在根本的问题还是农民问题,或者叫“三农”问题。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讲到这个问题。我针对有人关于与农民实行“三同”已不可能的说法,引用了李昌平的一句话:“现在很多城里人对三农问题越来越没有常识”。现在很多城里人只知道为城市人服务,很多记者根本想不到这个。有一次列席国务院常务会,因当时猪肉涨价,讨论给城镇居民价格补贴。有位同志就问,那农民怎么办呢?农民吃猪肉价格也高啊。一句话问得大家都不吭声了。我为什么把“三农”问题叫做世界观?世界观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记者不与农民“三同”,没有这个常识不行啊。中央常说不要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根本问题就在这儿。脱离中国国情是最可怕的。脱离国情的主要危险就是忘记了“三农”。但如果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不了,你就不能说中国现代化了。来源:《中国记者》2017年12月27日。
**********
据媒体报道,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新华社原社长田聪明同志于2017年12月26日晚因病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74岁。

田聪明
田聪明同志在任新华社社长期间,也是《中国记者》杂志的编委会主任。今天,我们推送《中国记者》杂志2014年第8期专访田聪明同志的文章《学习、调查、思考:一切为了履行职责》,以表沉痛悼念之情。
———————
责编:成才
编审:韩雄亮
编发:新媒体头条
推广:地球村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