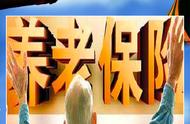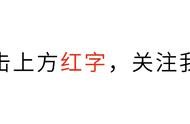川观新闻记者 邵明亮/文 摄影:蒋文
戴上老花镜,刘立彬迅速从桌子上抽出一张白纸,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幅“四川江河水系图”。10月30日,这位年近八旬的水利规划专家,当得知引大济岷工程前期工作推进速度空前,他眼睛一亮,兴奋地向记者讲起他与引大济岷的故事。
引大济岷,顾名思义就是引大渡河之水入岷江,源于我省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西水东引工程设想。刘立彬退休前曾担任原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分院副院长,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年轻的刘立彬就开始关注和参与引大济岷工程的各项前期设想、规划和勘测工作,如今他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
经过几代四川水利人的前赴后继,引大济岷工程如今迎来了重大进展。10月27-29日,水利部水规总院在北京组织召开引大济岷工程规模与总体布置专题报告技术讨论会议,经过近3天的深入讨论交流,引大济岷工程引水水源点及引水总干线方案基本敲定。引大济岷工程正从厚厚的图纸堆中一步步走进现实。

引大济岷工程通过水利部水规总院技术咨询
A/为什么要调水?
岷江已经不堪重负,成都平原仍“喊渴”
“千河之省”的四川,从总量上看,水资源丰富,人均水资源量高于全国,似乎并不缺水。
但是,除了全年70%左右的降水量集中在5-10月,容易形成季节性缺水外,甘孜、阿坝等地区人均年水资源拥有量高达4-7万立方米,而人口耕地集中的四川盆地腹部区却不足1000立方米,其中都江堰灌区人均当地水资源量仅305立方米。而国际社会公认的用水紧张线是人均水资源拥有量1700立方米,低于1000立方米即为面临缺水,低于500立方米即为严重缺水。
“我省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不相匹配,加剧了用水矛盾。”刘立彬表示,四川盆地腹部区生产总值约占全省的80%,水资源量却仅占全省的20%。

水利专家开展引大济岷工程前期勘探
这其中,岷江流域又最为典型。
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是成都平原的母亲河,是四川盆地腹部的最主要水源。每年春夏两季,上游高山融雪和丰沛降雨给岷江带来浩大的水流。自战国秦蜀守李冰筑都江堰“驯服”岷江,才造就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经过2200多年发展,都江堰灌区如今已发展成为覆盖成都、德阳、绵阳、资阳、遂宁、眉山、内江等7市40县(市、区),灌溉面积超1130万亩的特大型灌区。如今的岷江,除了向灌区提供农业用水,还要满足成都这座特大型都市(常住人口2094万人)的生活、工业和生态用水。而多项研究却表明,岷江的年均流量数十年来正呈下降趋势。
四川省水利厅厅长郭亨孝介绍,都江堰水利工程年均引水量为100亿立方米,而岷江上游来水(鱼嘴断面)年均来水量约140亿立方米,相当于上游70%的水都通过宝瓶口及六大干渠引走,而这些水大约有70亿立方米被在河道外利用,已超过国际上河流水资源利用率的生态警戒线(40%)。
一方面是有限的水资源,一方面是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岷江如今已是不堪重负!
“从区域发展来看,随着成都平原经济区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口增长,供需水矛盾将日益加剧。引大济岷工程有尽快上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郭亨孝介绍,根据四川水安全保障中长期规划测算,预计到2035年,都江堰灌区的年供水缺口将达25亿立方米。
弥补巨大用水需求,无外乎开源、节流两种方式。

大渡河位于甘孜州康定市若吉村的一段河道 韦维 摄
刘立彬表示,在都江堰灌区大力开展节水改造、建立节水型社会,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争水”局面,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灌区水资源紧缺的问题。“只有借助外来水源才是根本出路,不仅可以进一步满足灌区内用水需求,当岷江的生态环境水量增加后,可使通过青白江、毗河连通道进入沱江的水量也相应增加,这样一来整盘棋就下活了。”
B/为什么是大渡河?
使汛期洪水资源化,全程可实现自流引水
上世纪70年代,以罗汉卿、阮基康等为代表的四川水利专家提出,能否把川西北的水引过来?“那时的想法很笼统,没有完整方案。”刘立彬说。
四川大江大河众多,但为何选择大渡河支援岷江?
刘立彬指着自己刚刚画好的“四川江河水系图”,尽管河流众多,但看看岷江的这些“邻居”——沱江本身还要依靠岷江的水补充,属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涪江水位比岷江低,而且水量不大,引水给岷江不太现实;青衣江的位置也比岷江低。而环顾四周,大渡河尽管被崇山相隔,但因为水量充足,成为最有条件给岷江补水的河流。
选择大渡河,还有更为充足的理由。
一方面有助于汛期防洪。每年夏季,位于三江(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处的乐山常遭遇洪峰袭扰,其中大渡河就是重要的洪水来源。而根据引大济岷工程总体布置方案,通过建设数座大型水库进行调蓄,可以充分利用大渡河汛期洪水资源,实现大渡河洪水的资源化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