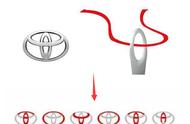第一章 缘起
1995
从数字上看,今天的“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是世界经济体中最大的一个。其“国民生产总值”(GNP)约为6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是5万亿美元,日本是3万亿美元。它的总人口如今超过了3.6亿人,接近美国和日本加起来的人口总数。然而,从政治上看,如此重要的力量却依然是有名无实的,与华盛顿或者东京相比,布鲁塞尔仍然无足轻重。因为欧盟不是一个主权政体,所以,它既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也不能与日本称兄道弟。但是,欧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大多数欧洲人自己也不知如何作答,除了新近加入欧盟的国家的公民(他们也对加入欧盟百思不得其解)外,对大多数人来说,欧盟或多或少还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团;对几乎所有普通选民而言,它是神秘莫测的;甚至在学者面前,欧盟的表面也笼罩着一层朦朦胧胧的薄雾。
一
欧盟的性质必定与它所包含的欧共体的起源有关——尽管通过特有的翻来覆去的司法转变,欧盟并没有全盘取而代之。一开始在政治方面为考虑其将来,厘清其体系起源似乎是可取的。此为一个依然存在着争议的议题。自一开始,历史专著就倾向于一种非比寻常的理论化的描述——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几乎没有多少人所熟悉的假设可以被想当然地接受。早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理论认为,支持战后西欧一体化的力量应当在客观上——不仅是经济上,也是社会上和文化上——从最初组成的“煤钢共同体”[1]及其后续组织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深化过程中去探寻。第一波进行诠释的“响亮声音”是新功能主义。该理论强调体制方面递进式发展的逻辑规律,亦即最为适中的功能变化,往往沿着一条无限延伸的不由自主的一体化道路导致增补性的变化。经济往来、社会交往和文化实践的跨国融合为逐步迈向全新的政治理想亦即超国家的大联盟奠定了基础。厄恩斯特·哈斯[2]认为,相对而言,这一过程的初期阶段存在诸多偶然性情况,不过其后续阶段发展的路径已确立;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发表了《欧洲的统一》(Uniting of Europe),该著可能仍是将这种观点理论化的最佳作品。
相比之下,第二波声音则强调了民族国家结构的快速恢复能力。此并非把战后西欧一体化看作迈向超国家主权的一段滑翔路径,而是相反,将它视为一种重振国家有效权威的有效手段。这种新现实主义论题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版本,但并非众口一词。迄今为止,最具权威和特色的是阿兰·米尔沃德[3]的著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欧洲一体化贡献最小的国家培养出了最透彻阐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学家。欧盟内还没有其他学者像米尔沃德那样把对档案的掌握和智力激情结合得如此紧密,米尔沃德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欧盟的起源问题。
他的出发点并不与此议题完全吻合,且富有创意。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经济复兴没有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模式——初期由于资源*而势头强劲,接着是突发性的增长与衰退?在《西欧1945~1951年间的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5~51,1984)一书中,他摒弃了传统的阐释——诸如凯恩斯主义[4]的出现、修复战争创伤、更大的公共部门、高额的防御开支、技术革新等方面的解释——他认为,1945~1967年间完全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其基础是这一时期大众收入的稳步增长,其背景是长期压抑且从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这种增长模式反过来得到各国新近的措施支持,各国“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1]导致了贸易的自由化和舒曼计划中一体化的头几项有限举措。
米尔沃德后来的著作重点关注的内容正是这些催生“欧洲经济共同体”[5]的措施,含有大量实证研究结果和日益犀利的理论要点。其名著《欧洲对民族国家的拯救》(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和《国家主权的边界》(The Frontier of National Sovereignt...
和平恢复以后,一种全新的机制从战前各项制度深陷的极度虚弱和信用丧失的危机中被建立起来。米尔沃德认为,与战前的狭隘和脆弱的状况相比,战后西欧各国的社会基础更为广泛,它们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发展、就业和福利的措施,将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首次全部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活。正是这些政策在各国所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又一次促进了整合范围的扩展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当它们在各自国家展开道义上的恢复重建之时,欧洲大陆的六个民族国家发现,通过共享对大家都有利的各自主权国家的某些元素,它们可以进一步加强各自的力量。这一过程的关键起因是早期的德国市场对其他五个国家出口商品的吸引力——再加上较为容易地进入法国和意大利市场对德国工业的吸引力,而最终会像比利时的煤炭和荷兰的农业一样,获得独特效益。在米尔沃德看来,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质上源自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考量,各国均认为国内正统性所倚靠的财富将通过关税同盟得以增加。
把作为强国的德国包括在内的战略需要也发挥了作用。不过,米尔沃德则认为这一作用实际上是次要的,因为用其他方法同样可以实现。如果一体化背后的驱动力是追求安全,那么在50年代对西欧各国人民来说的确至关重要的安全便体现于社会和经济方面:保证不再重复30年代的饥饿、失业和混乱。在舒曼、阿登纳和加斯贝里时代,[7]政治安全的愿望——即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和苏联扩张主义,甚或由天主教会的精诚团结赐予“精神”安全的愿望——则是另类表达的同样的基本诉求。“欧共体”(EEC)建立在六个新生国家社会经济利益方面的“相似性和可调和性”[2]的基础之上,它由每一个国家的战后民主秩序的政治共识所形成,在米尔沃德看来,这一初衷延续至今,且并未因共同体的扩大或其机构的复杂化而有所改变。
欧洲一体化的又一大明显进步亦即80年代中期的《单一市场法案》[8]展现了同样的模式。当时,在全球经济危机以及美国和日本日益加剧的竞争背景下,上述各国的政治共识发生改变,而选民们对于失业已经逆来顺受,转而要求解除货币管制以及放松社会管制。米尔沃德毫不掩饰他对“管理者的胡言乱语和出自抽象经济原则的狭隘的权威推论”[3]的厌恶,它们导致前述观念的变化。然而,正是因为完全转向新自由主义(1983年,密特朗[9]放弃了最初的凯恩斯主义纲领,从而确立了新自由主义),使得包括撒切尔[10]全盛时期的英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的大联合有了可能,伴随着国内市场的完善——像50年代一样,每一个成员国都在盘算各自可以从共同体内部进一步的自由化中获得的商业利益。再一次,民族国家仍然掌控着这个历程,其间放弃了某些司法特权,其结果是为了满足国内民众的期望而大大提升了物质生产能力。
久而久之,米尔沃德关于欧洲一体化的论述在接二连三的个案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每一个个案研究皆释放出巨大的驱动力——键盘上的制度详述和理论抨击一门心思地比试着,个人形象受到冷嘲热讽——他的研究的影响力可谓无人可比。但其影响力也同样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总的来说,米尔沃德的论述基于四个假设。也许,这四个假设阐述起来不会过于简单,具体如下:
首先,最清楚不过的是,国际外交事务——国与国之间对权力的争夺,亦即马克斯·韦伯[11]所理解的那种“国际政治”——的那些传统目标在通向战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始终是次要的选择。米尔沃德指出,这一不争的事实,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今,都是确凿无疑的。他总结道,共同体国家是否加快一体化进程“完全[12]取决于国内各种政策抉择的性质”[4]。米尔沃德将一句经典的普鲁士格言倒置过来,以假设一种几乎是无条件的国内政治之重要性(Primat der Innenpolitik)。而外交政策正如过去人们设想的那样未被束之高阁,但只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优先考虑的社会经济事务的补充。
第二个假设——在逻辑上有别于第一个——则是,决策中衡量外部政治及军事考量时是将两者作为追求国内民众幸福的延伸:这是一种补偿性的安全。外交事务的目标是与之相关的,但它们只与国内舆论的关注点相连而不是相冲突。后者亦即国内舆论反过来——这里,我们得到了第三个假设——体现了投票箱所表达的民意。“国家利益以及国家政策拟定受到的压倒性影响总是对选民要求的回应”,“正是通过他们的选票……选民在界定国家利益方面将继续施以压倒性的影响”。[5]这是因为民主共识在西欧各国很相似,工人、职员和农民的呼声最终都能被适当地听到,如此,受社会安全新目标鼓舞的民族国家足以采取为迈向一体化目标而进行的最初的重大步骤。在此——最不显著,但仍可察觉——最后一条假设就是:在重要的情况下,构建最初的关税同盟和完善国内市场的各国参与遵循一种绝对的对等之原则。
国内目标居于首位,与其外交目标相连;此外还有制定政策的民主机制,以及国内各种舆论的对等性。讽刺与压抑密不可分,米尔沃德的研究工作是细致且复杂的,它包含诸多不一致的现象,其中一些还相当明显。粗略说来,上述四个方面体现了他著作的要点。它们具有多么强大的说服力?了解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关注米尔沃德怎样处理他的出发点。欧洲一体化运动确切之起源就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人对此存有异议。然而,以独到的视角来看,战争本身的经历被认为是一场灾难,在这场灾难中,战前政治结构的普遍脆弱性——缺乏广泛的民主基础——突然显现出来,因为接二连三的民族国家在这场冲突的大熔炉里轰然倒塌。
这种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式合情合理且富有建设性,它为战后重建的故事搭起了一个舞台,进而导致了米尔沃德所言的一体化。不过,战争肯定不仅是一场所有欧陆国家均经受了考验并发现自身欠缺的灾难,而且也是大国间的生死较量,其结果是完全不对称的。挑起纷争的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几乎从未垮掉过——这绝非由于民意支持的狭隘性。它的士兵和国民毫无顾虑地抵抗盟军,直至最后。
战争记忆这段难以衡量的经历——德军霸权的规模及其导致的各种后果——同在战后更加繁荣和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各个民族国家的可衡量的工作一样,塑造了欧洲一体化。米尔沃德所关注的则是后者。重点关注的国家必然是法国,但它对欧洲各项常规制度的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就法国在西欧整体经济中的比重而言,则是不成比例的。这绝非偶然。在六国取得关于一体化的商业利益的巴黎共识之前,一开始就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遏制德国是法国的优先战略。一旦英美的反对排除了重新实践克列孟梭[13]那种用主要力量控制德国的想法,那么,唯一一致的选择便是与之建立最紧密的同盟,这伴随着一项比临时避难所似的传统外交更为经久耐用的建设性规划。
因此,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核心一直是两个主要大陆国家亦即法国和德国签订的两国间的特别协议。两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协议,从形式上看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则始终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对欧洲各项常规制度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巴黎和波恩之间的四项重大协议。第一项里程碑式的协议当然是1950年的“舒曼计划”,它促成了1951年最初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就法国而言,若言其依靠莱茵河的煤炭来作为其焦炭供应源的冶炼业的地区问题为“舒曼计划”开始时的一个要素,那么,该计划之用意则更为广泛。在两个国家中,德国拥有更为广大的重工业基地,而法国则担心其重整军备的潜力。另一方面,德国担心对鲁尔区[14]持续性的国际军事控制。资源合作的合资经营主权的确使法国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得以释怀,并使德国免于来自同盟国的经济监护。
第二个里程碑是阿登纳和摩勒[15]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使得1957年的《罗马条约》[16]成为可能。在否决了波恩的财政部和巴黎的外交部的保留意见之后,两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保证德国和法国的工业产品自由进入对方市场,双方市场的繁荣都依赖于此,同时对增加法兰西联邦共和国农产品出口的前景也寄予厚望。面对来自自由派人士艾哈德[17]——他担心法国较高的社会成本可能会蔓延到德国——的尖锐反对意见,阿登纳对这项协议的支持显然拥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他希望西欧的团结成为一道抵御共产主义的壁垒,也是德国最终统一得到法国尊重的保障。另一方面,在巴黎的经济顾问们依然在“共同市场”的规划上存在意见分歧,直到伦敦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些富有竞争性的建议看上去似乎更吸引波恩,威胁到了法德商业纽带的领先地位。然而,左右这一议题的既非那些政府高官们的技术性判断,[6]亦非摩勒本人的个人偏好——他一直支持欧洲一体化,但早在两年前就不能领导他的政党了,当时欧洲防卫共同体(EDC)已遭法国社会党的选票扼*。苏伊士运河危机[18]的政治冲击波使得平衡的局势发生改变。
当时,摩勒所领导的政府正全力以赴地声讨阿尔及利亚战争[19],准备打击埃及,而非展开任何类型的商业谈判。鉴于亲英派之背景,他与英国达成共识,在地中海东部采取联合行动。1956年11月1日,苏伊士运河远征行动开始;五天后,当法国伞兵在伊斯梅利亚[20]郊外降落之时,阿登纳到达巴黎,就共同市场问题进行秘密会谈——当他正同摩勒和皮诺[21]会谈时,艾登[22]突然从伦敦打来电话告诉他,迫于美国财政部的压力,英国已单方面取消远征。阿登纳在一阵目瞪口呆后,灵机一动,向主人暗示了这种道义行为。[7]法国内阁吸取了这次教训。美国因为印度支那改变了立场。英国已不可依靠。对致力于在非洲的帝国统治并计划制造原子弹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最后几届政府来说,只有欧洲联合才能实现对美国的必要抗衡。六个月之后,皮诺签署《罗马条约》,在法兰西国民议会上,正是这项战略主张——欧洲独立于美苏的必要性——获得了批准。
第三大关键时期则伴随着戴高乐[23]的执政一起来到,法国战后首个真正的强大政权必然改变协议之条款。1962年年初,戴高乐签署了有利于法国农民的《共同农业政策》,但却未在六国之间建立起政府间理事会,之后他在秋天就正式的外交轴心问题与波恩开始举行会谈。当时,法国是一个核大国。1963年1月,戴高乐否决了英国加入共同体;2月,阿登纳签署《法德条约》。一旦确立外交同盟,戴高乐——众所周知,他与布鲁塞尔的以哈尔斯坦[24]为首的委员会敌对——只要权力在手,就可以阻止欧共体(EC)进一步一体化。新的平衡的制度性表达导致1966年的“卢森堡妥协”,阻碍了部长理事会[25]里的多数投票表决制,该理事会在以后的20年里为欧共体树立了一系列的立法参照。
最后,在机构改革相对迟滞的一段时间里,1978年吉斯卡尔和施密特[26]一同创立“欧洲货币体系”,以抗衡“布雷顿森林体系”[27]的崩溃所造成的不稳定影响,那时在战后第一次严重衰退期间出现了固定汇率瓦解之局面。欧洲货币体系创建于共同体框架之外,被法国和德国用来反对来自委员会内部的抵制,作为控制金融市场反复无常现象的第一次尝试,它为在六国内推行单一货币打下了基础。
然后,在战后的最初30年里,这一模式始终丝毫未变。这两个最强大的欧陆大国以前是毗邻的宿敌,此时在追求各自不同而又趋于相同的利益过程中,促成了欧洲各项制度的发展。法国始终保留着军事和外交优势,它决心要德国遵守共同的经济秩序,如此可确保自身的繁荣和安全,同时使西欧摆脱对美国的屈从。德国在50年代中期已获得经济优势,它的工业产品不仅需要共同体范围内的市场,而且还需要法国支持它重新完全融入大西洋集团并且最终重新与——仍然是官方认定的中德——在苏联掌控之下的地区统一。这一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合作伙伴一直是法国,法国人构想了最初的“煤钢共同体”,谋划出共同市场的大部分体制机构。直到德国马克第一次成为欧洲货币区的支柱,巴黎和波恩之间的平衡才开始改变。
较之选民们追求耐用消费品和福利性支出的历史,以法德为轴心的高层政治更为古老。然而,如果这种政治既未重新给予两国国内备受关注之事以首要地位,亦不能使两国国内公众舆论达成默契——其他成员国则几乎无法与这两国的重要性相提并论——这似乎恰好证实了米尔沃德所提出的纯粹的政府间关系在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中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论断。但如果我们审视一下由此而产生的共同体的各项制度,就可以发现其存在着缺陷。即便是附带农业基金的关税同盟,也不需要拥有行政权威的超国家的委员会、可以推翻国家法规的高等法院和名义上拥有修订或撤销之权力的议会。米尔沃德认为,有限的国内目标是一体化的推动力,这些目标本可以在更为清晰的框架内实现——若是戴高乐在一年前掌权的话,他可以接受这样的框架;而今,这种框架在美洲包括南美和北美,均可看到。若非凭借另一种力量的话,共同体的实际机制则是难以理解的。
当然,此即联邦主义者关于超国家的展望前景,它主要是由莫内[28]及其团队发展的,这支专家小组构想了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并草拟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部分细节内容。现代政治人物中没有几个比莫内更难以捉摸,就像米尔沃德在谨慎地描写他的几页中所论述的那样。然而,自从他论及莫内以来,弗朗索瓦·迪谢纳[29]的优秀传记出版了,使莫内的形象更为明确。在没有贬低莫内职业的反常行为的敏锐而体面的著作中,迪谢纳给他描绘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欧洲之父”的形象。
莫内那种外省的保守性和循规蹈矩是具有误导性的。与乔治·杜哈梅尔[30]相比,他更是一个安德烈·马尔罗[31]式的人物。这名个头不高却衣冠楚楚的夏朗德人是个涉猎范围广的国际探险家,在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开始于战争采购和银行兼并行动的赌博中,他玩弄金融和政治,其赌博最终成为大陆统一的规划和创造全球理事会的梦想。从关心加拿大白兰地市场到组织同盟国小麦供应;从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发行债券到在旧金山和贾尼尼[32]在代理人问题上斗来打去;从在瑞典与克鲁格尔[33]的大公司结算到在上海给宋子文(T.V. Soong)安排铁路贷款;从和杜勒斯[34]一道工作以便在底特律建立美国汽车公司,到与弗里克[35]打交道以处理德国纳粹的化学公司——对战后“规划委员会”(Commissariat au Plan)和最高权力机构的主席职位以及“荣誉侍卫”[36]和“欧洲第一公民”等称号而言,上述这一切皆为其准备性的工作。
莫内的婚姻也许是他生活的最好写照,我们借此可以窥见他在两次大战间生活的一部分。1929年,他按照约翰·麦克洛伊[37]的要求,在米兰发行一种城市债券,这时,他爱上了他手下的一名意大利雇员的新婚妻子。在墨索里尼统治下没有离婚一说,而两年以后,这对已婚夫妇已育有孩子;终止这段婚姻的企图遭到已为人父的丈夫的反对,也遭到了梵蒂冈的拒绝。直至1934年,莫内的总部一直设在上海。某日,他从那里横越西伯利亚去见他在莫斯科的情人,她也从瑞士赶过来,且一夜之间获得苏联国籍,随后解除婚姻,并且在苏联的各种禁令下嫁给了他。他的新娘,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尤为喜欢这些非同寻常的安排——莫内解释道——而讨厌里诺那些有损身份的办事处。[38]斯大林政府为何允许他们如此而为,他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的结合发生于极为紧张的时期:两周后,基洛夫[39]遭暗*。结果,当与她分手的意大利前夫试图重新得到在上海的四岁的女儿时,莫内夫人为免遭绑架而在苏联领事馆避难——共产国际历史上颇有名气的机构。到1935年年底,她仍持有苏联护照,却获准住在美国,当时莫内让她使用了一个土耳其移民名额而得以迁往纽约。在《斯坦布尔火车》及《上海快车》中,[40]我们可以感受到其间的场景。
作为一名国际金融家,莫内堪称四海为家者,不过他依然是法国人,而且是一名爱国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结束,他先后在巴黎、伦敦、华盛顿、阿尔及尔为他自己的国家以及盟军的胜利而不知疲倦地工作。1945年,戴高乐任命莫内领导一个新的计划委员会,任命莫内可是个理性的选择。这位“现代化和装备计划”的组织者,被米尔沃德描述为“法国民族国家在战后复兴的最有成效的促成者”。[8]不过,这时他并非孤身奋战。使莫内与众不同的是当时机到来时他摆脱原有的羁绊的速度和胆量。1949年年末,艾奇逊[41]要求舒曼对德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法国政策,法国外交部没有作出回应,此时他的机会终于来临。正是莫内的解决办法——提出煤、钢资源的超国家联营——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八年以后,欧共体较大部分的机制模式直接源自1950年莫内设计的“煤钢共同体”。
毫无疑问,正如米尔沃德所说,这些年来莫内的倡议大多被归结于美国的支持。作为一名跨越欧洲各国国界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决定性的优势就是与美国政治精英——不仅仅有杜勒斯兄弟、艾奇逊、哈里曼、麦克洛伊、鲍尔[42]、布鲁斯等——的密切交往,这是他在纽约和华盛顿期间建立起来的,迪谢纳对此已有详述。当时,莫内在这个霸权国家里,与最高权力阶层的亲密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也正是与美国如此亲密无间的关系才使得他日后在自己的国家里广泛地不被信任。那时的国内同胞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在马歇尔计划[43]的战略框架之内,他的欧洲热情中究竟有多少是由他的美国赞助者所激发的呢?
事实上,结构的内在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莫内有可能是在美国期间的各种讨论中首次形成了战后一体化的想法,而可以肯定的是,他后来的成就的关键也在于美国的支持。然而,他的政治灵感与美国是相当不同的。美国政策受其对冷战目标的不懈追求驱使。强大的西欧作为防止苏联入侵的一道壁垒为美国所需要,它是世界范围内防止共产主义颠覆的最前线,而其外围地区被认定在亚洲,从北部的朝鲜到南部的印度支那和马来亚,这条防线由法国和英国把守。
令人奇怪的是,莫内对所有这些均不为所动。在他的祖国——法国,他和解放后的法兰西总工会(CGT)*的关系十分融洽。他认为,由美国财政支持的印度支那殖民战争是“荒唐和危险的”;他担心朝鲜战争会使美国对重整德国军备一事施加的压力升级,以至于法国公共舆论会反对“舒曼计划”中设计的共享主权;他还认为西方对苏联威胁的执着分散了注意力。到1950年6月,他对《经济学人》(Economist)的编辑说,煤钢共同体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欧洲的中立集团——如果法国不必担心德国,那么也就没有其他国家可担心的了,比如苏联”。[9]其重要使命是塑造现代的和团结一致的欧洲,它能够长期与美国保持独立伙伴关系。“我们将改变原有的社会环境”,他在1952写道,“并且将会对我们目前对俄罗斯的恐惧付之一笑”。[10]美国强权设定了欧洲所有政治活动的限制,而莫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如何处理。不过他又有自己的计划,这种计划则与美国的意图保持一定的距离。
何以至此?莫内历经了欧洲两次毁灭性的冲突,其最高目标就是阻止再一次的冲突。但是,此即他那一代人共同拥有的执着追求,并未激发任何联邦主义的构想。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部分原因是冷战的热情迅速取代了世界大战的教训,那些西欧政治精英们要优先考虑其他的事务,而对那种构想或置之不顾,或将其视为一种负担。莫内将这些都置之度外。他所从事的职业是那种当今已不存在的财政规划员,这种职业使之游离于稳定的国家力量即国家各行领域之外,从而也使他在心理学的角度,总是拥有一种他那个阶级常有的处事态度。正如迪谢纳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认为莫内“缺乏政治价值观”,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法国和俄国革命产生的经济平等的斗争”。[11]正是这种相对冷漠——与无动于衷迥然不同——使他自由地在超越国家体制的假设中有所作为,这些斗争正是在国家体制内进行的。
虽然他为他的国家而骄傲,但他并未致力于构建民族国家框架的工作,他反对法国拥有核威慑,并试图劝阻阿登纳签订《法德条约》。自煤钢共同体的设计构想之日起,他就为欧洲的超国家目标而不懈地努力。他最初对并非由他创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思想很冷淡,认为共同市场是一项“不甚明了的”计划——不管怎样,他对自由贸易的信条并无特别的印象。米尔沃德看来是大大低估了关税同盟促进一体化的潜力,但莫内早在1955年指出的这一问题——“如果共同市场没有联邦社会的、财政的和宏观经济的政策,这样的共同市场有存在的可能吗?”[12]——在40年后依然是摆在欧洲联盟面前的一个核心议题。遣词造句的前后顺序尤为关键。作为一名职业银行家,莫内在经济方面并不保守。他总是寻求工会对他的各种计划的支持。甚至到了晚年,他还表达了对1968年学生运动的同情,学生运动对社会不公的警示是“人道事业”。[13]
另一方面,按照通常的理解,莫内对民主进程是陌生的。他从未面对过公众,也从未竞选过公职。他只是和精英们在一起,而未曾与选民们直接接触。米尔沃德认为,欧洲一体化源自每一个民族国家内的公众共识,如民意调查所表示的那样——此本身就足以说明莫内对联邦主义并无多大影响。然而,吸取相反的教训似乎更加合情合理。莫内的经历纯粹象征了导致今天欧盟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直到——表面看来——1976年的英国全民公决,民众才真正参与到欧洲的统一运动中。
当然,议会多数派不得不团结起来,大公司的利益也要一致:机敏的游说团体以及行为乖戾的代表们要有说话之处。然而,从未有人与选民们磋商过。1956年1月法国共和阵线上台执政的民意调查中很少提及欧洲——他们因为阿尔及利亚冲突和布热德[44]的呼吁而争吵不休。不过,经济共同体命运最终发生改变的关键点是国民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几十张选票的改变,这些选票阻止了欧洲防卫共同体,以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的风云变化。此处即包含了米尔沃德四种假设论断中最为微弱的声音,他把整个一体化过程归结于依据想象的民主基础。上层已经设计好和辩论过的计划往往没有公众反对,他们只是消极地同意。在他新近的著述里,米尔沃德本人也承认了先前的许多误判,而实际现状则正如迪谢纳所描述的那样:“形势并非革命性质的,选民既非发动机亦非刹车。”[14]
然而,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得莫内及其同事们在和大臣们的谈判中发挥了作用呢?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欧洲一体化的结果并非像新现实主义的逻辑所暗示的那样在各政府间千差万别——换言之,这种结果也不是包括孟戴斯-弗朗斯[45]或者戴高乐(或者以后的撒切尔或者梅杰[46])可能会批准的某种框架,那么,答案则有两个方面。首先,在六个国家中,小的国家倾向于联邦制的解决方案。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关税同盟早在1943年的流亡政府期间就已初现端倪,它们将在欧洲发挥重大影响的唯一期待寄托于一个超国家框架之内,正是来自低地国家的两个外交部部长——荷兰的贝恩(Beyen)和比利时的斯帕克(Spaak)——率先走出了关键的几步,最终催生了《罗马条约》。事实上首先提议成立共同市场的贝恩,没有通过选举成为政治家,而是飞利浦集团的前业务主管以及联合利华公司的董事,他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直接进入荷兰内阁。米尔沃德忽略了他对莫内的责难,而是恰到好处地对其颂扬备至。
然而,另一个也是更为沉重的砝码压在天平的联邦主义一方的秤盘上。毫无疑问,此即美国。作为一体化的建筑师,莫内的作用力并非对欧洲内阁施加特别的影响——即便他最终还是获得阿登纳的信任——而是在于他直截了当地站在美国一边。在艾奇逊和杜勒斯时代,来自美国的压力尤为关键,它用一种真实——不只是理想化——的力量推动着“更加伟大的联盟”的设想,这种设想被《罗马条约》奉为圭臬。而一旦忽视了美国的影响,米尔沃德的观点就要受到指责,不是指责他过于实际,而是不切实际。
同时,美国的政策使得米尔沃德设想的最后部分显得尤为突出,因为美国对着力推进的一体化始终如一的支持(在关键时刻是一种压力)与重要的国内选民的利益及需求不一致。在已经作出的各种决策中,美国的选民无能为力。更为重要的是,当一个更加统一的西欧辅之以共同的对外关税,其越来越强的经济竞争力为美国财政部、农业部及联邦储备部门所留意时,这些部门的建议却被白宫和国务院毫不留情地否决了。在与共产主义的全球性的冲突中,美国政治军事之需绝对凌驾于那种商业考量之上。艾森豪威尔[47]对皮诺说,《罗马条约》诞生之日是“自由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天,它也许甚至比军事胜利还要辉煌”。[15]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寓意深刻,所言极是。
米尔沃德完全清楚美国人的优先战略,在这方面他以其惯有的语言加以描述。然而,他没有继续探讨这些优先战略考量在其诠释方案中所引发的理论问题。至少在美国,国内议程与外交目标并无连贯性:这些议程与目标冲突明显。若欧洲没有类似状况,美国只是个例外吗?而米尔沃德本人所提供的证据表明,这并非例外。这是因为,毕竟有一个西欧大国尚未走上一体化之路。
为什么在工党和保守党治下的英国抵制六国的理念呢?可以肯定地说,不断提升的大众标准背后,基于对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的坚持,英国国内的共识甚至要比法国、意大利更加彻底(法意两国仍然存在着不肯合作的大规模的共产党团体),这种彻底性甚至也要超越拥有经济自由主义强力支持者的德国吗?在主要政治力量的棋盘上,英国没有它自己的马蒂[48]或者艾哈德,而在欧洲大陆的词汇表上,也没有巴茨凯尔主义[49]的对应词。如果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基于强大的国家共识下对社会经济安全的一种普遍探索,那么,在艾德礼和麦克米伦时代[50]的英国,就不应该率先为之吗?
虽然米尔沃德指出了使得英国颇有些不同于其他六国的经济结构的元素——诸如英国农业补助金的构成、英镑的作用、英联邦市场的特点等——但他并不认为英国因而要置身于欧洲之外是明智之举。相反,他认定英国“没有签订《罗马条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16]他对这个错误的解释是英国那傲慢而狭隘的政治体制与认为英国“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其外交政策应该反映这种地位”的信念紧密相连。而它对周围世界的无知通过哈罗德·麦克米伦与其知己们的交流谈话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他认为正是“犹太人、规划师们以及过去的世界主义者”才该为欧洲委员会超国家的发展潮流而受责难。[17]
米尔沃德的详论表明,战后15年来,在应对欧洲一体化方面,英国的政策基本上是由对其国家政治力量和威信评判——或误判——经济状况评估之前的统治者来确定。此种模式与《欧洲民族国家的拯救》的整体框架之间的格格不入显然逃脱不了他的关注,于是他采用一种比平常更为试探性的语气而巧妙地暗示说,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争年代,英国的危机与大陆相比没有那么严峻,“因此1945年以后,对新的共识的探求就更加有限”,并且——尽管表面上看来并非如此——这种探求的结局“也许更加可怜”。他继续写道:“一体化所带来的繁荣也同样是更为有限的,最终,英国会对这种战后共识进行抨击,它仅仅是其中一个受益较小的国家。”[18]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艾迪生[51]的《通向1945之路》(Road to 1945)也许要进行大胆修正。然而,仍然存在那种假设: 社会共识的程度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欧洲政策的命运。不过“共识”实乃模糊之词,近似于委婉语,它被用于炫耀而非框定民意。它的使用者限于喜好对此高谈阔论的精英们。而从这一角度而言,英国的确存在着共识,并且——在此“对不住”米尔沃德了——是特别强的共识:但它却与竞选几乎没有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米尔沃德论述中的夸大其词源于那种颇为诱惑人的政治冲动。他对战后福利国家的成就——它使普通百姓生活在物质方面得以改善——疯狂且极富同情心的依赖和迷恋是其著作的基本主题。如果这些成果就是各民族国家国内政策的民主化选择的产物,难道就可以不因国家之间新的合作形式而持有同样的压力吗?这项举措的诱人之处是造就了古怪而具有启发意义的混合物——强调其自相矛盾,可以称之为外交上的民粹主义。[52]然而,若言米尔沃德是出于自己激进倾向的一面而对此作出让步的话,那么,他那种激进倾向的另一面——亦即对任何伪善已是忍无可忍——则是反复地阻止他作出让步。
所以,他近期的作品中存在着更为矛盾的观点。“选举及选民”,如今他承认,“比我最初提出假设之时的重要性要小”。[19]米尔沃德没有依赖于共识的主张,此时提出忠诚——“所有那些使公民效忠于各种管理机构的元素”——的概念,将它作为理解欧洲一体化之密钥。[20]这种代替是有意义的。与共识这种民主的外包装相比,忠诚是一副更为古老、更为猛烈的药剂。作为可以整合共同体发展涉及的各部分的要素而为米尔沃德所提出的这一词语的封建特色,是再恰当不过的,它表明的不是全民参与而是出自风俗习惯的支持:以服从换取利益——更能体现霍布斯而非卢梭[53]之观念。这当然更接近于西方的现实。
“自1945年以来,我们提出的保护国民政府的唯一做法”,米尔沃德写道,“就是使政府比过去更好地代表公众意愿,即使并非十全十美。对我们而言,此即政府得以幸存的历史原因。”——不过,他认为其幸存已被“很好地抵消了”。[21]欧洲一体化的加强就使它远离危险了吗?决非如此。救援可能只是一种临时的缓解行动。在保证了标题所述之事会发生之后,米尔沃德的这本重要著作的结语似乎撤回了自己原有的观点:“欧洲共同体的力量”归根结底存在于“民族国家的孱弱之中”。[22]
如果米尔沃德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无法达到一致,其著作中丰富的史学内容优于理论假设方案,那么,部分原因是,他的后期著作——不像他早期的——是按照选题而非按照系统论述来安排组织的。如果不同时追踪他原则上所承认的发挥作用的不同力量,那么依据对等条件,任何一种力量对一体化进程的相对贡献则无法确定。如此论述要等到档案资料更为全面开放之后。而没有相关档案,那什么样的临时性结论是合理的呢?
在一体化进程的背后,至少存在着四种主要力量。尽管这些力量相互交织,但其关注的焦点存在着差异。莫内身边的联邦制拥趸者的主要目标是要创建一种欧洲秩序,它将免遭灾难性的民族主义战争,这类战争在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两次蹂躏了大陆。美国的基本目标是要建造一座抵御苏联的强有力的西欧堡垒,以作为最终获得冷战胜利的手段。法国的主要目标是用一纸战略性的协议拖住德国,使巴黎在易北河[54]以西的兄弟中成为老大。德国主要关心的是要重返已经建立起来的大国行列,并保持重新统一的愿景。把这些不同的目标整合在一起的则是——米尔沃德在此当然是完全正确的——所有党派对确保西欧经济稳定和繁荣的普遍重视,此为上述各方达到各自目标的前提条件。
这种格局有效地维持到60年代末。在接下来的10年里,出现了两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作用的转换:英国迟到的加入将名义上与法国和联邦德国力量相当的另一国家带入共同体之内;而与此同时,当尼克松和基辛格[55]察觉到西欧这一强大竞争对手的潜力之时,美国则退回到更为警觉的立场。第二个变化则是根本性的。战后使得最初的六国凝聚在一起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因全球衰退的开始而出现崩溃,其结果是,官方完全改变了对待公共财政、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和竞争规则的态度,而此即80年代的晴雨表。
如此,迄今为止最后一个颇有成效的一体化措施,亦即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案》[56],多少显示出不同以往的模式,尽管它并非没有继承的一面。完善国内市场的倡议来自德洛尔[57]这位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他最近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在法国的负责人。在政府层面上重大的变化则是,如同米尔沃德正确强调的那样,密特朗政权在德洛尔的激励下转变为正统自由派——而不久前,在德国,向右翼的转变促成了科尔[58]的上台执政。不过在英国,这一次则是第三种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撒切尔为了解除对金融市场管制采取合作态度,英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在这片金融市场看到了获取巨额利润的前景,而在管理层面上,科克菲尔德[59]在布鲁塞尔对这个项目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这段时期里,委员会的高调行事证明,共同体内部由来已久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某种改变,通过在部长理事会内部推行(说恢复更合适)有资格的多数投票制度,上述单一法案本身也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法国在布鲁塞尔的最初联邦制度方面所留下的印记从来没有比在德洛尔统治期间更为明显,而巴黎和波恩则在政府间关系网中保留着传统优势。30年一体化的结果是今天欧盟内各种机构的奇怪聚合,包括如下四个互不关联的部门。
首先,最吸引公众眼球的是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可以说——就像是共同体的“行政部门”。该委员会是由各成员国政府指派官员组成的机构,其主席工资比白宫主人工资高得多,但却领导着一个工作人员比许多市政府还要少的官僚机构,并支配着和该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1%差不多的预算,而这些财政收入并非由该委员会而是由各成员国政府收取,委员会并没有这种直接的征税权。在一条美国的保守派只能做梦实现的规定中,《罗马条约》严禁该委员会出现任何财政赤字,其费用支出依旧大量集中在《共同农业政策》[60]上,关于这一点,欧洲内外都存在诸多怨言——美国和加拿大对农业的支持并不比欧洲少很多,在这方面日本显然要高得多。一些资金也用于“结构基金”,[61]以支持贫穷和业已衰退的地区。欧洲委员会管理这笔预算,发出调控指令,以及——拥有制定欧洲法律的独有权——提出新的法规。它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保密的。
其次是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一个完全误导人的名称,事实上,它是指每个成员国政府部门部长们出席的一系列政府间会议,涵盖了不同政策领域(大约总共有30个国家)。理事会决议等同于共同体的立法职能:它是在布鲁塞尔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会议的多头管理实体,其磋商是保密的,且大多数决定在低于与会部长的官僚层面上作出,其结果对国家议会具有法律约束力。自1974年起位居这一组织之上的是所谓的“欧洲理事会”,[62]它由各成员国的政府*组成,至少每年会晤两次,并为部长理事会制定宽泛的政策。
再次是卢森堡的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其法官由成员国任命,法官宣布委员会的指示合法与否,对联盟和国家之间出现的法律冲突发表看法,经过一段时间后,法官们把《罗马条约》视同《欧洲宪法》(European Constitution)一般。不像美国的最高法院,欧洲的法庭没有表决记录,也从不在裁决中陈述异议;法官的个人观点难以捉摸。
最后是欧洲议会(The European Parliament),作为唯一由选举产生的组织,它在这种复杂的机制中可谓那种形式上的“大众化的元素”。然而,它背离了《罗马条约》,缺乏通常的选举系统:其“居”无定所——如流浪汉般辗转于斯特拉斯堡、卢森堡和布鲁塞尔[63]之间;没有征税权;没有财权——仅限于对共同体总体预算简单地行使同意与不同意之表决权;没有行政任命权,而在非常情况下只是威胁反对整个委员会;没有立法权,对此只能修正或者否决。在所有这些方面,与其说它是一个立法机构,还不如说是政府部门的礼仪性质的机构,它所展现出来的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外表,几乎与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完全类同。
因此,欧洲一体化在制度层面上的最终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关税同盟,它拥有超国家性质的准行政部门,不过它缺乏任何贯彻其决策的机制;它有政府间部长会议的准立法机构,不受任何国家的监督,就如同上院那样运作;它拥有准最高法院,捍卫着并不存在的宪法;亦有一个拥有伪立法权的下院,其形式是无所作为的议会,不过它仍是唯一经过选举的机构,理论上是对欧洲人民负责的。所有这一切均叠加在民族国家之上,也决定着其各自的财政、社会、军事和外交政策。但到80年代末,这些临时凑合的众多举措已经固定下来。
然而,在90年代,这一联合体所处的政局出现了三次巨变:苏联的解体、德国的统一以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64]的出台推动了规模堪比二战结束的重大进程。这一切表明,欧洲联盟在将来很可能是集各种变化于一身的大舞台:欧洲货币联盟之路开启;德国重回欧陆霸主地位;前共产党国家争相加入欧盟。而对于这些重大变化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又有谁能够进行预测呢?
在此历史的十字路口,回顾一下莫内及其团队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回溯过去的历史,国家构建循着三条主线行进。第一条是国家版图和政府权威计划外的、渐进式且自然而然的扩展,如此发展之路就发生在——举例来说——中世纪晚期的法国或近代早期的奥地利,它们的设计师很少甚至根本就不存在长远目标规划。第二条路则是有意效仿已有的模式,它率先出现于18世纪的欧洲,由普鲁士人[65]及皮埃蒙特人[66]追随仿效法国人的专制统治。第三条道路也是最晚的一条道路,它是深思熟虑后的革命性的创新之路——亦即在极为紧迫的时间段内创立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如同在群众性暴动下发起的美国独立战争和俄国革命,或如同在精英推动下的日本明治维新。
联邦式欧洲“规划者”——这一伯克[67]的警告中所用之词可以被视为致敬——所启动的治理历程偏离了上述三种道路。在历史上,它根本就没有先例:因为其起源是深思熟虑后的设计,然而它们既非对他者的模仿且在规模上又非总体性设计;同时,其所确定的目标不是近在咫尺,而是非常遥远的。这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组合:是那种既具有高度自愿同时又脚踏实地且零打碎敲的政治构建——历经一个漫长的过程。凭借莫内所称的“动态失衡”,他的战略就是不断地累加总量,朝着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参照的目标——一个民主的超国家的联邦而努力。他对其事业的意义可谓心知肚明。他写道:“我们正在开始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够比广泛存在于西方之外的革命原则更加长久地塑造明天的世界。”[23]迪谢纳所著传记的优点之一是十分明智地试图衡量这项革新的重要意义,他称这种“革新”——较之征服、调整或剧变——为“历史上最为罕见的现象,一种经过慎重思考的政体之变”。[24]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方案。当然,其中同时有某些夸大之说,也有一些过度的轻描淡写。这些变化与其说是深思所得,不如说是临时拼凑,而所探讨的对象也不只是政体。
追溯过去,谁能否认这位拥有政治进步构想理念的天才——就像拿破仑[68]的勃勃雄心可以和塔菲[69]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呢?不过另一方面,这种结合需要付出特定的代价。如果所有历史性的事业的结局注定都会意想不到,那么越是过于深思熟虑,原先规划与实际进程的差距就越是明显。由莫内及其团队所开启的“欧洲建设”是一项规模与复杂性无与伦比的事业,然而它却几乎总是依赖那些乏味的体制发展进程及有限的社会支持。从历史上看,它所做的——亦即那种扰乱并阻止规划者们意图的持久性的结果模式——是必然的。
一连串的困扰延续至今。在50年代,莫内打算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也承担了共同市场的任务,他本来的目标是建立超国家的联盟,最后所得到的是一家政府间的国际财团,且被最反对他一切主张的政治家戴高乐所掌控。相反,戴高乐将军认为他在60年代程序中的固定地位将会阻挠欧洲委员会官僚们那些自命不凡的主张——事实上,那些主张在70年代引起了比以往更为强烈的反弹。在80年代,撒切尔夫人相信《单一欧洲法案》会再现并扩展她在英国所倡导的撤销了管制的国内市场——不料却发现它正朝着她最痛恨的单一货币方向发展。雅克·德洛尔的希望依然在我们心中;它们的命运在90年代会有可能不同吗?
二
1994年元旦,欧洲——一个代称——改换名号。包含10多个国家的“共同体”易名为“联盟”,尽管在一次西班牙的婚礼上新的名号并未取代而是包含着原有的名称。本质上而言,这一改变有什么意义吗?答案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随着3个前中立国的加入,其成员国数量已上升到15个。除此之外,局面与从前并无不同。而不同的是,人所共知,此局面不会持久。二战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是,对于代表整个欧洲的部分欧洲地区而言,欧洲处于一种对巨大而仍不可预知的变化的期望之中。三件事情占据着人们的视野。
第一件事当然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我们可以撇开条约里各种各样有关外交政策和国防的含糊的咨议以及对社会权利的无效保护的修饰性条款,甚至可以无视共同体内对机构关联性内容的小修小改。该条约的核心是各个成员国(除英国和丹麦外)的承诺,亦即到1999年之前,在单一中央银行的管理下推出单一货币。此为欧盟迈向真正联邦制的不可逆转的一步。在联邦体制之内,各国政府要么失去发行货币的权力,要么失去调整汇率的权力,唯一能够做的是极为有限地改变利率和公共借贷。如果违反中央银行的指令,就会招致欧洲委员会的重罚。它们仍可自主征税,然而在单一市场上,可预计资本的流动性将确保财政方面越来越多的共同点。欧洲货币联盟的诞生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中最重要特性的消失。
第二件事则是现今德国的统一。最初的共同市场是建立在六国中最大的两个国家——法国和德国,前者有重要的军事和外交分量,后者经济分量更重,人口也比较多——间的平衡基础之上的。后来,意大利和英国位于法德两侧,其人口和经济规模与法德两国大致相当。当欧洲货币体系(EMS)被证明是以德国马克这一在体系内唯一从未贬值过的货币作为枢轴之时,这种平衡在80年代即被打破。十年以后,德国的地位出现质变。德国人口超过八千万人,如今是欧盟内最大的国家,既拥有货币优势,又拥有日益增长的机构优势和外交优势。今天,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历史上首次可能面临霸权国家的崛起,其影响所有其他成员国的能力普遍存在着不均等的状况。
第三大变化紧跟着前《华沙条约》[70]国家内共产主义的结束而来。资本主义在易北河以东的恢复进一步改变了德国的地位,既恢复了德国作为欧陆“核心国”之地位(该国保守的理论家总是——有充分理由——坚持认为它会再次成为核心国家),也——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发展——削弱了法国和英国拥有而德国所没有核武器的意义。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东欧国家和一些苏联领土上的国家,普遍表达了要加入欧盟的愿望。就目前情况看,这些候选国的总人口大约有1.3亿人。如果把他们包括在内,便会使共同体的人口达到5亿人,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更为突出的情况是,欧盟成员国数量差不多要翻一番,从15个增加至约30个国家。一种全新的格局将引发讨论。
从历史上看,这三大变化是相互关联的。反过来看,正是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崩溃使德国走向统一,而德国的统一又催生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冲击波从东欧传到中欧,又传到西欧。然而,那些前因及后果仍有差异。这些过程的结局并不遵循单一的逻辑,不仅如此,较之欧洲一体化任何前期阶段,更大程度上而言,每种结局的影响皆是不确定的。我们面临着事发前的不确定性,用康德式的措辞[71],也许可以称之为后马斯特里赫特政论的三种歧义,它们表现出比一般想象更富于戏剧性的两难境地。
《马约》本身就带来了第一个歧义。其起源于德洛尔领导下的委员会的活力。1986年,在确保《单一欧洲法案》获得通过后,德洛尔说服欧洲理事会于两年后成立一个主要包括中央银行行长的委员会,由他本人主持,以就单一货币提出报告。1989年春天,理事会正式接受该委员会的建议。不过,正是民主德国的突然坍塌,促使密特朗在秋天的斯特拉斯堡峰会上与科尔缔结一份协议,从而将法德轴心的分量放在该项规划之后。当然,撒切尔针锋相对地表示反对。
然而,她完全被击败,尤其是败给了她最不喜欢的坐落于罗马的欧陆体制。每当《唐宁街岁月》[72]的女主人公来到欧洲,她那在其他方面不可征服的自信都令人安心地轰然倒塌。各章节的标题表明了这些。胜利的常规进程——“福克兰群岛[73]:大捷”→“瓦解左翼势力”→“帽子戏法”→“无需过多计划,更需生活方式”→“世界向右转”——被略微悲哀的语调所终止。我们迈入“无国界游戏”和“巴别塔快车”[74]的世界,这是一个“包含着豪言壮语和政治分赃的非英国式的结合体”,在那里,“政府首脑将不得不讨论一些足以令伦敦顶级会计师们惊恐不已的事情”,而且“欧洲共同体政策错综复杂性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智力和清晰思维的能力”。[25]
这种非典型的谦卑暗示有充分的根据。如同她经常充满悔恨、困惑的语气所显示的那样,撒切尔夫人似乎有些束手无策。其主旋律是:“追溯过去,如今可能看到”——然而,“我只能说,当时并非那么回事”。[26]激发她这种难堪的后见之明的情况有很多。而具有典型喜剧性的是1985年欧洲理事会的米兰峰会,该峰会确保《单一欧洲法案》中包括多数表决制。“克拉克西[75]阁下理性十足。”——“我离开时想到,让我的观点被理解是多么地容易(原文如此)”。不过我们再往下看……也就在第二天:“令我惊讶和愤怒的是,克拉克西先生突然要求表决。根据多数票的意见,理事会决定设立一个政府间委员会(IGC)。”[27]五年后,这个在米兰设置的先例在罗马被证明有恶劣的影响,这一次是在1990年10月的欧洲峰会上,正是安德烈奥蒂[76]的发难令撒切尔猝不及防。“只要与意大利人共事,要区分迷茫和阴险狡诈完全是困难的,”她颇感不幸地写道,“然而,就连我也没准备好应对事情会如何进展。”[28]在最后时刻,召集政府间委员会的一次投票再次摆到了她的面前,这一次是关于更具煽动性的政治联盟话题。她对自己掉进安德烈奥蒂那温柔的陷阱而勃然大怒,这也最终导致她的毁灭。在伦敦,杰弗里·豪[77]对她的反应持悲观态度,不到一个月,她被赶下了台。难怪她非常痛恨她的意大利同行们,以至于说:“更直白地讲,如果我是意大利人,我也会选择来自布鲁塞尔的支配权。”[29]
撒切尔尊重德洛尔(“显然有头脑、有能力且正直”),喜欢密特朗(“我偏爱法语的魅力”),也能够容忍科尔(“外交风格甚至比我更为直截了当”)。不过对安德烈奥蒂,她从起初就心存恐惧和厌恶。在她主政数月后首次参加七国峰会之时,她发现:
他对原则有一种明确的厌恶感,甚至坚信一个有原则的人注定是可笑的。他看待政治,就像一个18世纪的将军看待战争一样:一次阅兵场上的军事演习,场面宏大,军方精心组织,军队不会卷入冲突,而只是根据其表现出的军力宣示胜利、投降和妥协,为了合作而共享战利品。意大利政治体制需要的可能是能够进行政治交易的人才,而非坚信政治真理的人,这在共同体内被认为是合宜的。然而,我总觉得如此而为者实在是可恶。[30]
安德烈奥蒂对撒切尔的看法要更加直率。从一次次没完没了的专门处理英国回扣的欧洲理事会会议的表现来看,他说撒切尔使他想起因为租金问题而训斥租户的女房东。
在共同体各项事务中,作为重要的第三国,意大利不断增长的作用是这些年来的明显特点。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打下基础的1989年《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报告》是一个叫托马索·帕多阿-斯基奥帕[78]的意大利人草拟的,他是单一货币最有力的支持者,而且也正是另外一个意大利人——又是安德烈奥蒂——在最后一分钟的倡议增加了该条约1999年的自动期限,这使英国人和德国联邦银行不安。然而,在马斯特里赫特的磋商最后成形的版本本质上还是法国和德国的设计方案。巴黎的核心目标是成为一座金融大厦,取代德国联邦银行单方面的权力,从而成为邻国财富实际上的调节者,并拥有对欧洲货币区的法律上的中央权威,而在这样一个欧洲货币区,德国的利益将不再享有特权。作为交换,波恩接受了“趋同标准”的安全体系——实际上这是放弃了德国马克的苛刻条件,意大利单一货币的理论家们一向拒绝德国马克——以及有关“政治联盟”的所有的条款。
该条约的外交起源是一回事,而一旦实行,其经济效果则是另外一回事。十年后如期生效的货币联盟的社会逻辑是什么呢?在马斯特里赫特会议上所设想的那种系统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已是陈年往事:留给成员国的只有——必然减少的——在税收的竞争性层面上的平衡预算内的支出分配方案。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历史上致力于充分就业和传统福利国家的社会服务,它们对此类的热忱业已萎缩,或者说是在削减,将不再有更多的制度上的支撑。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前景。规划中的欧洲中央银行甚至比美联储的章程更加严格,它的唯一职责就是维护价格稳定。现有民族国家的保护和调节功能将被去除,稳健的货币成为唯一的调节者,如同凯恩斯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模式一样。
全新的元素——即未来货币管理机构的超国家性质——有助于加强这样一种历史性回归:它被提高至超过国家选民的地位,将更加不受来自大众的压力的影响,而且不仅仅是借助法令。简单说来,在此意义上,联邦制的欧洲不会是——如英国的保守派人士所担心的那样——超国家,也更不像国家。哈耶克[79]清醒地预见了这一点。他在1939年的一篇文章《国家间联邦主义之经济环境》中,极富激励之力且清晰地提出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现行逻辑。在论证这样一个联盟内的国家不会去追求独立的货币政策之后,他强调,宏观经济干预始终要求关于价值观及目标的共识。他继续写道:
很清楚,如此共识的有限程度将与一个区域内居民所拥有的观点和传统的同质性及相似性成反比例关系。尽管在民族国家里,民族主义神话助长了对多数人的意愿顺从,不过当领导政府的多数人的民族及传统不同的时候,人民是不愿顺从对他们日常生活的任何干涉的,这必然也很清楚。毕竟,如果包含着不同民族的联邦要避免遭遇其所包含的各类群体日益增长的反抗的话,那么,联邦体内的中央政府必须收缩其所管辖事务的范围,这只是一种常识。然而,在中央对经济生活的指导必然对不同群体进行区别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比这种中央的指导更为彻底地干涉人民的私密生活呢?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是,与民族国家相比,联邦体内的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生活的机会要少得多。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组成联邦的各国的权力将受到更多的限制,因此,在联邦组织内,我们业已习惯了的对经济生活的许多干预将无法实行。[31]
在这一描述中,《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使哈耶克所痛斥的凯恩斯的遗产的剩余部分被去除,西欧劳工运动的大部分成果都与此有关。不过,严格说来,这种前景的极端性引发了以下问题:在实践中,是否不会出现相反的逻辑?面对在国家层次上解除先前的对经济活动的社会控制所造成的严峻局面,为了避免联盟内部不同地区和阶层似乎不可避免的极化现象,不久以后——甚至提前——难道就不会出现要求在超国家层次上重新施加这些控制的呼吁吗?也就是说,为了建立能够重新调整的欧洲政治权力机构,单一货币和专一银行放松了哪些方面的管制呢?这可能就是雅克·德洛尔隐秘的赌博吗?雅克·德洛尔是货币联盟计划的发起人,也是一名政治家,其先前的全部政治生涯表明他忠于天主教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价值观,而对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持怀疑态度。
关于这种解读,哈耶克的设想很可能转向它的对立面——比如,由韦恩·戈德利[80]描述的前景。当条约即将被批准时,他注意到:
在马斯特里赫特方案中,不可思议的缺陷是,虽然该方案包括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和中央银行经营策略的整体规划,但是,从共同体方面来讲,并无任何关于堪比中央政府的机构的整体规划。然而,至少要有一套制度系统在共同体层面上执行所有目前由单个成员国的中央政府所执行的职能。[32]
也许,正是由于哈耶克担心这样的争论,所以到70年代,他改变了看法。德国担心如果德国马克被吸收进货币联盟,会出现通货膨胀,受此影响(当时,他在弗赖堡供职),哈耶克认定单一欧洲货币不仅不切实际,而且还是危险的方案。[33]从屈服于选民压力的民族国家政府手上夺得货币控制权肯定比以往更有必要。不过他如今了解,补救之法并非把货币控制权自下而上地交给超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而是自上而下地交给市场上相互竞争的私人银行,由它们发行相互竞争的货币。
就连原则性很强的右派也没有几个人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帕多阿·斯基奥帕称赞该方案是除了他自己的方案外唯一的严密的选择,也许他这么说是不怀好意。[34]不过,对这种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设想出来的单一货币对社会经济的稳定有何意义的疑虑却是十分普遍的,这种担心甚至出现在各国中央银行行长中间。目前,欧盟各国内差不多有2000万人失业,而如何防止萧条地区大范围的持续性的失业状况呢?英格兰银行行长警告,如果把货币贬值排除在外,仅有的调整机制就是大规模地削减工资,或者是人员外流;而欧洲货币机构[81]的负责人、负责单一货币技术准备工作的比利时—匈牙利银行家(著名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拉姆法鲁西[82]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他所参与的德洛尔委员会报告的一份附件中——如果“在欧洲货币联盟(EMU)内唯一可使用的全球宏观经济的工具是由欧洲中央银行实施的共同货币政策”,那么,其结果“会是一种毫无吸引力的前景”。[35]他指出,若货币联盟要发挥作用,共同的财政政策则是必需的。
然而,既然预算仍然是国内政治的中心论题,那么,如何才能够做到不由选举决定的财政协调呢?戈德利坚持认为“体制系统”的必要性,该系统只有在以下的基础上才可以构想:它必须在欧盟层面上以名副其实的超国家的民主制度为基础,并且首次在真正有效的负责任的欧洲议会上体现出真正的公众主权。阐明这一前提条件之后,就足以发现无论是成员国的官方话语抑或其民意,对摆在它们面前的选择级别均没有充分准备。
其次,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设想的欧洲内,德国的地位是何种状况呢?加快促成货币联盟的不仅仅是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的希望或担心。而归根结底,更为重要的则是法国政府的政治愿望,亦即将新近面积得以扩大的新德国塞进更为紧凑的欧洲框架之内,在这一框架中,利率不再只由德国联邦银行控制。在巴黎,置于超国家掌控下的单一货币的发明,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措施,防止德国国家霸权在欧洲的重新崛起。同时,甚至部分德国政界及公众舆论也颇具自缚桅杆、拒绝诱惑的奥德修斯[83]的精神,倾向于——至少声明——赞同这一看法。对于双方而言,单一货币背后的假设是欧洲货币权威可能意味着经济上最强大的民族国家亦即联邦共和国的权力的削减。
不过条约一经签署,完全相反的预计应运而生,因为自从20年代周边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后,德国的利率水平出现新高,并且德国在巴尔干地区出现外交举动——再一次,就像20世纪早些时候为奥地利的布局投下阴影一样——这两件事立即激起令人不安的记忆。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84]则非常尖锐地表达了另一种观点。南斯拉夫危机期间,波恩坚称唯有民族自决原则才能说服己方——当然那不大适用于人数较少的种族:车臣人、库尔德人和马其顿人[85]——对此,他写道:
德国支持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体的其他国家则表示反对,美国也强烈反对。在任何这类事务上,面对如此明显强大的“西方共识”,1990年之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会体面地退缩。然而新统一的德国根本不理会美国,并且终使共同体转变立场。德国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数日内共同体其他国家随即跟风承认。对于法国而言,共同体立场的大转变是尤为屈辱的……这两个新生的共和国如今是广大的德国在本国以东的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德国在欧洲的经济霸权现在是一种生活现实,我们其他欧洲人应当尽我们所能适应这种现实。在这些环境条件之下,推进联邦制将不会“勒住”统一后的德国强大的力量的“缰绳”。那将有可能使我们完全屈从于德国的霸权。[36]
毫无疑问,几个月之后在法国的全民公决中,如此担忧成为反对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活动的动员主题。在单一货币是将弱化还是强化大陆上最强大民族国家的问题上,法国选民分成了意见相反的两半。实际上,由密特朗和吉斯卡尔领导的大多数政治精英主张唯一可压制德国的优势地位的方法就是货币联盟。而由塞甘和维里耶[86]领导的反对派则反驳认为,货币联盟最有可能促成德国的主导地位。这种论争在第一次货币风波的背景下展开,它是由德国6月贴现率的上升引起的,在这场运动的最后一周,贴现率的上升把里拉和英镑排除在欧洲汇率机制(ERM,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之外。一年以后,在由德国联邦银行的方针激起的汹涌的投机狂潮之中,法郎宣告“沦陷”。
在伯纳德·康诺利[87]所著的《欧洲腐烂之核》(The Rotten Heart of Europe)一书中,我们如今已能看到对这些事件内幕的生动描述。标题和封面的粗俗就是一种误导:较之作者的人品,这更是一种精明的出版业自甘堕落的表现。该书具有偶尔欠缺品味及热衷闹剧的弊病。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它依然不失为一部文字功底深厚且专业的研究。事实上,该著相当引人入胜。作为布鲁塞尔共同体金融机构的最高级别内一名撒切尔夫人的私下支持者,康诺利在欧洲政界的态度与撒切尔的困惑全然相反。实际上,他的书展示了对每一个欧盟成员国内银行业和投票权之间联系的高度掌握:不但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英国,而且比利时、丹麦、葡萄牙以及爱尔兰均有详略结合的相关叙述。(唯一明显的例外是荷兰,它在自由经济和联邦政治之间的模棱两可的表现被以不耐烦的脚注形式表述。)沙文主义信条造就了世界主义的技巧。
康诺利的立场,不仅对单一货币,而且对不同货币的固定汇率的原则性的敌视——在他看来,后者是一种危险而无效的操控金融市场行为的企图,这种企图只会扼*无序经济体系的活力所依赖的经济自由。正如其简明扼要地所强调的那样:“遭受遏制的西方资本主义是招致毁灭的资本主义。”[37]他描述了1992~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内部的一番混战争斗,同情最坚定的德国反对派,他们反对向邻国对利率的忧虑作出让步,他尤其支持固执的赫尔穆特·施莱辛格[88],当时赫尔穆特·施莱辛格担任德国中央银行行长。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这份同情是策略性的——施莱辛格作为不妥协者而备受称道,其影响力会破坏汇率机制稳定的前景,如此就提前暴露欧洲货币联盟(EMU)无法生存。这与德国中央银行的理想化毫无关系,康诺利成功揭穿了该银行“独立”于政治影响之外的神话——其政策时常符合竞选舞台上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之需。
今天,德国政治阶层的民族主义之本能不再蛰伏,他们在重新思考货币联盟,因为在莱茵河对岸,[89]单一货币的前景看上去也是模糊一片。在马斯特里赫特的磋商中,德国有可能只获得幻影而非实实在在的东西吗?执政联盟的魏格尔[90]和中央银行的蒂特迈尔[91]均一直在提高对货币联盟的要求,他们声音洪亮地要求“严格遵守”该条约所附加的趋同标准(公共债务不高于GDP的60%,公共赤字不超过GDP的3%,通胀率在欧盟内三个情况最佳国家水平的1.5%之内,利率在欧盟内三个情况最佳国家水平的2%之内),除外还要严格遵守额外的一种“稳定条约”(Stability Pact)之标准。这种精心策划的呼吁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在马斯特里赫特所签署的文本中,趋同标准不是无条件满足的目标,而是可作为目标的“可参考值”,是否采取了足够的行动则是由委员会单独——不是联邦共和国,也不是其他政府——决定。这些条款由比利时的外交部部长菲利普·迈斯塔特[92]创设,这个拥有历史上某些特定记忆的国家有充分的理由坚持灵活性。如今的德国不顾及法律细节和小邻国的感受,其外交语调越来越像威廉二世。[93]
然而引人注目的事实则是,迄今为止,如阿多诺[94]所言的这种“日耳曼长篇演讲”并未遭遇阻止。巴黎不仅没有作出应对,反而急不可耐地去适应对方。对康诺利而言,这完全是可预料的结果。犹如维希政府[95]一样,在密特朗的领导之下,法国精英们一直屈从于德国经济的威力。为了和德国马克保持一致,法国精英阶层寻求制订惩罚性利率以便做强法郎,代价是大规模失业,如此而行是对法国人民的背叛。在最近每一次的民意调查中,康诺利注意到明显的对政界的普遍的疏远,他也饶有趣味地回忆起法国群众动乱的悠久传统,康诺利——自视为托利党派的激进分子——怀着无情的满足感期待法国再爆发一次革命,那时大众意识到为货币联盟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会发动起义摧毁这种寻求推动该联盟的寡头政治。[38]
如此预测在法国不再被认为是完全牵强之说,因为当下的前景并不引人注目,但依然令人忧虑。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全民公决揭示了法国舆论在单一货币可能带来的结果上的分歧之深——此为老问题,它会导致出现一个欧洲化的德国,还是会出现一个德国式的欧洲?雅克·希拉克在随后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必然导致相反推测所引发的紧张局面将继续困扰爱丽舍宫。因为没有一个法国政治家曾如此不停地在立场上来回转变,或者如此恰当地体现选民们那些不同的看法。凭借挑战罗卡尔—巴拉迪尔[96]时期的两党共识亦即做强法郎优先于创造就业的“单一思想”的政纲,希拉克登上权力之巅,在经过了几次失误的开端之后,执政的希拉克再次很不理智地恢复金融上的传统方式。此时的朱佩[97]政府实行着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以迫使赤字降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的基准。
然而,即便推出最严厉的预算也不能保证做强法郎。如同康诺利准确认定的那样,“趋同标准”排除了正常经济指标中的增长和就业状况,那毫无实际意义。那些标准是为使金融市场安定而设计的,它们满足的只是各个中央银行行长,但市场本身没有被糊弄,在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社会紧张的地方,货币迟早会贬值,无论价格有多么稳定、公共账目有多么平衡——如法国财政部1993年夏季时所发现的那样。希拉克政权当时在国内的作为只能在一些大城市强化业已突增的压力,此举是以失去选举诚信为代价的,其汇率也依赖于这种诚信。到11月末,大规模的街头游行预示着更大麻烦的来临。民调中政府支持度的骤跌在第五共和国[98]是史无前例的。它对德国中央银行言听计从的形象蕴藏着高度的政治风险。
希拉克恢复核试验可被看作一种显示军力——炫耀一份法国仍然拥有而德国所不具备的战略财富——来弥补经济疲软的笨拙尝试。此种尝试所带来的唯一结果是法国遭到国际性的羞辱。尽管这次反应大都是偏袒的或者是虚伪的(究竟有多少讽刺诗文反对以色列的炸弹),希拉克这种试验性的做法依然毫无意义。这些试验具有男人们外强中*风格,左右不了欧洲的政治均衡。核武器在欧洲已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正当法国外交本应当争取同盟以反对德国那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变得强硬的企图之时(法国的近邻如意大利、比利时和西班牙都完全乐意接受该条约),法国却平白无故地招致了充满敌意的孤立。如今希拉克之所为可以证明他是自布朗热[99]以来最反复无常、最无成效的法国政治家。
然而,与公认的观点相反的是,最终却是法国而非德国决定了货币联盟的命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界的自信尽管在上升,但依然相当脆弱。而更为冷静且更加严厉的、可以担任大众历史的提醒者的法国政府能够毫不费力地戳穿德国的牛皮。德国不能退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只能设法使之屈服。法国却可以退出。若非法国尽力削减赤字,就不会有欧洲货币联盟。对货币联盟的忠诚来源于精英阶层的政治考量以及那些传统的治国方略——一种决意要限制德国和维持法国国家权力的外交政策。做强法郎的社会经济成本由全民承担。在此绝对清楚的状况是,其外部目标与阿兰·米尔沃德从早期的一体化记录中所删除掉的国内愿景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德国是否在外交上重新主宰大陆对法国普通选民究竟有多重要——创造就业和收入增长难道不是更贴近国内的话题吗?在法国,接下来的几年有可能提供一个有趣的检验: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消费与战略究竟孰轻孰重。
与此同时,从罢工和游行中涌现出来的自下而上的压力仅仅是增加了上述困惑。表面上看,与全民公决之时相比,而今法国精英们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问题上存在着较少分歧。然而,并不能更肯定单一货币会实现其目标。德国受到了约束——还是没有受到约束?在新的欧洲,作为一项经济工程的货币联盟的模糊性与其应对内部潜在的民族竞争的政治逻辑的模棱两可程度相当。
最后,欧盟东扩的前景又是怎样的呢?就其自身的原则而言,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成员国之间没有分歧。所需补充的则是,对此也没有深谋远虑。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一个大方向并非由政治家亦非由技术官僚,而是由民意决定。选民没有参与,不过在充分考虑到各种结果之前,不同政治观点的社论写手和专栏作家们罕见地异口同声地宣称对其他途径不予考虑。同意东扩和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独立的精神一样。此并未充分考虑成本和效益,这方面已被欧洲一体化前期数十年来的史家们详加论述:意识形态上的美好愿望——本质上说,那些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的人们需要补偿——就是一切。政府完全被舆论共识拖着走。原则由媒体确定,政治家们只需搞清其应用。
在此问题上,西欧三个主要国家发生了分歧。起初,德国优先考虑使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斯洛文尼亚迅速加入进来。在这组国家中,波兰在德国的眼中仍然是最重要的。波恩的构想可谓直截了当。早先这些国家是享有特权的德国投资区域,它们将构成围绕德国和奥地利的信仰天主教国家的安全缓冲地带,其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可以——在明智地支持意见一致的政党的同时——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谐一致。法国则对扩展节奏更为谨慎,对以前与小协约国中的国家——罗马尼亚或者塞尔维亚——的联系比较警觉,因而不大倾向于如此挑选中意的地区。密特朗在布拉格曾明确地表达过,其最初更想要的是西欧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东欧之间在欧盟框架之外的一般性联合。
此外还有英国,它不仅努力让“维谢格拉德集团”[100]各国迅速加入欧盟一体化之阵营,而且力主最大程度接纳其他国家。在西方*中,唯独梅杰设想着欧盟最终要将俄罗斯纳入。英国人毫不掩饰其理由:按照这个观点,欧盟的范围越是广大,它就一定会越弱——因为其所包容的民族国家越多,凌驾于它们之上的真正的超国家权威就越难以存续。一旦延伸到布格河[101]流域甚或更远,欧洲联盟实际上就会演变成广大的自由贸易区,在伦敦看来,整个欧盟本就应该一直是自由贸易区。在此,欧盟范围的扩展则同时意味着体制方面的宽松和社会层面的放宽管制:接纳东欧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储备对西欧工资成本施加下行压力,这种前景是英国人所设想的方案的额外红利。
哪一种结果最有可能发生?当下,德国的规划方案最为春风得意。就欧盟草拟的政策来看,它是依照基督教民主联盟所设定的方向而为的。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下德国的考量与波兰、捷克及匈牙利的愿望趋同。在此颇有一种历史的嘲讽。自80年代后期起,匈牙利、捷克、波兰及稍后的斯洛文尼亚甚至克罗地亚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们开始向世界宣传,他们这些国家属于与西欧天然相似的中欧,完全不同于东欧。这些诠释涉及的地理上的广度可能过于极端。例如,维尔纽斯[102]被切斯瓦夫·米沃什[103]描述为欧洲中部的一座城市。[39]然而,如果波兰——更不用说立陶宛了——真的是在欧洲中部,那么,谁又在东部?可以想象,从逻辑上来看,答案必定是俄罗斯。但既然同样是这些作家,其中许多人——米兰·昆德拉[104]也被归入此类作家——都认为俄罗斯从不属于欧洲文明,[40]那么难题则是,一个地区同时自认为属于核心区域和边缘地带。
也许,虑及上述困难,来自美国的一位支持者、《旁观者》(Spectator)杂志的国外编辑安妮·阿普尔鲍姆[105]悄无声息地将波兰提升到西方国家之列,且将她的——不出意料造成了冒犯——对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考察命名为“东方与西方之间”。[41]而另一条出路来自米克洛什·豪劳斯蒂[106],他认为目前“中欧”的提法并不具备地理学意义,它只是表达了那些人——波兰人、捷克人和马札尔人[107]——在政治上的团结,他们反对共产主义,而完全异于那些不反对共产主义的邻居们。当然,1989年死亡的罗马尼亚人比这三个国家多年的反抗中死去的合计人数更多。然而,今天,这种概念的意义比起回溯过去,更多的是一种约定:本来它最初形成的目的是否认它们在冷战时期与苏联的经历有任何干系,而如今其作用是划定优劣,区分加入欧盟的候选国中的高级者和低级者——亦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
然而,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难以彻底避开其源头。“中欧”(Mitteleuropa)概念源自德国人,马克斯·韦伯的朋友弗里德里希·瑙曼[108]在一战期间创立了一套关于它的著名理论。瑙曼的构想仍然是吸引人眼球的议题。他所设想的中欧将以德意志日耳曼民族为核心融合普鲁士的工业效率和奥地利的文化魅力组织起来,并且“从维斯杜拉河到孚日山脉”[109],[42]在一个广大的关税共同体——关税同盟 (Zollgemeinschaft) ——和军事协议内,吸引周边卫星国。这样一个联合起来的中欧将成为他所言的“宗主国”,即一个能够抗击英美和俄罗斯帝国的“超级国家”。作为路德教派的一名牧师,他遗憾地指出,那将会是天主教占绝对优势——为此付出的必要代价——的但又是一种宽容的秩序,为犹太人及少数民族留出了空间。它所创立的联盟不会是联邦制的——瑙曼也很早预言了今日那种权力下放原则之学说。除了经济、军事之主权,所有形式的主权皆由各成员国保留着,它们保存着各自的政治认同,多种职能的首都亦将消失,而给予各种不同的城市——汉堡、布拉格、维也纳——特定的行政功能,如同今天的斯特拉斯堡、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43]以此构想为背景,不难看出,“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的中欧远景的构想要求是如何在联邦共和国找到政治资源的。
不过,考虑到欧盟东扩现在在欧盟内部被奉为官方的——即使仍模糊不清的——政策,这一过程是否有可能被限定于一批挑选出来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呢?想要加入的申请者还在增加,且无阻止它们的明显分界点。正如J.G.A.波科克[110]敏锐观察到的那样,欧洲并非一块大陆,而是连绵不断地延伸至白令海峡[111]的大陆块上未封闭的次大陆。它与亚洲唯一的自然边界是位于赫勒斯滂的一片狭长水域,利安德和拜伦勋爵[112]曾横渡此片水域。平原和草原向北一直延伸至突厥斯坦。文化疆界比地理疆界更无法清晰划定:穆斯林的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113]在基督徒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西数千英里,古代人在那里划定了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难怪论及该问题的首个史学家希罗多德[114]就曾指出:“欧洲的边界不甚明了,无人知晓其界终于何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欧罗巴(他是指由宙斯所劫掠之美人)[115]乃亚细亚人,从未踏上今日希腊人所称为‘欧洲’的土地,仅仅通过航行(骑在公牛的背上)从腓尼基[116]抵达克里特岛。”也许,希罗多德的嘲讽还留给我们一个教训。若斯洛伐克是加入今日欧盟的候选国,为什么罗马尼亚不行呢?如果罗马尼亚是,那么为何摩尔多瓦[117]不行呢?若摩尔多瓦是,为什么乌克兰不行呢?若乌克兰是,为什么土耳其不行呢?数年之后,伊斯坦布尔将在被称作“欧洲”——不管你如何定义它——的地方取代巴黎成为最大的城市,而对此没人会提出异议。至于莫斯科,自叶卡捷琳娜大帝[118]在一项著名法令中宣称“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以来,已然过去两个多世纪。从那以后,从苏沃洛夫、普希金[119]时代起,欧洲的文化史和政治史均强化她的这一说法。戴高乐关于“自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120]之欧洲的构想将不会轻易地消失。目前在关于欧盟扩张的讨论中所有的停滞只是那些最靠近欧盟的国家的方便手段,或表现了布鲁塞尔官僚机构的想象力的局限。它们不会拒绝这种扩张的逻辑。
1991年,J.G.A.波科克指出:
“欧洲”……在文明和稳定的区域之意义上再次成为一个帝国,该地区必须决定是否对其边界上而非体制内的暴力文化行使政治权力,或者拒绝行使这种权力: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如果两者之一有机会成为奥地利人;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如果土耳其被接纳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这些均非由市场来决定而是由国家进行决策的。[44]
然而,既然欧洲不是一个在更为熟悉的意义上——中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的帝国,而仅仅是(如他所言)一个没有关于边疆的共识的“众多国家的组合体”,那么,它的“界域”尚待各国政客们划定就不足为怪了。不过自他的著述后,为弥补这个缺陷,真知灼见并不缺少。
譬如,作为最早也是最为热情地倡导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尽快加入欧盟的人之一,蒂莫西·加顿·阿什[121]最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过去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试图向西方读者解释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华沙属于中欧而非东欧,我是最后一个需要让别人来提醒波兰和阿尔巴尼亚之间巨大差别之人,”他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如此写道。“不过如果要说在所谓维谢格拉德集团的这些中欧民主国家和如波罗的海国家或斯洛文尼亚之间,存在着一条极为清晰的历史分界线,这就是在促成一种新的神话。”[45]相反分界线必定在“第二欧洲”(亦即包括大约20个他所描述为处在加入欧盟“进程之中”的国家)与“第三欧洲”(亦即没有上述前景的国家,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在地图上夹杂在邻国间难以察觉的——塞尔维亚)之间划定。
较之那种其所代替的虚幻之区分,上述大有裨益的对分方法可能更难以持久。《整合欧洲》(Orchestrating Europe)是一本有关欧盟正式确立的以及对那非正式的复杂机制拥有开阔视野和强烈激情的指南读物,在结尾处,基思·米德尔马斯[122]展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他认为,欧洲被一道从摩尔曼斯克到卡萨布兰卡[123]的具有潜在威胁的圆弧所包围。为了保持一定的距离,欧盟需要一条隔离带,由有望加入共同体的“第二圈”国家组成,它们将保护欧盟免受来自“第三圈”——即俄罗斯、中东和黑非洲——的危险。照此理解,这些各自的缓冲带逻辑上有三个地区:东欧,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和土耳其,以及马格里布[124]地区。不过米德尔马斯认为,前两个区域最终可以加入欧盟,而第三个则是不太可能。这是因为,“马格里布地区的国家作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屏障是无关紧要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除了有少量非法移民外,并不存在威胁”。事实上,与之相反,“‘祸根’来自北非本身”。[46]如果这一划分方式比加顿·阿什的划分方法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话——他明确表示要把土耳其排除在欧洲之外,那么,它实际上在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行,和所有这类譬喻一样陷入困境。到目前为止,每一种想划定欧盟未来边界的尝试的结果都是它自身的解构。
作为入盟之门槛而正式设计出来的“欧洲协定”已由6个国家签字: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此外,还有4个国家即将签字(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当前,记下这一点就已足够。而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以及波斯尼亚的余下部分也将加入其行列,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种前景——我们可以称之为反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骨牌向里倒,而不是向外倒——意味着英国的预想会发生吗?带着一种朴实无华的民族口吻,哈罗德·麦克米伦曾谈及他的愿望,当共同体直面广大自由贸易区的良性的压力时,它就会“如同一杯茶中的糖一样融化”。[47]这仍然是他的继任者们所喜爱的前景,他们的考虑是,加入的成员国越多,在实践中共同享有的主权就越少,而联邦梦想彻底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它究竟有多真实呢?
毫无疑问,扩展到20多个国家的欧盟将在根本上改变其性质。如果其现有决定只是东扩,那么,仅仅是整合“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成本就得增加60%的欧盟预算。而今每一国家国内呼吁都是要求减少税收之时,现有成员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负担。于是,要么减少对西部农业地区和较为贫困地区的现有扶持,而这些地区的选民们拥有抵制上述措施的选票;要么修订共同体法律条款以为新加入者创立第二等级成员国资格,它们将不享有第一等级成员国加入时得到的利益。
这些只是欧盟的快速扩张中财政方面令人头痛的问题。对前共产主义经济体来说也有实质性的后果。如果说坚持货币联盟的趋同标准的努力已经使得繁荣的西方社会处于崩溃边缘,那么,人们可以指望贫穷的东方国家接受那些标准吗?从前的候选国无论在一开始多么贫穷都无需攀登这样一座宏观经济的悬崖。考虑到欧洲货币联盟的要求,支持扩张的热心人开始呼吁完全抛弃单一货币的想法,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对加顿·阿什而言,华沙和布拉格的需求至少与伦敦的智慧是一致的。“眼下,欧洲也许可以更多地采纳英国的思维方式”,关于货币联盟,他写道,“在此使用‘英国’一词,意味着我们独特的思想传统更为深层的意义:怀疑、实验和务实。”[48]一个不太可能的人物——雅克·阿塔利[125]从相反的角度提出同样的怀疑,指出欧洲货币联盟与欧盟东扩也许不能和谐共存,他认为单一货币的推行是正确但如今已失去方向的事业,东扩是一项将要偏离联邦式欧洲设想的德国规划,而迷恋于美国文化的大多数的民族国家精英对此设想不感兴趣。欧洲不喜欢自己,他在密特朗执政结束之时心事重重地注意到这点。[49]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不会那么轻易地失效。然而,东扩的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为新旧成员国所带来的经济陷阱之中。即使为过去的“被奴役国家”进行各种削减计划——“共同农业政策”、“结构基金”以及单一货币诸方面,也将依然存在着更为根本性的、纯政治性质的困难。成员国数量翻一番完全有可能削弱欧盟的现有制度。在部长理事会中,原有的六国或九国平衡已经处于不妙的境况。今天,五个最大的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占有80%的欧盟人口,却只在理事会中拥有一半多的选票。如果目前的10个前共产主义申请国都成为成员国,上述五国的份额将会进一步下降,同时,欧盟里贫穷国家的比重——那些如今有资格加入的国家——将由15个国家中的4个上升为25个国家中占多数的14个。
选票权重的改变会以某种方式使“法制国家”回归到“真实国家”。然而,这无法解决由东扩引起的可能最棘手的问题,这体现在数字之中。欧洲卫星国几乎同欧洲持续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多(据最近统计,“东欧”国家有16个,“西欧”有17个——若将瑞士包含于内的话),人口为后者的1/3。不管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如何巧妙地伪装,这种规模的盟友扩张预示着将出现体制方面的僵局。照这种情况,欧洲议会的规模可能增至800名代表,委员会代表数量增加到40名;在开始进行正规事务之前,出席理事会的各国部长每人作一场十分钟的开场白,将导致会议长达5小时。现有制度的复杂程度人所共知,委员职务要小心翼翼地轮换,政府间要进行费力的谈判,各式各样的部长和议会否决层出不穷,该体制行将超负荷运作且面临瘫痪。
在如此条件之下,难道欧盟的扩张不会必然意味着松动吗?此可谓伦敦的赌博,从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门(FCO)到《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LS),都或多或少地公开表达了这种意思。长期来看,官方的思路是,东扩必定意味着去联邦化。然而,这是唯一的逻辑推理吗?在此,我们遇到了最后一种歧义。这是因为,体制僵化之前景难道不会恰好造成一种比当今所存在的更为集权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以之为一种功能上的绝对需要吗?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12~15个成员国差不多可以进行协调,无论是多么困难。而增加到30个,实际上就排除了这种可行性。当大国的数量越来越被较小国家的数量超过之时,加入欧盟的国家越多,部长理事会中人口和代表之间比例的不一致就越大,整体决策能力变得越来越弱。其结果将与英国人的预期相反——不是联邦权力的削弱,而是在国家投票权被重新分配且多数决策成为常态的新的宪法决议中联邦权力的集中。换言之,成员国规模问题可能会迫使体制上的节瘤被剪除,而这些毒瘤恰好是宽松自由贸易区的支持者所竭力去避免的。欧盟扩张可以阻止及扭转深化的现象,但也有可能使问题突然加速出现。
如今,欧盟面临的三个重要问题——单一货币、德国的作用和成员国的增加——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均表现出基本的不确定性。在每一问题上,歧义的特殊形式如出一辙。一组含义是如此极端,以致似乎也很容易转向它的反面,导致一种特别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就是未来的欧洲建于其上的政治流沙。
注释:
[1]Alan Milward,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5—1951,London 1984 p.492.
[2]Alan Milward and Vibeke Sorensen,‘Interdependence or Integration: A National Choice’,in Alan Milward,Frences Lynch,Ruggierro Ranieri,Federico Romero,Vibeke Sorensen,The Frontier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History and Theory 1945—1992,London,p.20.
[3]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London 1992,p.xi.
[4]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p.447.
[5]‘Conclusion: The Value of History’,in The Frontier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pp.194,201.
[6]关于那些官僚政客们对一体化敌视之程度,参见Gérard Bossuat,‘Les hauts fonctionnaries français et le processus d'unité en Europe occidentale d'Alger à Rome (1943—1958)’,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istory,No.1,Vol.1,1995,pp.87—109。
[7]Christian Pineau, Le grand pari: L'aventure du traité de Rome,Paris 1991,pp.221—223.
[8]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p.334.
[9]François Duchêne,Jean Monnet: The First Statesman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 1994,pp.226—228,198.
[10]Duchêne,Jean Monnet,p.228.
[11]Jean Monnet,p.364.
[12]Jean Monnet,p.270.
[13]Jean Monnet,Mémoires,Paris 1976,p.577.
[14]Jean Monnet,p.357.
[15]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p.375.
[16]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p.433.
[17]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pp.395,432.
[18]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p.433.
[19]The Frontier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p.195.
[20]‘Allegiance: The Past and the Future’,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No.1,Vol.1,1995,p.14.
[21]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p.186.
[22]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pp.447—447.
[23]Duchêne,Jean Monnet,p.390.
[24]Jean Monnet,p.20.
[25]Margaret Thatcher,The Downing Street Years,London 1993,pp.727,729—730.
[26]The Downing Street Years,p.536.
[27]The Downing Street Years,pp.549—551.
[28]The Downing Street Years,pp.765—766.
[29]The Downing Street Years,pp.742.
[30]The Downing Street Years,pp.70,742,736.
[31]Friedrich Hayek,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Chicago 1948,pp.264—265.以今日之见,哈耶克的洞察力是如此引人注目,这由其写作的背景与欧洲货币联盟的最终来临之间的距离表现出。围绕着对联邦制的不同观念和不同方案的争论可参见《新联邦季刊》(The New Commonwealth Quaterly),此为探讨这些问题的最好的平台之一,他于1939年9月发表的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篇。其直接背景是跟随慕尼黑的、对阻止纳粹扩张的联邦制联盟的突如其来的热情,美国政论家克莱伦斯·斯特莱特(Clarence Streit)向全世界15个民主国家发出号召以结成联盟共同对抗轴心国引发了这股热情。在学术思想方面,哈耶克受到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过去50年干涉主义的‘去规划’”(见Economic Planning and Intellectually Order,London 1937,p.248;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London 1907,p.98)以及阿克顿(Acton)“在对民主的所有制约中,联邦制是最有效和最适宜的”信条的启示。在政治上,他似乎怀疑斯特莱特提出的结成从美国经英国到澳大利亚的民主联盟的建设(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和罗宾斯一样赞成一旦战争爆发便成立英法联盟。到《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出版之时,出于为战后所作的考虑,他推荐了艾佛·詹宁斯(Ivor Jennings,著名法学家——译者注)现已被人遗忘的《西欧联邦》(A Federation for Western Europe,1940)。不过,当欧洲一体化最终根据舒曼计划而开始进行之时,他因煤钢共同体统制性过强而不予支持。
[32]Wynne Godley,‘Maastricht and All That’,London Review of Books,8 October 1992.
[33]Friedrich Hayek,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 The Argument Refined,London 1978,pp.19—20.
[34]Tommaso Padoa-Shioppa,L'Europa verso l'unione monetaria,Turin 1992,pp.xii,189.
[35]‘Macro-coordination of fiscal policies in 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Report o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the Europe Community,Luxembourg 1989,p.101.
[36]Conor Cruise O'Brien,‘Pursuing a Chimera’,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3 March 1992.
[37]Bernard Connolly, The Rotten Heart of Europe,London 1995,p.64.
[38]The Rotten Heart of Europe,pp.391—392.
[39]Czeslaw Milosz,‘Central European Attitudes’,in George Schöpflin and Nancy Wood(eds),In Search of Central Europe,London 1989,p.116.
[40]Milan Kundera,‘The Tragedy of Central Europ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6 April 1984; see also George Schöpflin,‘Central Europe: Definitions and Old and New’,In Search of Central Europe,pp.7—29.
[41]London 1994。同大多数这类作者一样,阿普尔鲍姆的观点也时常是前后矛盾——在中世纪,波兰被视为“普通的中欧国家”:p.48。
[42]Friedrich Naumann,Mitteleuropa,Berlin 1915,pp.3,129—131,222ff,254ff.
[43]Naumann,Mitteleuropa,pp.30,67—71,232—238,242.
[44]J.G.A. Pocock,‘Deconstructing Europe’, London Review of Books,19 December 1991; now in The Discovery of Islands,Cambridge 2006,p.287.
[45]Timothy Garton Ash,‘Catching the Wrong Bu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5 May 1995.
[46]Keith Middlemas,Orchestrating Europe,London 1995,pp.664—665.
[47]Duchêne,Jean Monnet,p.320.
[48]Garton Ash,‘Catching the Wrong Bus?’.
[49]Jacques Attali,Europe(s),Paris 1994,pp.15,145—150,181—199.
[1] 参见“前言”注释。
[2] 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1924~2003),德裔美国人、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新功能主义学派创始人,著述甚多,代表作《欧洲的统一》在1997年被《外交》评为20世纪国际关系50本重要著作之一,他将一体化界定为“说服若干不同国家环境里的*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转向一个新中心的过程”。
[3] 阿兰·米尔沃德(Alan Milward),当代英国学者,伦敦经济学院荣誉教授,认为欧洲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民族国家自我拯救的内在之需,亦为对“一体化”和“相互依存”这两种国际框架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
[4] 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所创,他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三大革命”。他反对古典经济学放任自流的政策,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其名著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5] 参见“前言”注释。
[6] 比利牛斯山(Pyrenees)位于欧洲西南部,山脉东起地中海,西止大西洋,分隔欧洲大陆与伊比利亚半岛、法国与西班牙。北海(North Sea)位于大不列颠岛以东,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南和欧洲大陆以北,属于北大西洋,西南有凯尔特海,东部有波罗的海,向北是挪威海。
[7] 前述舒曼(Robert Schuman,1886~1963)是法国政治家,曾任总理和外交部部长、“欧洲议会”首任议长,以其名字命名的“舒曼计划”为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铺平道路,他与让·莫内(Jean Monnet,1888~1979)都被称为“欧盟之父”。阿登纳(Adenauer,1876~196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1949~1963)。德·加斯贝里(De Gasperi),二战后意大利总理。
[8] 《单一市场法案》(Single Market Act)源自1957年《罗马条约》,它确立了欧共体在1992年年底前建立单一市场的目标,而作为“德洛尔计划”(Delors Commission)的一部分,该法案先后在卢森堡和海牙签署。
[9] 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5),法国政治家,长期出任法国总统(1981~1996),1981年上任而结束保守派此前23年的统治;上台后推行改革,认为经济复苏必须和“新文艺复兴”相伴而行。
[10] 撒切尔参见“前言”注释,她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替代物——新自由主义的推行者。
[11]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强调宗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主因;诸多 “韦伯命题”影响后世;与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12] 此处“完全”用斜体(原英文版本中的“absolutely”用斜体字)加以强调,下同。
[13] 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第三共和国总理,其政治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为一战协约国的胜利及《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贡献甚巨,被誉为“胜利之父”。
[14] 鲁尔区(Ruhr)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下游支流鲁尔河与利珀河之间,处于欧洲十字路口,被称为“德国工业的心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该地曾被共管,也曾被法国等国家占领。
[15]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德国政治家,被公认为最杰出的政府总理及跨世纪政治家,二战时因不愿与纳粹合作而两度被捕;他使德国在二战后重获主权进而强盛,创造“经济奇迹”,所谓“阿登纳时代”的“阿登纳印记”影响至今。居伊·摩勒(Guy Mollet,1905~1975),法国政治家、总理,1946~1969年任社会党*,签署建立共同市场和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条约,曾出任戴高乐政府的国务部部长。
[16] 《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是1957年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基础上由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政府在罗马签署的《欧洲经济合作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两条约合称《罗马条约》,它标志着“欧共体”正式成立,是迈向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步骤。
[17] 艾哈德(Ludwig Erhard,1897~197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63~1966),英美共同占领区经济委员会主席,曾在阿登纳内阁中任经济部部长,后接替阿登纳担任总理,辞职后成为基督教民主联盟名誉主席。
[18] “苏伊士运河危机”(Suez Crisis),是指1956年10月29日英国、法国与以色列联合对埃及发动的军事行动,目标是夺取运河掌控权,后美国、苏联均介入,11月6日达成停火决议。这场战争标志着美苏成为主宰中东乃至全球的真正力量。
[19] 阿尔及利亚战争(Algerian War,1954~1962),是指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它对法国政坛形成巨大冲击,导致戴高乐重掌权力、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结束并由第五共和国取而代之,法国签署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依云条约》。
[20] 伊斯梅利亚(Ismailia)市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省会和最大城市,位于苏伊士运河西岸,在北面的塞得港和南面的苏伊士城之间,为战略要地,而运河在该地加宽,隔运河向东就是西奈半岛。
[21] 皮诺(Christian Pineau,1904~1995),法国二战后杰出的政治家,曾任战后亨利·克耶政府的公共工程、交通和旅游部部长,1956年出任社会党领袖摩勒组阁的政府的外交部部长。
[22]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英国20世纪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二战期间任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副首相等职;1955~1957年出任首相。
[23]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法国政治家、作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被尊称为“戴高乐将军”,二战期间创建并领导自由法国政府(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抗击纳粹德国,战后成为第五共和国总统。任内提倡东西方“缓和与合作”,主张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强调泛欧外交,减少美英影响,其思想被称为“戴高乐主义”。
[24] 沃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1901~1982),德国政治家、法学教授,1958年成为“欧共体”委员会首任主席,“哈尔斯坦主义”由联邦德国政府首任总理阿登纳倡导,主张如下:不承认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代表整个德国;不同与民主德国建交的任何国家(苏联除外)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等等。
[25] 欧盟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作为欧盟决策机构之一,由各成员国的政府部长组成,正式名称是“欧盟理事会”,其官方内部简称“理事会”,其任务是协调各国事务,制定欧盟法律和法规。
[26] 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926~ ),曾任法国总统(1974~1981),因主持起草《欧盟宪法条约》被誉为“欧盟宪法之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Heinrich Waldemar Schmidt,1918~2015),德国政治家,曾任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主席,国防部部长、经济部部长、总理等。
[27] 欧洲货币体系(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是1979年在德、法两国倡议下由欧共体八个成员国所建立的,它将各国货币汇率相对固定,共同应对美元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orders)是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1944年西方主要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开会建立,按照美国利益制定原则、实现美国经济霸权,它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后因美元危机以及体制方面的诸问题,该体系于1973年终结。
[28] 让·莫内(Jean Monnet,1888~1979),法国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总设计师”,享有“欧洲之父”美誉。
[29] 弗朗索瓦·迪谢纳(François Duchêne),法国当代学者,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非军事强权”概念。
[30] 乔治·杜哈梅尔(Georges Duhamel,1866~1984),法国著名作家,认为美国物质主义是庸俗的信号,它威胁法国文明,有遮盖法国文明的可能;作品包括《文明》等。
[31] 安德烈·马尔罗(Andrê Malraux,1901~1976),法国小说家、演说家,能说会道,口若悬河,从不谈论其家庭和早年生活,他在《反回忆录》中说:“我认识的作家几乎都爱他们的童年,而我憎恨我的童年。”
[32] 应为阿马迪·彼得罗·贾尼尼(Amadeo Peter Giannini,1870~1949),美国美洲银行的创始人,一生具有传奇色彩:只有小学文凭但能用各种语言与人打交道;父亲因1美元贷款被打死,他却将钱款无息贷给贫民;他在欧美秘密建立意大利银行分行网络;晚年成为“全美第一银行家”,是改写美国金融史的巨人。
[33] 应为伊瓦尔·克鲁格尔(Ivar Kreuger,1880~1932),瑞典土木工程师、金融家、企业家,因企业实际已*、只是尚未宣告,最终在巴黎自*,他也被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骗子”。
[34]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Dulles,1888~1959),美国政治家、前国务卿,出身政客世家,1911年参加华尔街大垄断组织,他是许多大公司和银行的董事,与洛克菲勒财团有密切联系。
[35] 不太可能是纳粹时期的内政部长、后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处绞刑的弗里克(Flick,1876~1946)。此处可能是与纳粹有直接关系的弗里克家族财团,其创业者、出生于德国北威州普通农民家庭的弗里德里希·弗里克(1883~1972)曾加入纳粹党,被希特勒授予“国防经济领袖”称号,其企业成为纳粹军队最大的军火供应商,因而大发战争财,后虽被宣布为战犯,被判处七年监禁,但提前出狱后继续扩展其事业,到50年代他被媒体称为“可以买下半个德国政坛”。
[36] “荣誉侍卫”(Companion of Honour)或曰“荣誉同伴者”是英国国王传统上所授予的国家最高荣誉,该勋衔是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
[37] 约翰·杰伊·麦克洛伊(John Jay McCloy,1895~1989),美国律师、银行家,曾任世界银行行长(1947~1949)。
[38] 里诺(Reno)是美国有名的“离婚城市”,在内华达州西部,凡欲离婚者,只须在该市住满三个月,即可离婚。此处寓意就是离婚手续方便。
[39] 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Sergei Mironovich Kirov,1886~1934),他是20世纪20~30年代苏联联共(布)的主要*之一,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各一枚,后来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地名、城市、军舰等。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暗*,而后被葬于莫斯科红场。
[40] 两者均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作品:前者是格林(Graham Greene)1932年出版的小说,里面有“东方快车”,后在美国出版时易名为《东方快车》;后者是美国导演斯坦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1932年拍摄的同名影片,而非指我国著名作家张恨水1935年创作的同名小说。
[41] 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1971),美国政治家、国务卿(1949~1953),曾促使美国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任职期间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成,同时他也是顽固的反共分子。
[42] 此处的哈里曼应为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1986),美国商人、外交家、政治家,民主党人,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驻英国大使、美国商务部部长和纽约州州长。鲍尔(Ball)指的是二战前后的政治家鲍尔,他的家族类似于肯尼迪家族,曾出资兴建鲍尔州立大学的前身鲍尔师范学院。
[43]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亦称“马歇尔援助计划”),官方称“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的经济援助、协助重建之计划。1947年6月5日,它由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时率先提出,故名“马歇尔计划”,它于当年7月正式启动,持续4年;西欧各国总共接受美国各种形式的援助130亿美元,该计划对欧洲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44] 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e,1920~2003),平民主义政治家,1953年发起倡议,主张保护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利益、反对征收重税,这一运动被后世称为“布热德运动”,他的演说颇受欢迎,其观点也被称为“布热德主义”(Poujadism)。
[45]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1907~1982),法国政治家,曾任总理(1954~1955),其家族是犹太裔的葡萄牙人。
[46] 约翰·梅杰(John Major,1943~ ),英国政治家、首相(1990~1997),曾出任撒切尔夫人内阁财政部秘书长、外交大臣及财政大臣;2001年下议院大选后淡出政坛。鉴于其前任撒切尔夫人和继任者布莱尔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夹在中间的梅杰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47]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美国第34任总统(两任,1953~1961)、陆军五星上将,北约首任最高统帅。
[48] 此处马蒂似应为法国的弗朗索瓦·马蒂(Gabriel Auguste François Marty,1904~1994),曾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以及巴黎大主教。
[49] 巴茨凯尔主义指的是政敌们在某些政策上存在着一致或相似的观点,其源自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英国温和的保守党代表R.A.巴特勒(Butler)与温和的工党代表休·盖茨凯尔(Gaitskell)的政治主张达成共识,亦即所谓“巴茨凯尔共识”(Butskellite Consensus),于是当时人们用巴特勒之姓氏前一半与盖茨凯尔的后一半合成了名词——“巴茨凯尔主义”(Butskellism),后来用以描述这种政敌间的共识。
[50] 克莱门特·理查·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英国工党领袖,在1945年大选中意外击败丘吉尔,是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工党党魁,还被视为20世纪和平时期最具效率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亦即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1894~1986),保守党政治家、战后英国首相(1957~1963),1984年被英国女王册封为世袭贵族;其任内见证了大英帝国的衰落,因“普罗富莫事件”而辞去首相。
[51] 保罗·艾迪生(Paul Addison,1943~ ),英国当代学者及史学家,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英国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代表作《通向1945之路》的全名是《通向1945之路:英国政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Road to 1945: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52] 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政治用语,它认为平民被精英所压制,而国家作为一种工具需要改变这些自私自利的精英团体,以便改善全民的福祉和进步;承诺移除“腐败的”精英阶层,倡导“人民优先”;1980年以后该术语多用于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场合。
[53]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创立机械唯物主义体系,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忏悔录》《新爱洛漪丝》等。
[54] 易北河(Elbe)是中欧地区主要河流,约1/3流经捷克共和国,2/3流经德国;全长1165公里,发源于捷克、波兰两国边境山麓,穿过捷克西北部的波希米亚,进入德国东部,并在下萨克森州库克斯港注入北海。
[55] 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是美国第37任总统(1968~1974),因1972年著名的“水门事件”而于1974年被迫辞职;他是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次数最多者(43次),还两度荣获“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称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 ),德国犹太人后裔,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尼克松政府、福特政府时期的国务卿。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戴立克(Robert Dallek)著有《尼克松与基辛格:权力伙伴》(Nixon and Kissinger: Partners in Power)。
[56] 《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1986年2月由欧共体理事会签署的法案,是德洛尔计划的部分内容,其目标是在1992年年底前实现商品、资本、劳务、人员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
[57] 雅克·德洛尔(Jaques Delors,1925~ ),法国政客,1979年当选为欧洲议会首次普选产生的议员,1981年担任密特朗政府经济和财政部部长,1984年被推举为欧共体主席,1987年他制定《为一体化的成功而奋斗》报告,通称“德洛尔计划”。
[58] 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1930~ ),德国政治家,1973~1998年任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主席,1982~1998年主政,是俾斯麦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1982年通过不信任投票战胜对手施密特,成为战后唯一通过这种方式上台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两德统一中发挥关键作用,且对一体化进程作出贡献。
[59] 科克菲尔德勋爵(Lord Cockfield),英国政治家,曾担任撒切尔内阁工业大臣(1982~1983)及负责完成内部市场项目的欧盟专员,在强调单一市场原则方面与撒切尔观点一致;后出任欧盟欧洲委员会副主席,专门负责“1992年欧洲单一市场计划”。
[60] 共同农业政策(The 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CAP)是欧盟的一项核心制度,是以建立关税同盟和农业共同市场为目标的《罗马条约》的中心内容之一,它始自1962年,目的是鼓励农业生产;后历经多次改革,核心是解决欧盟的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问题。
[61] 结构基金(Structural Funds)是欧盟两大基金之一,是旨在促进经济与社会整合的计划;结构基金主要来自四个部分,其计划包括欧盟优先目标、社区行动和创新措施。
[62] 欧洲理事会(The European Council),欧盟最高决策机构,又称欧盟首脑会议或欧盟峰会,它由欧盟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及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通常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它是1974年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的提议下宣布成立的,当时被称为欧洲经济体首脑会议。
[63] 斯特拉斯堡(Strasburg)是法国东部城市、最大边境城;卢森堡是一个被法、德、比包围的内陆小国,卢森堡市(Luxembourg)作为卢森堡的首都位于欧洲西北部,欧洲及欧盟多种组织均在这两地设立总部;布鲁塞尔(Brussels)作为比利时首都和最大城市则是欧盟主要行政机构所在地,有“欧洲首都”之誉,欧盟、北约总部在此安营,另有200多个国际行政中心及超过1000个官方团体在此设立办事处。
[64]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简称《马约》)是1991年12月欧共体第46届首脑会议上由12个成员国在荷兰东南部林堡省的马斯特里赫特城所草签的包括《经济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的《欧洲联盟条约》,该条约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
[65] 普鲁士(Prussia)位于德意志北部,曾为普鲁士王国(1701~1947)及后来德意志帝国一省,历史上长期作为普鲁士公国领地及德境内最强邦国,近代效仿路易十四的封建专制而逐渐强盛,19世纪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德国并最终击败法国,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它是德国专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源。
[66] 皮埃蒙特(Piedmonte),意大利西北部一个大区,三面被阿尔卑斯山山脉环绕,面积为2.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430万人,首府是都灵;中世纪成为萨伏依领地,后升为公国,1720年,萨伏依公爵成为撒丁国王,后发展为撒丁-皮埃蒙特王国,该国成为欧洲重要的封建专制王国。
[67] 此处应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作家、哲学家,被视为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68]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世界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官,法兰西第一帝国缔造者,颁布《法国民法典》等,完善了世界法律体系,执政期间称霸欧洲,除英国外欧洲其余各国都向拿破仑臣服,造就了庞大的拿破仑帝国体系。
[69] 可能是19世纪后期奥匈帝国的爱德华·塔菲伯爵(Count Eduard Taaffe),曾短期担任首相(1868年9月至1870年1月)。
[70] 《华沙条约》(Warsaw Pact)是一个军事条约,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里除南斯拉夫外的八个国家针对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于1955年在华沙签订《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并正式成立军事政治同盟——“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总部设在莫斯科。1991年7月1日,该组织正式宣告解散。
[71] 康德式(Kantian)的表达主要指康德所提出的“二律背反”——凭借经验无法证实的问题,此时思维与实际就可能产生矛盾。此处所表达的应该是康德式的表达方式。
[72] 指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一书。
[73] 福克兰群岛(Falklands)为英国、阿根廷争议领土,位于阿根廷南端以东南大西洋水域,西距阿根廷500多公里,又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西班牙语:Islas Malvinas)。
[74] 巴别塔又译巴贝塔、巴比伦塔、通天塔,《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当时人类兴建通往天堂的高塔,上帝为阻止人类的计划而使人类使用不同语言,使之无法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散居各地。此处两个短语形容当今世界无边无际以及千变万化的状况。
[75] 亦即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1934~2000),意大利政治家,社会党*,首任社会党政府总理,西方“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他执政3年8个月,领导了战后意大利时间跨度仅次于贝卢斯科尼的政府,著有《从圣地亚哥到布拉格的社会主义》等。
[76] 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1919~2013),意大利著名政治家,三十余岁就担当政府部长,出任意大利政府各个重要职位。1972年起开始担任总理,此后20年间六度出任总理。
[77] 杰弗里·豪(Richard Edward Geoffrey Howe,1926~ ),英国资深保守党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内阁成员中任期最长久者,曾先后出任财政大臣、外交大臣、下议院议长及副首相;亦是中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关键人物之一;1992年获封为终身贵族。
[78] 托马索·帕多阿-斯基奥帕(Tommaso Padoa-Schioppa,1926~2010),意大利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欧元区奠基人之一。
[79]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又译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成员之一,他以坚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其“价格信号”理论被视为经济学领域里的重大突破;1974年与其理论对手贡纳尔·默达尔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80] 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1926~2010),英国经济学家、应用经济学教授,经济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持凯恩斯主义观点,曾预测20世纪70年代希思保守党政府的繁荣“将以泪雨告终”。
[81] 欧洲货币机构(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缩写是EMI)是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
[82] 亚历山大·拉姆法鲁西(Alexandre Lamfalussy,1929~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欧洲中央银行创建者、前行长,欧盟理事会于2000年7月建立欧洲证券市场规范专家委员会,由他出任主席,该委员会又叫“亚历山大·拉姆法鲁西委员会”,其所提出的四级立法程序成为著名的“拉姆法鲁西程序”。
[83] 奥德修斯(Odysseus,罗马神话易名为“尤利西斯”)是希腊《荷马史诗》中第二部《奥德赛》中的主角,是希腊西部伊塔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之一,后在海上漂泊十年,最终回归故乡并且与妻子团聚,其间历尽劫难,拒绝女妖、女神们的各种诱惑。他矢志不渝,成为后世西方文本所歌颂的对象。
[84] 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Conor Cruise O'Brien,1917~2008),爱尔兰政治家、作家、历史学家,其关于英国在爱尔兰及北爱尔兰事务中的作用的激进观点在20世纪中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许多对国际事务的观点都是非主流、反传统性的。
[85] 车臣人(Chechens)今为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属欧罗巴人种高加索语系达格斯坦语族,约75万人(1979),他们集中于海拔4493米的北高加索地区——处于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弹丸之地,但却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且石油资源丰富,也是自中亚向欧洲输送石油的必经地。中世纪该地区大致属阿兰人所建国家,13世纪蒙古人侵入后车臣人逐步移居他处,19世纪该地区被沙俄兼并,1936年改为自治共和国,1944年车臣人被强迁至西伯利亚,此举造就了仇恨;苏联解体后发生两次战争,但均被平定。库尔德人(Kurds)是中东的游牧民族,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居于西南亚库尔德斯坦地区(包括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境内),多信奉伊斯兰教,今总人口约为3000万人,也是土耳其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中东仅次于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民族。马其顿人(Macedonians)是巴尔干半岛南部斯拉夫民族之一,属欧罗巴人种巴尔干类型,约有134万人(1981),占今马其顿全国人口的64.18%,多信奉东正教,部分为穆斯林。
[86] 菲利普·塞甘(Philippe Séguin,1943~2010),法国政治家,曾担任国民议会议长、法兰西审计法院院长。菲利普·德·维里耶(Philippe de Villiers,1949~ ),法国政治家、右翼政党“法国运动”(MPF)党魁,曾在希拉克任内担任通信部部长;主张欧洲怀疑主义、保守主义、强力执法、反移民,与让-马里·勒庞一样属于反对移民的极右派势力,曾与萨科齐竞选法国总统。
[87] 伯纳德·康诺利(Bernard Connolly,1950~ ),著名经济学家,对欧元区持有悲观主义经济学观点,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受教于牛津大学,著有《欧洲腐烂之核:肮脏的欧洲货币之战》(The Rotten Heart of Europe: The Dirty War for Europe's Money,1995)。
[88] 赫尔穆特·施莱辛格(Helmut Schlesinger,1924~ ),经济学家、德国中央银行行长(1991~1993),曾预言欧洲货币体系内面临货币压力,从而引发紧张;为此他提出大幅度提高利率的计划。
[89] 此处指的是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
[90] 魏格尔(Theodor Waigel,1939~ ),德国政治家、前财政部部长。
[91] 蒂特迈尔(Hans Tietmeyer,1931~ ),经济学家、政治家、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强调保持德国央行的独立性,曾促使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实行货币统一,此外他还参与撰写《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欧元相关准则。
[92] 菲利普·迈斯塔特(Philippe Maystadt,1948~ ),比利时政治家、经济学家,曾担任政府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和副首相,也曾担任欧洲投资银行(简称EIB,亦即European Investment Bank)总裁。
[93] 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1859~1941),1888~1918年在位,普鲁士国王、霍亨索伦家族首领、德意志第二帝国末代皇帝,是腓特烈三世和英国维多利亚长公主的长子,他生性冲动鲁莽,因此未能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理性的方案。
[94]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
[95] 维希政府(Régime de Vichy,亦称“维希政权”)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属下的傀儡政府:1940年6月,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投降,7月,政府迁至法国中部的维希;1944年盟军解放法国,维希政权宣告覆灭。
[96] 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1930~ ),法国政治家、社会党第一*(1993~1994)及政府总理 (1988~1991)。爱德华·巴拉迪尔(Édouard Balladur,1929~ ),法国政治家、政府总理(1993~1995),出生于土耳其伊兹密尔一亚美尼亚家庭,1935年移居马赛,2006年他宣布不会参选连任国会议员。
[97] 阿兰·马里·朱佩(Alain Marie Juppé,1945~ ),法国政治家,曾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作为1995年结束法国社会党14年执政的希拉克总统之盟友,他被任命为总理,两年后下台。
[98]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the Fifth Republic)是成立于1958年而延续至今的共和国政府。
[99] 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1837~1891),法国历史人物,他毕业于圣西尔军官学校,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役、意大利战役、越南战争和普法战争,担任过荣誉军团指挥,1884年晋升准将,在军中威望很高,而所谓“布朗热事件”或“布朗热运动”(Boulanger Incident,1887~1891)时值第三共和国政治危机,是以他为首的民族沙文主义运动,目的在于推翻共和国、效仿拿破仑、建立独裁政权,不过他最终(缺席)被最高法院终身监禁,不久自*。运动最终瓦解,1879年的法国共和政体得以巩固。
[100] 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是由中欧四国组成的跨国组织。1991年年初,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布达佩斯以北40多公里多瑙河畔的维谢格拉德举行会议,目的是加强彼此间合作,1992年12月捷克和斯洛伐克独立后,该集团成员国由三个变为四个。
[101] 布格河(the Bug),波兰最大河维斯杜拉河(Vistula,又名维斯瓦河)的支流,又名“西布格河”,源出乌克兰西南部高地,由东南向西北流,为乌克兰、白俄罗斯与波兰的界河,全长831公里,流域面积7.3万平方公里,大部在波兰境内,有运河西通第聂伯河等河。
[102] 维尔纽斯(Vilnius),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立陶宛的首都。
[103]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生于立陶宛的波兰著名的诗人、翻译家、作家、外交官、社会主义时期持不同政见者,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包括《被禁锢的头脑》《伊斯河谷》《个人的义务》《务尔罗的土地》等。
[104]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捷克裔小说家,生于捷克布尔诺市,196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获巨大成功;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主要作品有《小说的艺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
[105] 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1964~ ),曾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和编辑部成员、伦敦《旁观者》杂志国外编辑、《经济学人》杂志驻华沙记者,著有《东方与西方之间:跨越欧洲的中间地带》。
[106] 米克洛什·豪劳斯蒂(Miklós Haraszti,1945~ ),生于耶路撒冷,新闻记者、大学教授、人权倡导者,其力作《工人国家中的工人》表明在工人中存在着极强的“阶级认同”和“冲突意识”。
[107] 马札尔人(Magyars,又译马札儿人),为匈牙利主要民族(2001年人口约为1000万人),属于乌拉尔语系,曾生活于中亚一带,因此现代匈牙利人带有突厥血统。另一部分居住于东欧、东南欧等地,少数在北美、巴西与澳洲。
[108] 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德国政治家、政治教育事业创始人,一战期间鼓吹建立一个统一的中欧(提出“中欧”一体化概念),以期在未来统一欧洲大陆。
[109] 维斯杜拉河(the Vistula,又译维斯瓦河)是波兰最长河流,全长1047公里,流域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占该国面积的2/3;它发源于贝兹基德山脉,流经克拉科夫、华沙等名城,在格但斯克注入波罗的海。孚日山脉(the Vosges)位于法国东北部、莱茵河左岸;南北走向,长约125公里,宽40~70公里。
[110] 约翰·波科克(J.G.A. Pocock,1924~ ),出生于英格兰的美国史学家、政治思想史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古代政制与封建法》《政治、语言与时间》《美德、商业与历史》等著作。
[111] 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位于亚欧大陆最东端的迭日涅夫角和美洲最西端的威尔士王子角之间,宽约85公里,深度在30~50米之间,它连接楚科奇海(北冰洋之部分)和白令海(太平洋之部分),其名字源自丹麦探险家维图斯·白令(1728年在俄国军队任职时穿过此海峡)。
[112] 赫勒斯滂(Hellespont)亦即赫勒斯滂海峡,也称恰纳卡莱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它连接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今属土耳其内海,为亚欧分界线之一,常与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统称为土耳其海峡。利安德(Leander)出自古希腊神话,他每晚渡过上述海峡与阿佛洛狄忒(亦即维纳斯)的女祭司海洛幽会,其间海洛点燃火炬为他指路;在一风雨交加的夜晚火炬熄灭,利安德因迷路而淹死,海洛在悲恸中跳海自溺。拜伦勋爵亦即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品包括《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等,曾亲赴希腊,投身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之一。
[113] 波斯尼亚(Bosnia)位于东南欧,或为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简称。
[114]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史学名著《历史》的作者,西方历史学的奠基人,自古罗马时代起开始被尊为“历史之父”。
[115] “欧罗巴”一词源自古希腊神话,众神之主宙斯(Zeus)到处拈花惹草,迷上腓尼基国公主欧罗巴,宙斯变成大白牛将公主劫持至克里特岛,生下儿子弥诺斯和拉达曼迪斯。
[116] 腓尼基(Phoenicia)是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古代一地区,其范围接近于今日的黎巴嫩;腓尼基人属于闪米特种族的一支,为犹太人近邻,其全盛期曾控制西地中海贸易;腓尼基字母是欧洲字母之源。克里特(Crete)岛位于地中海北部、爱琴海最南面,是希腊第一大岛,希腊神话发源地之一,也是欧洲文明的一个摇篮。
[117] 摩尔多瓦(Moldova)是东南欧北部内陆国家,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接壤;历史上与罗马尼亚人同宗同文,皆为达契亚人后裔,原为苏联加盟共和国,曾分别隶属于罗马尼亚和苏联,1991年独立。
[118] 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即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1729~1796),俄罗斯女皇(1762~1796年在位),与彼得大帝齐名,她政绩卓越,建立空前绝后的俄罗斯帝国,史称“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在19世纪的强势被归因于这位女皇,其后六位沙皇在治国政绩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119]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Alexander Vasilievich Suvorov,1730~1800),俄国军事家、统帅,俄罗斯军事学术奠基人之一,常胜将军之一,著有军事学名著《制胜的科学》。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1799~1837),著名文学家、诗人、小说家,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及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
[120] 乌拉尔山脉(Urals)北起北冰洋喀拉海的拜达拉茨湾,南至哈萨克草原,绵延2000多公里,介于东欧平原和西伯利亚平原之间;山脉自北至南分为5段,是欧亚分界线和重要通道。
[121] 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1955~ ),英国史学家、作家、评论家,欧洲史研究专家,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兼任许多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研究员,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
[122] 基思·米德尔马斯(Keith Middlemas),英国学者、当代欧洲研究专家,著有《绥靖战略》《工业社会的政治》等。
[123] 摩尔曼斯克(Murmansk) 位于科拉半岛东北,是俄罗斯最西北部摩尔曼斯克州首府、不冻港、北冰洋沿岸最大港市,距离挪威及芬兰不远,人口为31万多人(2009年),也是北极圈内最大城市,临巴伦支海的科拉湾。卡萨布兰卡(Casablaca)是摩洛哥第一大城市、最大港口,濒临大西洋,东北距首都拉巴特88公里。
[124] 马格里布(Maghreb)是非洲西北部一地区,阿拉伯语意为“日落之地”,古代原指阿特拉斯山脉至地中海海岸间的地区,后逐渐成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的代称。19世纪末,它几乎全部成为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殖民地,当今除休达和梅利利亚两地属于西班牙外,其他地区均已并入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
[125] 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1943~ ),法国政论家,曾被评为世界百位最顶尖思想家之一,1990年创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曾参与起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作品包括《21世纪词典》、科幻小说《大爆炸》以及《国家的*》,他认为“过度的公债造成一种使公共和个人行动都会瘫痪的政治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