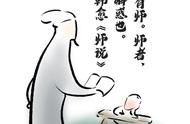槐花初初开放应该是在人间四月天的,然而,它的花期很长,谢了又开,开了又谢,直到六七月,依然能闻到清甜的槐花香,所以,白居易写到“蝉发一声时,槐花带两支”。高高的槐树上,一串串,一蓬蓬,一簇簇白得玲珑剔透的槐花藏在翠翠的树荫间,含苞待放时,一小朵一小朵象半个月牙儿,而怒放时,又象穿着蓬蓬婚纱的娇媚的新娘,远远的,在田间巷陌的那一端就能闻到淡淡的清香袭来。
槐花多在乡里人家的池塘边,河埂旁,不华丽,不张扬,似邻家女孩样朴实,生养它的老槐树在皖人的心目中,是成人之美的红娘,落难的董永在老槐树下遇到了七仙女,哑木头开口说话,成就了一对恩爱夫妻。

小时候,跟着母亲去打槐花,用长长的竹竿绑上一个铁丝弯成的钩子,再挎上个大竹篮,母亲伸长了胳膊去钩,每落一串,我们都欢呼雀跃着去捡,直到竹篮成了满满的一篮白。回家来,母亲把槐花用开水烫过后,铺到阳光下去晒,这是要等到晒干后做冬季的菜的。还有的新鲜的花会放点五花肉,烩成一盆美味的槐花烧肉,肉里,汤汁里都是槐花的香。
我依然是喜欢冬季里的那道菜,干槐花蒸干大虾,感觉它们两个真的是绝配。晒后的槐花已经是干枯的深黄色,不再娇柔,不再妩媚,也不再明艳,洗尽青春的涩涩,却依然朴实纯净,温婉细腻,闪耀的是岁月沉淀后的光华,而大虾硬朗朗的,有些锋芒,有些倔强,与槐花正正好的互补,日子也就这样的缓缓的在相互磨合中延续着。自然,要加点葱,加点姜,加点蒜,加点盐,加点酱,加点醋,还要加点辣椒,这样的五味杂陈,弄点荤素油往里面一搅和,放点味精一调,原本平平淡淡的日子也就蒸出了别样的味道,谁能说这样的生活是单调而乏味的?谁又能说这样的菜式上不了大雅之堂?没有尝试过,怎能说,那不是别样的爱情的味道?
年轻时样貌清秀似槐花一样的母亲,个性却不似槐花,却似大虾,硬朗朗的,于是,与同样硬朗朗的大虾性格一样的父亲可谓是针尖对上了麦芒,二老的半生都生活在刺碰刺,硬碰硬里。 婚姻里总得有一个人做槐花,生活也不是战场,于是,步入婚姻殿堂的自己选择了做槐花,收敛起骄傲与锋芒,在平实的生活里,做一个平凡的妇人。
每年的春季,年逾六旬的母亲仍旧会独自扛着竹竿去打槐花,只是身后再没有孩子们来陪伴着她,而她总是把这些花全部烫好,晾晒干净,用塑料袋平均分成三份,三个子女,每个孩子家送一份过去,孩子们的生活都好了,对这些东西早已不象小时候那样稀罕,可她依然年年送。只有我,因为爱吃这道菜,吃完了又管她要,于是,我的冰箱里,长年累月的放着一袋袋的干槐花,从春季一直吃到来年槐花又开。
年又来了,在异乡又做起这道菜,年的味道,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