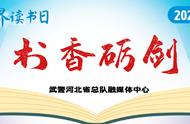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向北看,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庄严肃穆,照耀着国家的未来;向南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底座伫立在广场中心,托举着民族解放的历史。每天,数以万计的行人、车辆在它们的注视下川流而过。
这两件作品,都凝聚了林徽因的心血。
现在的文艺青年和影视作品热衷于把林徽因演绎成柔弱的美女、多情的才女,描述为“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嫁得好、干得好的‘五好女性’”,并津津乐道她的感情经历,好像她不曾经历国难家愁。
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她生于1904年,卒于1955年。短短51年间,祖国大地上外敌入侵、百姓流离、政局动乱,而她,始终与国人家人同甘苦、共患难。在战火中,她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潜心治学;在病痛中,她仍殚精竭虑培养人才;在任何危局中,她都坚守祖国。
这才是真正的林徽因:一位建筑师,一位坚忍忠诚的知识分子。
2014年是林徽因诞辰110周年。我们在她女儿、学生、亲友的讲述中,探寻林徽因真实的精神世界。
1937年
1937年夏天,山西五台山区荒凉、崎岖的路上,出现了几驾步履迟缓、颠簸不已的“骡轿”,上面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妻,33岁的林徽因和36岁的梁思成,还有他们的同事——“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的成员们。
这是林徽因第三次山西之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她曾在1924—1928年赴美学习美术和建筑学,24岁回国后与梁思成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27岁加入营造学社。他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时发现:框架式木结构是中国古建筑的基本形式,于是下决心要找到一处唐代的木结构建筑。
然而,经过上千年的朝代更迭与战火,当时学者们了解的唐建筑实物只有砖塔结构,没有木结构。日本建筑学界甚至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木结构建筑。这深深刺激了这对年轻夫妇。
他们从敦煌壁画中得到启示:唐代佛光寺或存在于五台山地区,于是便兴致勃勃地出发了。一路上,林徽因带着少女般的欢愉,心情激动,不时与丈夫热烈讨论。

尽管过去5年的野外考察不乏这样的经历——千辛万苦地跑了几百里路,结果只见到一片废墟,或是明清以后仿建的赝品,但这一次,他们依然充满期待。
走了两天崎岖山路和陡峻山崖后,他们在傍晚时分到达一个名叫豆村的小山村。夕阳西下,他们惊喜地发现,前方一处殿宇沐浴着晚霞的余辉,气度恢弘,屹立于荒凉空寂的苍山中。佛光寺!它就这样神奇地出现在林徽因、梁思成的眼前。
一行人的兴奋难以言表。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生前回忆说:“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与臭虫堆中摸索测量。”林徽因凭着一双远视眼,发现大梁下有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为了求得题字的全文,他们在梁下支起高架,清洗梁底尘垢,看出了一行‘功德主故左军中尉王’的字样,字体均是唐风。字的意思表明:修建大殿的施主是一位宦官,官衔是左军中尉(由宦官出任,执掌唐代的中央禁军),姓王。”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张德沛回忆说,林徽因在佛光寺测绘时,与当地老百姓和教书先生相处极为融洽,“他们主动帮她拉皮尺、拓碑文”。面对大殿角落中“女弟子宁公遇”庄严美丽的雕像,林徽因更生出一种崇敬的心情。“母亲说,她恨不得也为自己雕一尊像,让自己陪着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盘腿再坐上一千年!”梁从诫说。

测绘结束后,林徽因、梁思成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然而就在此时,数百里外的北平,卢沟桥上响起了枪声。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军队向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蓄谋已久的挑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和民族到了救亡图存的时刻,营造学社的古建筑考察不得不戛然而止,这次山西之行成为林徽因夫妇考察事业的最后一个高峰。
“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
匆匆赶回北平的梁氏夫妇,面对华北当局战和不定的暧昧态度,于7月16日和北平高校的26位教授、文化名人,联名致电正在庐山参加座谈会的军政要员。他们一致主张守土抗战,“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
当时,他们的女儿梁再冰正在北戴河同姑姑们一起度假,林徽因给她写了一封信:“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在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日军分三路进城。街头冷落了,胡同寂静了,政府部门开始撤离、疏散。林徽因和梁思成为防不测,连日清点、整理营造学社的研究资料。后来,为防止这些珍贵的资料落入日本人之手,他们将其存进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两人一面联系可结伴流亡的清华大学教授,一面尽快收拾行李。他们被迫离开北平,但坚信自己必将回来。

当时,匆忙逃难的林徽因不会想到,1937年就这样成为一个分水岭,将她的人生截然分开。1937年之前的林徽因,是传说中的林徽因:出身名门、事业顺利、婚姻美满、儿女双全,可谓幸福生活的范本。1937年之后的林徽因,人生是不断的失去:疾病夺走了她的健康,战争让她流离失所、事业中断、失去至亲。但1937年之后的林徽因,才是真正的林徽因。
林徽因、梁思成和他们的朋友决定南下昆明,这段路程格外艰难。如今,许多当年的“南渡者”去世了,梁再冰已是一位85岁的老人。作为唯一健在的亲历者,她选择母亲生日当天——2014年6月10日,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了一家人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
林徽因、梁思成带着5岁的梁从诫和林徽因的母亲何氏,赶到天津与8岁的梁再冰会合。此后两人扶老携幼,先从天津坐海轮到青岛,再坐火车经济南、徐州、郑州到汉口,靠摆渡船过长江到武昌,又坐火车去长沙。林徽因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到长沙后不久,日本敌机的轰炸就来了。“有一次,事先没有警报,日本轰炸机就到了头顶上。爹爹以为是中国飞机,直到炮弹爆炸才急忙跑回房间把我抱起来。妈妈也立即抱起小弟,搀扶着外婆往楼下跑。当时整个楼房震动,到处都是碎玻璃。当我们跑到楼梯拐角时,又一批炸弹落下,抱着孩子的妈妈在刹那间被震到了院子当中。后来我们跑到街上,听到飞机再次俯冲,那时毫无战争经验,竟然不知道卧倒,全家人都站在那里,幸好这批炸弹没有爆炸。”
长沙不能久留,从1937年11月下旬开始,一家人再次踏上旅程,取道贵阳去昆明,这是一段最艰苦的路。“湘黔一带都是高山峻岭,我们乘坐破旧的长途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妈妈、外婆、弟弟和我都晕车。”此时,梁再冰印象最深的是父母在困难的旅行中配合默契、应付自如。“譬如打行李,两人合作,动作敏捷熟练,很快就能把一大包被褥枕头打成一个结实的铺盖卷,用油布包好防潮;在外吃饭准备好一小铁盒的酒精棉,将碗筷消毒后再吃。这显然是他们过去到野外考察古建筑时‘练’出来的本事。”
走到湖南和贵州交界处的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时,林徽因病倒了。感冒多日的她,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休息并发了肺炎,高烧至40度。“那时还没有抗生素类药物,肺炎是很难治的病症。”幸好同车人中有一位女医生,为林徽因开了中药方,林徽因服用后缓慢退烧,两周后烧才退尽。经过这场大病,林徽因的身体虚弱了许多,也为她后半生缠绵病榻埋下了祸根。
1938年初,一家人终于到达昆明。“父亲在昆明市郊龙头村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夯土墙盖了三间小屋。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虽然他们只住了半年。”梁从诫生前说。有了立锥之地,林徽因显得愉悦起来,在写给美国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说:“这儿的阳光总是异常的明媚,天空昼夜湛蓝,云朵自在惬意地飘动。”据梁从诫回忆:“昆明这高原春城绮丽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记得她曾写过几首诗来吟咏那‘荒唐的好风景’,一首题为《三月昆明》,可惜诗稿已经找不到了。还有两首:《茶铺》和《小楼》。”在昆明的3年,整个家庭得到短暂休整,梁思成也有机会在此前从未到过的四川和西康(民国时期旧省,包括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展开古建筑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