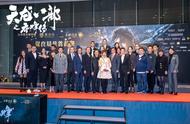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键点,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具有标本意义。其实,敦煌的环境是艰苦的,敦煌的人口是较少的,西汉时期敦煌的人口是38335人,东汉时期敦煌的人口是29170人,皆不及与其毗邻的酒泉,西汉时期酒泉的人口是76726人,东汉时期酒泉的人口数史书漏载,只有户数12706户,人口数当为五万多。在古代世界,人就是生产力,敦煌这个人口较少的西北边缘之郡,绝不会是最富庶的地方,但敦煌却造就出辉煌灿烂的文化,十分值得我们深思。

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无垠的戈壁与绿洲交相辉映,大山之外是大漠,点点绿洲连接起来的道路,就是东西交往的孔道。敦煌就矗立在东西要道的中心点上,再往前就是西域,一片更为神奇的土地,也是汉帝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匈奴对西域的经营,至少要早于汉朝一百年,匈奴骑兵纵横西域诸国,控制着东西交通。张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逃脱匈奴的羁押前往月氏,而在回来的路上,还是被匈奴擒获,可见广大的西域、河西诸地,都在匈奴的强力控制之下。
汉朝要想走向世界,必须开发西域,把西域从匈奴的手中夺回,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作为汉朝经营西域的窗口的敦煌,重要性无与伦比,也的确赋予了敦煌太守这样的职权,故敦煌虽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经营西域的前线。李广利第一次伐大宛,失败而归,汉武帝令其屯田敦煌,再谋西伐,在敦煌备战的时间里,敦煌的地位变的更加重要,此时的敦煌既是前线又是后方。总之,敦煌不是后人眼中的边远小城,而是窗口、前线,是可以建功立业的地方。
中古时代,敦煌名人辈出,位至三公亦是常事,即使后来中原发生了战乱,乃至改朝换代,而河西晏然,敦煌稳固,这群扎根西垂的人们,逐渐形成世代之家族。敦煌大族虽多以军功起家,但十分注重儒学修习,经学传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儒家世族。其实,敦煌大族是开风气之先的一群人,他们身处各种异质文化之中,他们最先接触到从西传来的各种异质文化,他们最先完成了异质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升华,当这些拥有异质文化的人们进入中原之时,他们又将早已融合在体内的蛮夷戎狄风气引入中原,而这些所谓的异质文化、蛮夷戎狄之风,恰恰是新鲜空气,恰恰是打破平静湖面的层层涟漪。
敦煌是幸运的,自西汉设郡以来,中原虽然经历了三国纷争,两晋聚合,南北动乱,但是敦煌从未受到大范围的破坏,反而由于远离中原而成为世外桃源,避难而来的人们聚居在河西之地,独享清平,而后是隋唐时代,对于西北的重视与开发,再次提上最高议程,作为西北门户的敦煌之地繁荣依然。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河陇陷于吐蕃,敦煌的汉文化传统被截断。从汉武帝到唐玄宗,一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传承,连接起来的是中华文明最繁盛的汉唐时代,汉唐文明的精华聚汇于此,汉唐文明的根深深扎入敦煌大地,才会造就出无比灿烂的敦煌文化,展现出来的就是石窟艺术的巧夺天工,文化文明的博大精深,还有藏经洞的神秘神奇。文化的繁荣使得敦煌有了底蕴、有了自信、有了希望,如果没有这群有文化的敦煌人的坚守,如果没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延续,敦煌的辉煌灿烂如何创造,没有文化自信的时代,是不可能造就出如此兼容并蓄、辉煌灿烂的文明的。
但是,敦煌绝不是丝绸之路上的唯一明珠,丝绸之路是一串明珠的组合,如武威、张掖、酒泉、瓜州、龟兹、高昌、于阗、天水、庆阳、平凉等,皆是明珠。石窟亦是如此,世上不是只有一个莫高窟,还有榆林窟、西千佛洞、马蹄寺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克孜尔石窟等。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诸多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没有保留下来,而敦煌由于机缘巧合,为全人类保存下如此精美绝伦的瑰宝,故敦煌无疑是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但也不是唯一。
敦煌学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交叉学科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六七万件珍贵文献文物,有写卷、绢画、拓本、供养器等,沧海遗珠,无价之宝。敦煌文献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记载了很多历史典籍没有记载或者简略记载的历史事件,是我们探寻历史真相的直接证据。敦煌归义军是一个被史*载极其简略的藩镇,而敦煌文献的发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藩镇运行的诸多材料,一个可供研究的个案。
安史乱后,敦煌之地先是被吐蕃占据,而后是归义军,无论是张氏归义军,还是曹氏归义军,此时此后的敦煌,皆是多民族聚居的家园,甚至曹氏归义军家族本身就是粟特人,其间敦煌又受到回鹘与于阗的强烈影响,再后来是西夏对敦煌的统治时期,诸民族的文化、文献、文物都遗留在了敦煌,故敦煌出土了大量的吐蕃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等文献文物,是研究藏学、粟特学、于阗学、回鹘学、西夏学等学问的重要资料来源。
敦煌之外,丝绸之路沿线亦出土了大量汉文和少数民族文献,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吐鲁番文书、悬泉汉简、黑水城文书、库车文书等,这些文书、简牍与敦煌文献互为补充、互为鉴证,共同描绘出先民们开发西北、开拓边疆的壮丽画卷。吐鲁番地区的开发本身就是从敦煌开始的,敦煌人多迁徙至吐鲁番屯田,故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敦煌文献是紧密相联的。悬泉汉简主要是汉晋时代敦煌郡悬泉置的驿站文书,是丝路畅通、中西交流的档案见证。黑水城文书主要是西夏、元时期的写本和印本,是研究此时期丝路文化交流的宝库。库车文书是库木吐喇石窟附近佛塔废墟中挖出的古代梵语、婆罗谜文写本,有印度古代医方选集、骰子占卜文书等,反映的亦是东西文明之间的交流盛况。
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是全世界石窟艺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窟艺术最初的风格,必然源自印度、贵霜、希腊,古代犍陀罗地区是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随着佛教的东向传播,石窟艺术渐渐有了西域风格、凉州模式,再后来就是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中原风格,与佛教艺术风格东进形成对比的是西向回传,而诸种风格汇聚的地方,就是敦煌。
敦煌学本身就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等性质。欧美诸国的汉学家,无论是从事语言文献研究的,还是从事绘画艺术研究的,多与敦煌学有交叉,他们对敦煌学的开拓有贡献,敦煌学对他们认知东方亦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敦煌学是国际汉学研究中的“显学”“绝学”。
讲好敦煌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国学大师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诚然,敦煌的文化价值是突出的,敦煌的标本意义是鲜明的,借助敦煌文化、敦煌艺术、敦煌精神传播中国声音,用文化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争夺话语权的有效举措。
敦煌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家园,各民族在敦煌长期和平共处、友好往来,共同塑造了丰富多彩、绚烂多姿的文化。粟特人、吐蕃人、于阗人、回鹘人、西夏人的形象,至今还伫立在壁画之中。岁月变迁,时光流转,虔诚的吐蕃王子,繁忙的粟特商人,美艳的回鹘公主,乃至卑微的侍女,耕作的农夫,嬉闹的儿童,转瞬千年,美丽依旧。
敦煌是诸宗教和平共处的地方,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都曾在这里流行,敦煌藏经洞中保存有汉文景教文书《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景教志安乐经》,还保存有汉字摩尼教经典,即《下部赞》《摩尼光佛法仪略》和《摩尼教残经》,在一个佛教建筑中,在一个佛经为主的藏经洞中,竟然会保存有景教、摩尼教的经典,这种并行不悖,所反映的不正是敦煌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吗?
中国文化自古就认为世界应该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和而不同、百花齐放,正是这种推己及人、兼收并蓄的优秀民族品格,中华文明才能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继承和弘扬兼收并蓄的敦煌文化精髓,既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和谐包容,才是处理文明间冲突的根本出路,只有这样,古老的丝绸之路才会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才能真正造福各国人民。
( 刘全波 作者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