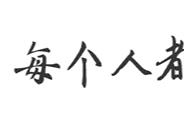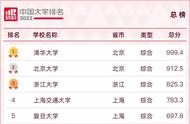1960年4月3日,余华出生于浙江杭州。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名副其实的“双职工”。时至今日,双职工都是人人艳羡的家庭。余华父亲正儿八经只读过六年书,三年小学,三年大学,中间课程都是在部队当卫生员时自学的。毕业之后,学校把他安排到浙江省防疫站,但他拒绝分配,跑回小城嘉兴,接着从嘉兴跑回更小的县城海盐。
海盐是个“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偏僻小县。父母上班后,就把余华和他的哥哥锁在家里,两人经常爬在窗台上看着外面的景色,一看就是一天。有时候父母整晚不回家,两人只好在家里玩,把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这种孤独的童年养成了余华爱好冥想和不合群的气质。上了幼儿院,他“不吵也不闹,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母亲每天早上送他上学,到了晚上接他,发现他还在早晨离开时坐的位置上,独自一人发呆,身边小朋友都在嬉戏打闹。
余华中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父亲便安排他进入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当了一名牙医。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尽心尽职的医生。余华在卫生所干了整整五年,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毫无波澜,一眼就可以望到生命的尽头。
如果余华服从命运的安排,就会和他的父亲一样,在小县城干一辈子医生,娶妻生子,过上体面安稳的生活,直到容颜老去。只可惜这种对好多人而言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对余华而言却如在酷刑中煎熬。王小波常说一句话,此人的美酒佳肴,便是他人的穿肠毒药,诚哉斯言。“一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自己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想不想改变和能不能改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有段时间,他发现总有一帮闲人在街上晃悠,穿着体面,意态风发,不像无业游民。上前一打听,原来都是县里文化馆的上班族。既然上班,为啥还能每天在街上晃悠呢。人家说,我们就是在上班啊。原来文化馆的人不用坐班,他们需要从办公室走出来,深入田间地头,深入人民大众,体验生活,观察生活,去采风,去了解,然后搞创作。这种“散漫,自由,任性”的工作方式让余华非常羡慕。
他觉得,自己也应该进文化馆上班。

然而文化馆不是那么好进的。文化馆顾名思义,你得先有“文化”,才能进去上班。文化馆的人要么会唱,要么会跳,要么会画,要么会写,都有一技之长。余华如果想调入文化馆,也得具备跟文化相关的一技之长。余华想了一下上述几项手艺,除了写字靠谱点,其他都不行,于是决定练习写作。其实写作是最容易入门的行当,只要认识几百个常用方块字就能干。相对而言,唱歌跳舞弹琴画画,都得名师指点,否则连门都进不了。所以现在满大街各种艺术班,鲜见开写作班的。
余华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夏天被蚊子咬,穿高筒雨靴,牛仔裤,手上绑着干毛巾,唯恐把稿纸弄湿,全身汗如雨下。跟所有文学青年一样,创作之路漫长而艰辛,并且看不到一丝光亮。余华后来回忆,“当年写作的时候多苦啊”。当然成功之后再说苦,就有点忆苦思甜的矫情了。其实认真说起来,他并不算苦,起码有体面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有幸福的家庭。要知道很多做着作家梦的文艺青年连一口饱饭都吃不到。
我在大学期间看过一位不知名作家的回忆,他在农村搞创作时,村里有个文友,对写作非常痴迷,可谓废寝忘食,虽是农民,却不干活,全是老婆干。老婆如果抱怨牢*,他轻则离家出走,重则一顿老拳。有一年过节,老婆给他五毛钱,让他去镇上买点酱油咸盐花椒面,回来包韭菜馅饺子。结果直到日落西山,他才晃悠回来,手中并没有酱油咸盐,却拿着鲁迅先生的散文集《野草》,边走边看。
老婆大哭一场,带着孩子走了,留下他继续做着作家梦。最后此人结局如何,书里没写,我不敢妄自揣测,但是大约应该可能差不多的确,会很惨。
其实余华的苦闷是所有小镇文艺青年共同的苦闷,这种苦闷在贾樟柯和顾长卫的电影中阐述的相当真实。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贾樟柯的《站台》和顾长卫的《立春》。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全民创作的年代,只要一个人认识几个字,就要搞创作,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那时候写作也是“显学”,会写的人头戴光环,对象好找,结婚还能少花钱。姑娘们找了会写的,脸上有光,出门有面。如果这位“作家”再会说点,穿着打扮注意一下,更是如虎添翼。
1983年,余华先后发表两篇短篇小说,顺利调入海盐县文化馆。从卫生院进入文化馆,是决定余华人生命运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一步。他从此可以把所有时间都用在读书写作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同事们还可以互相交流。
1986年,余华和朋友去杭州逛书店,买了一套《卡夫卡小说选》,读完之后,如闻惊雷,“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卡夫卡生前是个默默无闻的保险公司小职员,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他神情忧郁,寡言少语,内心波涛汹涌,用如椽巨笔构造了一个荒诞的世界。卡夫卡的作品影响深远,起码影响了现代两位作家,一个是余华,另一个便是王小波。王小波受卡夫卡《变形记》影响写了《绿毛水怪》,余华受《变形记》影响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
余华最早高仿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后来卡夫卡替代了川端康成。“卡夫卡从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当成命运的恩赐。(卡夫卡)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间成了一堆破烂”。
《十八岁出门远行》讲述了“我”第一次离家远行,途中遇到很多光怪离奇的事情,后来被抢劫,无法继续远行,只好恸哭而归,“风起了,很大,摇动树叶的声音宛若波涛汹涌,让我莫名恐惧,浑身冰冷”。《变形记》讲述一个小孩变成昆虫感知世界,《十八岁出门远行》讲述一个小孩独自远行感知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同年,余华在《收获》连续发表两篇小说,从此跻身先锋作家行列。我国纯文学有顶尖两本杂志,一为《十月》,一为《收获》,能不能在这两本杂志上发表作品,是一个文艺青年是否成为作家的标志。作家跟任何行业一样,都是有圈层的,只要进了圈子,就能得到圈外人梦寐以求的资源,从而踏上成功快车道。进不了圈子的人,成功就会非常艰难,王小波和海子终其一生没有进入圈子。王小波不无遗憾的说“听说有个圈,不知在哪里”,海子经常抱怨说“北京诗人圈非常难进”。所以他们在身前混的非常惨,都是身后封神。如果他们能够早早入圈,估计命运就会大为不同。
很快,余华便去北京鲁迅文学院文学讲习班学习,与莫言等人成为同班学习。读书期间,他广泛接触了包括但不限于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人的作品。这帮人的作品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余华和莫言后来都是走的这个路子,莫言靠这个路子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何谓“魔幻现实主义”?说实话我也不懂,查了很多资料,看到这么一句:魔幻现实主义是指在高度细节化的现实背景环境中嵌入奇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看了这句解释,我更加糊涂了。
不过真正让余华声名大噪的并非“魔幻现实主义”,而是暴力美学。余华先后写了《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等,被著名批评家张颐武批为“好像迷上了暴力”。余华自己也承认,“暴力源自人们内心的渴望,让我心醉神迷。现在的拳击运动,斗蟋蟀,都能让我们意识到暴力如何深入人心”。
暴力美学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流行,种种打斗、枪战、血腥等暴力场面被仪式化、英雄化,道德和社会的功能降低了,形式的美感被剥离出来,譬如吴宇森的《英雄本色》,还有北野武的《花火》。周润发和北野武都长着一张威而不猛的脸,看起来恭敬安详,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任何对他们尊严的冒犯必将带来灾难性的报复,必将被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撕成碎片。小马哥那句“永远不要用枪指着我的头”,至今都是英雄片的经典台词,听来让人荡气回肠,无有出其右者。
余华和吴宇森不同的只是,吴宇森的暴力美学是一场人性上的返祖,而余华却是暴力加美学,他将人性中暴力的一面,以美学的形式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也属于暴力美学范畴,所以才能在大众中广泛流行。如果他们的小说去掉暴力因素,我想根本没有几个人会看。

1991年,余华在《收获》杂志发表个人首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 。这本书是余华的精神自传,充满了温情与隐隐的疼痛,犹如一次必要的低泣和倾诉,一次楚楚动人的悲伤与哀悼,一次淋漓尽致的自我触摸。“呼喊”是本书的中心意象:谁在呼喊,向谁呼喊,呼喊什么,在何处呼喊,为何呼喊,有没有应答,谁来应答。这让人想起《圣经》中旷野中的呼号。
1992年,余华在《收获》发表长篇小说《活着》,该书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本书主题是:只要能够活着,可以承受任何苦难。它主要表现了底层小人物生存的坚韧性和顽强性。
1993年,余华从嘉兴市文联辞职,成为一名北漂,靠写作为生。记者问,(你的辞职)和王小波差不多?余华说,我跟王小波不一样。他开专栏,是自由撰稿人,我是职业作家,区别于作协的专业作家。职业作家靠写作谋生,就像在公司里工作一样,只不过时间自由,不用坐班而已。记者又问,靠写作能够维持生活吗?余华说,(别人不知道),我可以。作家不仅可以写小说,还可以接触影视,还可以翻译成多国文字,写一本15万字的书(挣来的钱)生活四五年时间不成问题。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有没有工作并不重要,几百块钱也不管啥用,重要的是,在写字台前不断地写。
有评论家认为,余华是中国的“半个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著名文学家,父亲也是医生,自己也干过公职,后来辞职专心搞创作。陀氏结过两次婚,余华也结过两次婚。陀氏被誉为“恶魔般的天才”,他的作品既阴郁,又热烈;既痛苦,又快乐;既绝望,又梦幻;时而大喊大叫,时而狂乱迷离;时而沮丧叹气,时而热情洋溢。对底层生存含泪的关切与对人性、信仰、存在等等终极的拷问极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鲁迅说他“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
余华作品中陀氏意味非常浓郁,但他达不到陀氏那种“巅峰感受”,与陀氏相比,他欠缺一种巨大的悲悯心,因此是“半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中国很多作家,连半个余华的高度都达不到。
莫言说:余华是个具有很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人。他清晰的思想脉络借助着有条不紊的逻辑转换词,曲折但是并不隐晦地表达出来。余华具有在小说中施放烟雾弹和在烟雾中捕捉亦鬼亦人的幻影的才能,而且是那么超卓。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
孟京辉说:余华是个伟大的作家。他有着“窄如手掌,宽若大地”的伟大作家的胸怀和情怀,有情感,还有一种特别深沉、特别广阔的东西在里面“活着” 。
阎连科说:我们所有人对余华都应该保持一种尊敬的态度。
这套余华文集,印刷精良,物美价廉,实为不可多得之佳品,喜欢余华作品的朋友赶紧下单入手一套吧,点击下方链接即可直接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