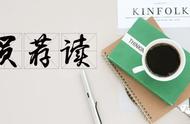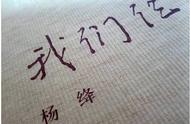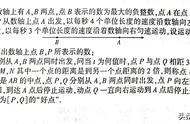《我们仨》--一部值得细读的好书知道杨绛,是因为钱钟书,看了《我们仨》,更知道了钱钟书的一家。
《我们仨》是一部回忆录,有书评这样说:“在温婉平实的文字中,蕴涵着深邃和厚重;所写的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及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股朗朗清气”。而我刚翻几页,就被里面飘浮动荡的文字抓住了心。之所以说它飘浮动荡,是因为记叙是从梦开始的,作者称自己老是做梦,文章开篇好几页都是对梦的描述,但显然,梦里的情景是透着很深的凉意的,不知怎么,总觉着一点哀伤,其时我便也跟着游离不定,误把梦境当作真。然而起初并不太明白回忆里讲什么,只是觉得这叙述挺让人揪心,于是便一页一页看了下去。故事的第三篇章《我一个人思念》,作者终于不再做梦了,故事开始从杨绛与钱钟书的学习、工作、生活多方面叙述,文章用词朴素得让人心痛,常常看到某处,很是替其一家担心,哪怕写到一点趣事,诸如杨不会切肉,而创造性地用剪刀把肉剪成一条一条这类,也只让人暗自苦笑,想他们的生活真是太过纯粹,生活被大量的读书、“探险”、“捡珍珠”所占据--他们在散步的途中不断去发现新鲜的事物,也旁听行人的说话,判断他们的身份,此举他们称之为“探险”,这样的“探险”为他们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一直陪伴着他们远赴国外,依旧乐此不疲。直至写到他们有了爱的结晶钱媛,回忆便成了牢不可分的《我们仨》。
钱媛是他们的女儿,也并不单纯是他们的女儿。杨绛、钱钟书、钱媛,是密不可分的三个人。虽然他们因为局势或环境所迫,曾有过几次分离,但是文中对这些分离的描写也是完完全全不着痕迹的牵挂,这使我很惊讶,因为爱情、亲情可以密切成这样。书中没有让人悲痛欲绝的词句,没有让人撕心裂肺的呼喊,然而处处洋溢着思念,对丈夫、对女儿的思念。我的惊讶还没有停止,在书的末尾,作者附上了一些家书及其女儿钱媛在病榻上写的《我们仨》片段,看着这些泛黄的歪歪扭扭的字,再翻翻书中夹带的照片,总觉得有什么牵扯着,有些不忍,又有些沉重,这两年已经好久没有读到这样的书了。
近来有关家庭的电视剧多如牛毛,但是没有一部让我有看了《我们仨》这本书而生出对家庭成员间那种牵肠挂肚又不着痕迹的纽带关系那样的亲情的由衷感慨,以至于把书看完的当儿我长时间的沉默不语,兀自发呆。我对某说:我多希望你看一看《我们仨》,但是某早已没了看书的习惯,要我讲给他听。我觉着这样的书是没法讲的,这样的情感只有亲自去读,才能细细地领略,故没有讲给他听,只惊叹说:人世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感,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亲情。而关于书中讲到钱钟书一家三口常常各自捧一本书学习,我甚为羡慕,对于某不喜看书这一点,颇为遗憾。
《我们仨》摘录: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锺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锺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粘在纱布上的末一丝脓连根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我们免得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我们日常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我们常挪用工作时间偷偷出去玩,因为周末女儿回家,而假日公园的游客多。颐和园后山的松堂,游人稀少,我们经常去走一走后山。那里的松树千姿百态,我们和一棵棵松树都认识了。 动物园也是我们喜爱的地方。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读书,钟书北来,我曾带他同游。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钟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十余年后重来,这几间房屋,连同松树和那一湾流水,都不知去向了。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