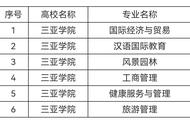人常说“覆水难收”,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不过写了错字还是可以用涂改液进行改正的,而很久以前那个用毛笔写字的、没有涂改液的年代,聪慧的古人也自有妙计。历史上之“错别字”康熙五十年间,康熙帝曾为承德避暑山庄亲手题写匾额,“避”字右边的“辛”下部明目张胆地多写了一横,工匠照此凿刻的匾额至今还挂在正宫内午门中门上方。
该匾额被今天的人誉为“天下第一错”,后世专家结合历史,猜测康熙帝是故意多写一横,为其想出各种不得不错的、符合身份地位的原因。
不过,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在《九成宫醴泉铭》中也写过“避”字,确如康熙帝一样多写一横。
该写法有使字形美观之说,也有其他不可得的原因。
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合葬陵墓明孝陵,其保护碑上“明孝陵”中的“明”字,和济南市“大明湖”中的“明”字,均被写成了“?”。
日、月为“明”,变成了目、月为“?”,私以为书写之人想说的是:缺少了太阳(日),是否还有朗朗乾坤?这些和现代书写不一样的所谓“错别字”,其背后的原因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书写界不成文的改错方法古人在进行书写活动之时,自有一套不成文的改错处理方法。
非正式书写场合,在错字右边点两个、三个或四个点,或在右侧写一小小的“卜”字,就表示该字不算入正文,不要了,很少直接涂抹;如果是漏字或掉字,在上一字的右下角处补上即可。
正式书写场合,一般会先打草稿后进行抄写,以保证卷面干净整洁。不过,据说书法大家王羲之、颜真卿之流,会直接在错别字上写字覆盖,或者大笔一挥直接划去,没办法,字好的人就是这么任性!雌黄=涂改液,哪里写错涂哪里其实,古人在错别字的修改上,也有一个终极秘密武器,那就是雌黄。《白蛇传》里的白娘子误喝了雄黄酒而显出真身,直接吓坏了许官人,雄黄酒就是由雄黄泡制而成。
在矿物界,雄黄还有个伴侣叫做雌黄,两者是共生矿物,还有个很浪漫的称号叫做“矿物鸳鸯”。雌黄在书写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术业有专攻”。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中记载:“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
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又易脱,粉涂之则字不没,吐数遍方能漫灭。
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
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
看来古人在改错字上没少下功夫:刮洗伤纸、贴纸易脱、用粉繁琐,只有雌黄,轻轻一涂就能书写,还经久不脱,在书写改错界无往而不胜。雌黄的其他功效除了用作书写涂改之外,雌黄还有更多其他用途。雌黄为色泽明亮的黄色,所以也被用作绘画颜料。比如闻名遐迩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使用的黄色颜料里就有雌黄的存在;在西方,雌黄也被碾碎当做颜料用于画画。虽然因其有毒性、与石墨及铜基颜料不能很好共存等原因,被镉黄和其他染料代替,但我国国画创作依然使用雌黄。
雌黄味辛,平,有毒,入肝经,可用作*虫、解毒、消肿等,在古医书上也有药用记载。
《神农本草经》中说雌黄“主恶创头秃痂疥,*毒虫虱,身痒,邪气诸毒。炼之,久服,轻身增年不老。生山谷。”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已经不再将雌黄列入中药材名录,在现代医疗活动中,已经很少见到雌黄的使用记录。雌黄衍生品:信口雌黄晋·孙盛的《晋阳秋》中记载:“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西晋人王衍喜欢老庄学说,每天都谈老庄玄理,但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也满不在乎,甚至不假思索随口更改,这就像雌黄随意涂改错误一样,大家就说他是“口中雌黄”。《颜氏家训》中也有“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的说法。雌黄可用作随意涂改,可你连天底下的书都没有看过来,就不要自作聪明随口乱讲了。这就是“信口雌黄”一词的由来。我们也不得不感慨,虽然“矿物鸳鸯”都有*虫解毒之作用,但相对于只能用作检测白娘子的雄黄而言,雌黄还是更胜一筹。毕竟,雌黄不仅是书写界改错的技术担当,更是言谈界衡量言论的一把尖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