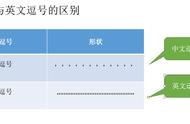钱维军土生土长的崇明人,老家港西镇八字桥河。1984年离岛就读于上海,后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本文经授权后发表,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编辑授权。
追忆父亲
这些天,我把大多数的时间花费在阅读著名作家叶振环老师的赠书《绿叶情怀》上面。那是一本选编自叶老师历年来撰写的散文力作,共计九十一篇的散文集。优中选优的美文佳作,使我爱不释手。其中一篇《父亲的“背影”》更是看得我泪眼朦胧,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叶老师写作此文的背景是在其父仙逝二十九周年的忌日那天,他怀着对父亲刻骨铭心的爱和深深的遗憾、歉意,追思、怀念着自己的父亲。虽然时光流逝,许许多多的陈年往事依然记得是那样的清晰,音容笑貌、一举一动仿佛仍然就在眼前发生的一样。
文中,叶老师这样写道:父爱如同一座山,我们儿女就是父亲这山上的一棵树,我们就在父亲这座山上成长,不断地被父爱滋润着,一代接着一代,在人世间繁衍!
叶老师的这段文字写得真好,感同身受,也正是我想要说的心里话。
我跟叶老师相比,出生于不同的年代,有十几年的时间跨度,成长的环境、经历也有所不同,但是对父亲的挚爱、依恋却是一样的深厚,也同样留有遗憾,心里有着抹不去的对父亲的愧疚、歉意。
叶老师生于1953年,1969年参军入伍,与其父长时间共同生活至少有十六年。而我和我的父亲长期共同生活却还不满三年,少得可怜。我的父亲于1955年参军入伍,1981年的年底转业回到崇明老家,戎马生涯二十六载,期间一年一次探亲,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有几次刚回到家,部队的一个召回加急电报就把父亲从我们身边拉走了。1984年高考之后,我离开了生养十八年多一点的家乡,开始了独立生活。1981年11月底父亲转业,1984年8月底我离家读书,屈指一算,三年差了整整三个月。这是我唯一与父亲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

在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未能探亲回来。等到一年之后,春节之前,父亲终于探亲回家了。那时,我虽然才期过把,却已脱步,而且说话也已经比较连贯了。第一次见到陌生的父亲,理所当然地拒人于千里之外,父亲想要抱我,我哭着、喊着不让,双手还不停地拍打、抓挠,父亲只得放手作罢。我的叔伯阿姐还骗我,说我的父亲不是我爸爸,是假家人(崇明方言,义指外人,特指陌生人),我竟然信以为真。到了吃夜饭当里,我对着父亲说:“假家人,乃尔好转去了。”父亲无奈地恳求道:“让吾吃子一顿夜饭再跑,好伐?”我点头同意了,但吃好了夜饭,我又旧事重提,“乃夜特,尔好转去了。”这个我小喊底闹出的笑话,至今仍是姊们淘里相聚时拿来开刷我的笑料,我面上陪着傻笑,心底却是五味杂陈。
1970年春,我公公(方言,即祖父)自己感觉身体不适,没有力气,迫于当时的经济压力,他一声不吭地硬挺着,只是在与老友闲聊时偶尔提及,家人却一无所知。拖到双抢大忙,改制田里临近要掰大米(玉米)时,公公一病不起了。拉到中心医院一检查,确诊是食道癌晚期,医生已经回头,并关照病人只有两个月的生存期,尽量做点好吃的东西满足患者,随即就让我公公回家静养。我清楚地记得,公公从医院回家后没多久,就出现了吞咽困难,其时喝水都要靠一根削制的芦头管子慢慢地缩(方言,即“吸”)一口,哪能还吃什么食物啊!再后来,公公连用芦头管子缩水都不行了,只能用棉条蘸湿了润润嘴唇。我父亲是奶末头儿子,也是最为孝顺的儿子,为了不让公公留有遗憾,大伯、二伯和两个姑娘催促着我母亲给父亲拍了一份加急电报,让父亲火速归家。但是,当时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结束不久,部队正处于备战阶段,探亲假一律不准。1970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十四),公公还是未能见到心爱的奶末头儿子,带着不舍永久离开了人世。直到第二年的寒里(即冬季),父亲才探亲回家。父亲挑着行李直奔前头屋门口,撂下行李就静立在公公的遗像前,豆大的泪珠从父亲的眼眶里滚落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坚强的父亲在默默地流泪。
1980年的暑假期间,父亲也正好探亲在家,我几乎一刻不离父亲的左右。那时,我的婆阿(方言,祖母)已经病重,卧床不起了。我婆阿住在二伯家里,因为其它的家人均要出工,服侍婆阿的一切事物实际上由我父亲一个人承包了下来,一天里在自己家和二伯家之间不停地经布。早上,我做火头军,专门在灶口头烧火,配合父亲煠针筒、橡皮条(当时均非一次性使用的),给医疗器械消毒。然后到二伯家里给婆阿吊盐水、打针,婆阿怕疼,以往每次打针、吊水都会拼命挣扎、乱动,极度的不予配合,需几个人同时揿手掐脚,但父亲总是像哄小孩一样轻言细语地安慰着婆阿,在不经意中已经把针头扎了进去,婆阿并不感觉到疼,以致于父亲假期结束归队后,婆阿再也不肯让大队里的赤脚医生打针、吊水。挂上盐水后,父亲把我留下来看管盐水,他回家盛菜盛饭,拿过来后再一调羹一调羹地喂(音同“衣”的阴上调)给婆阿吃,并不时给婆阿擦拭嘴角。饭后,父亲总要给婆阿揩面、梳头。趁空档,父亲还会给婆阿做全身按摩,修剪手指甲、脚趾甲。或者扎上几根金针,进针时提捏、捻转,定位准确,基本无痛;行针时,或提插、捻转,或搓针、弹针……手法多样;留针过程中,有时采用静留针,有时采用动留针;出针时,边捻边提,轻轻将针提出皮肤,婆阿还不知针灸已然结束。午饭时间,还是由父亲喂饭。午后二三点,挂好盐水,父亲把婆阿搀扶起来,勒床横头垫上一条棉被,让伊隑(音“开”的阴上调,斜靠)一歇,喂药后,就陪着婆阿聊家常。喂完晚饭后,父亲还要给婆阿喂药、揩面汏脚,一直坐到婆阿安然入睡了才回家。整个探亲假里,父亲天天重复着差不多同样的程序,并且独自承担婆阿所有的医药费用。父亲细致、耐心的程度,我的两个姑娘见了也自叹不如。暑假结束前,父亲的探亲假也期满,父亲不得不重返部队。一个多月后,1980年9月30日(农历八月廿二),我的婆阿也就告别了人世。父亲生前曾经对此表露过,他未能为公公、婆阿送终是他一生的遗憾之事。
父亲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后,我对父亲的了解开始深刻起来。
父亲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上下班还总是穿着一身军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规而八矩,好几年之后才开始穿便装;起床后,被子叠得方棱出角,像是仍有人检查内务似的;父亲叠衣服更绝,不但动作利索,折叠好的衣服似熨烫过的一样平整,跟没拆封的新衣服无异。我叠被子、叠衣服的本领就是得自于父亲的真传,不夸张地说,丝毫不逊色于父亲。

父亲的时间观念特别强,单位离家不近,他总是早早地骑着自行车出门,第一个到单位,亲自到锅炉房泡开水、打扫办公室的卫生,时间充裕的话连走廊、院子都会打扫一遍。其实,这些完全是由顶替父母的几名勤杂工负责的工作范围,父亲却越俎代庖了。身为一院之长如此,一段时间之后,各个科室的医护人员不好意思起来,纷纷自觉地早到,也开始打扫所在科室的卫生、自己泡开水,形成了良好的风气并且固化下来。父亲借机把多余出来的勤杂工进行了调整,除住院部仍保留几名勤杂工意外,选派年轻、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那些勤杂人员到医技院校学习深造,毕业后均充实到了医技岗位。事隔多年以后,那些人都成了业务的骨干,有的还成了领导。他们对我父亲当年的举动都念念不忘,甚至是感恩戴德的。父亲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影响了一批人,潜移默化之下成为自觉的行动,父亲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一次内部改革不说,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好几个人的命运,否则他们一辈子可能就是一名勤杂工。
父亲待人热情、和善,亲眷朋友到医院就医,父亲一概招待周全,全力以赴,力求花费少、疗效好。即使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遇到经济窘迫的困境时,也是倾力相助。因父亲数日没回家,母亲让我去医院探望父亲,那天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父亲正对着几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发火,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那几个外科医生噤若寒蝉,低着头站得毕端毕正,任凭父亲的训斥。原来是一位老农在平整土地时被大型拖拉机刮到误伤,创面很大而且骨折,几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怕担责任、相互推诿,要求患者去上一级医院诊治。那几个外科医生虽然一声不吭,实际上是有抵触情绪的,或许也是存心要跟父亲作对,就是不动手采取必要的救治措施。最后,还是由我父亲亲自操刀进行清创、消毒、缝合、上石膏固定、吊盐水。父亲始终认为,农民实属不易,能帮则帮,尽量减少额外的负担是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不但教育了几位外科医生,也使医者仁心的风范蔚然成风,而且那位患者时隔多年总要竖起大拇指夸赞我的父亲,说他有一颗菩萨心肠,逢年过节均要前来探望父亲。
1985年,父亲所在的医院选择新址重建,父亲大权在握,不少建筑材料的供应商、工程队的老板闻讯,就蠢蠢欲动起来。那些人为了避人耳目,当父亲下班回家时,尾随其后,悄悄跟到了家里,目的不言而喻。材料供应商、施工队老板以不低于15%的回扣做利益输送,想以此为引诱,轻松接到这一大项目。其时,我家也正有将平房翻建成楼房的打算,如果父亲有私心,与建造医院同步进行的话,让材料供应商随便拺几车,那是不在话下的事,也无需请专门的施工队,对人家来说可谓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父亲不会那样做,这不是他的性格,他有自己的处事原则。父亲对那些不速之客虽然一如既往地笑脸相迎、烟酒招待,他没有架子,认为来的都是客,但绝口不谈有关建筑工程上的事情,只是告知如果想参与工程项目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进行竞标,只要材料符合要求、工程质量有保证、价格有优势,完全可以取胜,至于其它的则免谈。父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个水都泼不进的人,他有一句名言:拿子不该拿的物事,总有一天会肚皮痛个。为了避嫌,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被人盯上纠缠,自家的房屋翻建只得搁置起来,一直拖到1988年才动工。
药品、医疗器械的采购供应当今存在着许多猫腻,这是公开的秘密,为世人所诟病。而有相当多的从事人员却是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放弃原则和良知,一切向钱看,被冲昏了头脑、迷失了方向。虽然一时得益,收获了不少不义之财,但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最终的结局大多非常悲催,有的被调离了岗位,有的被开除了公职,还有的锒铛入狱。其实,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医药市场的逐步放开,常有医药代表带着礼品、礼金等登门拜访,希冀打开一个口子,能列入采购名录,以推销药品,并许诺以优厚的佣金作诱惑。在某些人的眼里,这可是一个极好的生财之道,会紧紧抓住不放,但在我父亲那里却根本行不通,一概严词拒绝。父亲要求采购人员必须从正规的医药公司进货,若发现由非正常渠道进来的,必追究相应的责任。对于采购人员每次报上来的采购清单,父亲总是仔细审核、严格把关。

父亲是奶末头儿子,大姑娘比我父亲大十九岁,长姐如母,父亲与我大姑娘的感情极其深厚。1988年3月3日(农历正月十六)小大姑娘二岁的二姑娘因感冒发烧,到大队卫生室打了一针,因药物过敏当夜突然离世。亲眷朋友都愤愤不平,准备追究赤脚医生的责任,并扬言要打掉那人家里的灶头镬子。父亲当即出面进行了劝阻,极力反对这种野蛮的过激做法,主张必须以合法手段来维权,避免了一场惨剧的发生。而那时大姑娘已经瘫痪在床,表哥、表嫂去了二姑娘家参与丧事活动,被大姑娘察觉了,因悲伤过度,从此一蹶不振起来。父亲天天要去大姑娘家里,打针、喂药、劝解,但仅隔四十天,即1988年4月12日(农历二月廿六)大姑娘还是离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痛失了两个阿姐,这一阶段是父亲的艰难时期。二姑娘去世时,父亲除了悲愤、把那个肇事的赤脚医生骂了一通之外,我并没见父亲流泪。而在大姑娘去世时,父亲却是痛哭流涕,任人怎么劝都无济于事,大姑娘的丧事办完,父亲就睏倒了很久。
1992年11月份,我外婆因脑梗而摔倒,留下了全身瘫痪的后遗症。外婆病倒后,由七个男女负责轮流一天二十四小时服侍,姊们七个一周各自轮到一天。轮到我母亲的那天,父亲下班后就直接去外婆家里,夜里也留宿在外婆那里,协助母亲一起服侍。即使不是轮到我母亲服侍,只要没有紧要事,父亲在上班或下班时总要顺便到外婆那里弯一下,询问情况或提醒注意事项。外婆虽然口不能言,但脑子非常清楚,哪一天父亲有事未出现在外婆的面前,外婆会咿咿呀呀地叫嚷着,给她解释一番后她才会安静下来。
1993年6月27日(农历五月初八),我挚爱的外婆还是离开了人世间。半年后,外公开始轮流在三个儿子家里生活,每家为期一个月。时不时地,父亲会把外公接到家里住上十天半月。外公一来,父亲就会把整条烟供给外公,天天早上问外公想吃什么,下班时从镇上带回来。外公喜欢啄老和(玩长牌),父亲也会不定时地给个十块、八块的,供外公消遣。外公是个有故事的人,平时也喜欢说笑,我常见他们丈人、女婿胜似父子相视一笑和交谈甚欢的场景。外公在我家是绝对的太上皇,饭桌上,外公还未动筷其他人是不敢先吃的,有父母作表率,子孙辈耳濡目染,也成为了自觉的行动。直至2002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十五),外公无疾而亡,寿终正寝,在这九年里,父亲虽是作为女婿,但丝毫不输于儿子的孝顺。
父亲在妻舅、连襟淘里也是有口皆碑的,他们都极其信任父亲。无一例外,但凡有事,想到的第一相商人就是我的父亲。无论翻建房屋,还是小囡结婚、生子,事无巨细均要征求我父亲的意见,而父亲也总是不遗余力,事里事外问心,既要出力,又要出钱,从无二话。
我母亲姊们多,尽管读书很好,但那时重男轻女,读到二年级时因要带弟妹、做家务,不得已而辍学。我从三年级起就担负起给父亲写信的重任,直至父亲转业。记得给父亲写的第一封信,是毕工毕正的宋体字,虽然是寥寥数语,父亲收信后喜不自禁,还把信拿到战友之间传阅,这是父亲在回信时特意告知的。正是在父亲的鼓励下,信越写越顺手,父亲的每次回信总不忘把我写的原件附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写得好的句子、词语还会画上线条,加以重点评述。父亲在信中极少提及我们姊们三个读书学习的问题,但总会不嫌其烦、甚至是絮絮叨叨地说着为人处事的道理,教育我们要孝顺长辈、兄友弟恭、尊敬师长,所以直至现在即使遇到平辈,我们姊们三个都不会直呼其名,要么XX哥、XX姐,要么XX弟、XX妹。
我与父亲的书信联系在父亲转业后曾一度停顿了,但我于1984年离家后随即恢复,直至1996年家里安装了电话,改由电话联系,觉得方便多了。记得,在我入党前,单位组织科的人员去父亲所在医院外调政审,正好是我父亲负责接待的,随后父亲即写给我一封厚厚的信件,除了道贺之外,更多的则提醒和勉励,谆谆教诲犹记于心。
父亲写的字极具功力,用不同的书写工具写出的各种字体均有板有眼。父亲转业回崇明后,每年春节前夕,总是抽空动手写门对。不但字写得好,而且内容寓意深刻,不知情的外人见了,赞不绝口,以为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对联。父亲写给我的信件,单位同事在转交给我时总是满脸的惊羡,说信封上的字堪作字帖了。
似乎父亲从未过问过我学习上的事情,不问学习成绩,更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甚至在填写高考志愿时也没有指手画脚——悉听尊便,对我是放牧似的散养着。但在我读初二时,父亲利用驻防在深圳的便利机会,特意托人从香港买了一块进口的西铁城全自动手表,独独送给了我这个奶末头,我成了年级里唯一一个居手表的学生,而且又是名表。那时候,还有许多老师也不居手表,即使有,好一点的无非是上海牌之类的。年幼无知,虽然当时不懂父亲的用心,但因为有了手表的缘故,我对时间概念却把控得很好,再也无需由母亲每天喊起床、催促着上床睡觉。那块手表一直陪伴着我的成长,直至有了手机以后才不戴。
我参加了工作、结婚生子,忙单位里的工作、忙小家庭的经营,很少主动去关心父母,总以为今后有的是机会去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然而我是彻底的错了。
1997年年底,父亲退休了,闲赋在家,照理可以颐养天年了,而我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很难抽出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父亲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而让父母来沪住上一段时间,却像是把他们圈在了鸡棚里,一点也不习惯,呆上一个星期的话简直是要了他们的命一般。用母亲的话说,去趟上海就像生场毛病。几次之后再也不愿来上海,一则他们与我周围的邻居不熟悉,整天呆在房子里,实在是厌气相;二者语言不通,听不懂上海话,偶尔去菜场、超市,与人也无法交流沟通。因而一到了寒暑假,父母宁愿让我把女儿送回到乡下,由他们带养,消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几次想要趁父母身体状况尚好,还走得动,打算带着他们一起出去旅游。父亲总是借口说,全国各地他大多去过了,看过了也不过如此,推三阻四地不肯去。其实,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工作忙,一怕我影响工作,二怕我经济上额外的付出。为子女考虑得多,而不求子女的回报,这是父母亲的一贯做法。
2012年,我另买了一套房子,乔迁新居热宅时叫父母过来自己人一起庆贺一下,我许诺开车接送,哪怕是当天来回,但也就是不从,倒是担心我因为搬家而累着了,说要等我以后有空的时候再来也一样的。直至父亲离世,父亲也未能踏进我家的新居半步,还不知道门是朝哪个方向开的,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心里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