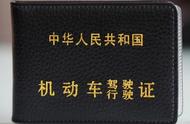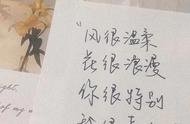中国早期聚落与水系密不可分,依托于密布的水网,发展出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城镇体系。水的网络促生发达的城镇网络,历史文化空间覆盖了城镇网络中的生产、生活、生态系统,形成了整体性的地方文脉与历史景观。
芜申运河是太湖和长江间的重要水道,顾名思义贯穿芜湖和上海。其前身是公元前506年开凿的胥河,也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自古以来,它便是太湖平原沟通长江中游和皖南水系的交通要道,支撑了苏皖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现代芜申运河与古胥河及周边运河系统间的关系。制图:赵忞,部分信息来源:论文《胥河流域历史文化空间变迁与发展研究》
春秋末期:胥河始建,本为“鸠苏运河”
胥河尚未开凿时,现南京石臼湖、固城湖、宣城南漪湖及其东部低洼地带曾是一个连成一片的大湖——古丹阳湖。在早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古丹阳湖周边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背山面水且平原肥沃的胥河流域,成为以采集渔猎为生活方式的原始聚落的择址首选,也为稻作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至春秋末期吴楚相争时,位于“吴头楚尾”的胥河流域掀起了第一波城建热潮。吴国依托自然环境优势,开凿了多条用于军事、运输、灌溉和防洪等的水道,沿河道形成的农业灌溉区,为吴国西拓军事重地提供后勤保障。
特别是吴王阖闾为了运输伐楚所用的粮食,命伍子胥开挖胥河,从都城姑苏(苏州)经太湖通到鸠兹(今芜湖),再随青弋江注入长江,提高了沿线区域的经济与军事地位。
自芜湖的青弋江逆流而上,不向宣城泾县的方向溯源,而是通过历史上的人工河道,穿过流经宣城和马鞍山当涂的水阳江,进入南京高淳的固城湖。
从固城湖继续向东,便是狭义的胥河(古称胥溪、胥溪河、淳溧运河),全长30.6公里,分为上中下河三段。上河西连固城湖,到达南京高淳与常州溧阳的交界时,与安徽段的梅溧河相遇,而后者称为中河。
中河流经溧阳的南渡镇时,与南河相会,于是进入了广义的胥河,芜申运河的南河段。南河流至宜兴,称南溪河;另一段中河从南溪河的北部流经,而后进入北溪河,与南溪河共同汇入三个“氿”(湖)后,进入太湖。
最初开凿胥河时,出太湖的终点是吴国首都姑苏(今苏州),另一端为鸠兹(今芜湖)。流域主要有鸠兹、濑渚邑(今高淳固城遗址)、陵平(溧阳周边,楚伐吴导致城址多次变迁) 3 个重要军事城建。
据清《康熙高淳县志·水利志》:“春秋时,吴筑固城为濑渚邑,因筑是圩附于城,为吴之沃土。”因此,筑圩附城的做法应是吴国在战争条件下城市建设的一大创新,既疏通了太湖-长江的水系,更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农业和渔业产品。
濑渚邑西围固城湖沿岸的相国圩保留至今。这种“圩”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步普及到整个江南地区,对农业发展、聚落形态以及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江南地区城乡聚落肌理形成的基础。
六朝至宋元:稳定通航,城镇体系初现
胥河初通时为季节性河流,不能全年通航,后经历代疏浚、唐代修筑五堰、宋代改筑东坝、下坝,胥河逐渐成为稳定的航运河道,流域聚落也随之变化。
六朝期间因政治中心的辐射,胥河流域郡县城镇自上而下,形成多层级多功能的整体格局。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使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城市经济功能逐渐提升。
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酝酿着州、郡、县等城市以外的新城镇形态,一方面包括军事性质的“镇”兴起和演变;另一方面包括“市”的空间局限被冲破,自发形成众多“草市”,进行“非正式”的市场活动。
市镇初现于六朝时期,到宋代大量增加。宋代这些新兴市镇主要分布在胥河水道,以及由溧阳通镇江府府治的水道沿线。永平(今溧阳)、阳羡(今宜兴)、润州(今镇江)等郡县城市由于地处太湖、胥河、长江、江南运河航运交汇点,城市综合性快速发展,地位提升。胥河沿线发展了高淳、固城、邓步、南渡等多个市镇。
在经济贸易的影响下,胥河航运功能使流域城镇网络初现,加强了城镇间的经济互动,反过来又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发展。胥河沿线的水运枢纽,成为新城市出现的主要区域,中间虽等级有所变化,但空间位置基本上没有改变,整体稳步发展至宋元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