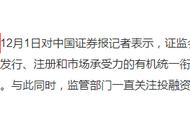文/冉纸

枣树曾长在三叔那边。虽然枣子很甜,因为花开的不好看我就不喜欢它,早已忘记了它的模样。我喜欢我们家那棵梨树,曾站在梨树下听天鹅的叫声。
我的青葱岁月,梨树正置旺年,春季千层瑞雪,秋天一树梨果。梨子个大皮薄熟得香甜欲滴,我却不敢摘;要等八月节这天父亲统一摘下来,最大最好看的孝敬爷爷,品相好的送邻居,剩下的自家吃。
我十六岁以前,家里的住房面积膨胀了一倍,两间草屋变成了四间。我家原本只有小院里的东头两间草屋,西头两间草屋三叔三婶住着。后来三叔盖上新房子搬走了,我父亲拿出一些钱和粮食交给我爷爷,西头那两间草屋就归在了我父亲名下;西边的枣树也成了我们家的树。
那时候,姐姐已经在砖厂做工了,她和两个妹妹住在西头两间草屋的里屋;我和哥哥住在外间。父亲又托了城里的亲戚关系,把哥哥安排在板纸厂上班。上班这两个字听起来时髦,其实就是每天垛麦穰,很苦很累,一天擦湿无数次衣服,是城里人不愿意*活。
父亲一生中最后悔的是复员时犯了浑,拒绝团长的挽留,失去了可能考军校的机会。“考军校”只是一种“可能”,父亲为那份“可能”遗憾了一辈子。父亲学历不低,高小毕业,当过连司务长,是相对有眼界的农民。父亲比其他土里刨食的叔父大爷们有文化,更注重教育。姐姐初中毕业,父亲不甘心他的宝贝女儿打庄户,鼓励姐姐复读。姐姐复读一年去砖厂务工,后来成了种菜园的行家里手。接着父亲透支了全家的经济能力,透支了自己的智慧细胞和所有的人际关系搭建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平台供哥哥上学。父亲很有自知之明,深知草椽茅牖和高等学府之间不仅仅是筋斗云的距离,不让哥哥读高中考大学,安排哥哥冲刺小中专。父亲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首先通过他舅舅的关系,安排哥哥到相邻公社的中心中学复读。哥哥也够辛苦,为了满足父亲望子成龙的战略需求,不得不每天步行十多里路去那所学校点名报号。父亲令行帷幄,却没能决胜十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老人家用大米撬动了我外婆家的老表亲关系。那些老表亲都城里人,十分珍惜不用粮票和钞票就能得到的新鲜粮食;他们非常热情,安排哥哥去临沂一中初中部就读。父亲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父亲的成龙计划看上去天衣无缝,怎奈哥哥天资聪颖,却不耽鼓箧,每次发榜都榜上无名。三十六计计计落空,父亲撞在南墙,头破血流。父亲擦擦额头带上大米和小豆,又托热情的老表亲给哥哥找了个临时工的工作,去板纸厂当了垛草工。暑假的一天,我循着拉麦穰的马车去过板纸厂的草料场,哥哥带着用报纸折叠的帽子,浑身晒得黝黑,只穿着大裤衩,顶着烈日用铁叉子将无边无际的麦穰堆垛成一座座小山。
“巧了能转正呢?”我记得父亲这么说过。
父亲还时常说,上好学才有出息,有文化才有前途。哥哥姐姐的学业落下帷幕,俩妹妹都不愿意上学,我似乎可以站在父亲培养孩子的平台中央。
那年那个夏天,我参加了残酷的中考。中考本来没有那么残酷,到了我们这一届突然就残酷起来;不仅残酷,而且极度的不公平。那几年,九年义务教育从5加2加2变成了5加3,第九年不知被哪位专家教授就着小米粥喝了。那次中考,奇葩得有点诡异:学校里没有英语老师,学生连英语课本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中考却堂而皇之地有了英语试卷,占了八十分的分值。不知哪个崇洋媚外的教育界精英搞了那套教改方案,用英语这把洋铁钳死死地钳住散发着牛粪味的孩子的喉咙,别说发声连喘息的机会都没给我们留。那次教改对那届学生的家庭来说是普惠政策,所有家庭都不用再为承担这群孩子读高中的费用而发愁,直接把这群没缓过劲来的娃推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汪洋大海。
毕业茶话会上,老师告诉我们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大家都明白,另一种准备是奢侈品,那条充满希望的阳光大道对我们关闭了大门。老师说我们的母校将关闭中学,只保留小学,新学期初中生都去新建的联中上课。新联中有英语老师,开设英语课程。老师鼓励有潜力的孩子复读,学习英语再搏中考。我在老师动员的学生之列。初三那年我刚开窍,参加了几次公社单科竞赛,虽然没拿到名次,也是老师眼里的潜力股。我被老师讲得热血沸腾,没来得及和同学们洒泪话别就急匆匆回家。
姐姐不想复读,父亲鼓励姐姐;哥哥不愿意学习,父亲托舅舅、找老亲为哥哥搭建平台。老师的热情鼓励让我心中充满了想象:相对于姐姐哥哥的被动学习,如果我积极主动提出来去复读考高中,父亲一定会平易近人起来。当时学校在邻村常旺,我跑出学校没走石桥,就近跃过水坝回到冉庄。走在冉庄的大街上,每一道墙都是那么亲切。拐进巷口就能看见门前井台上的水车;水车翠绿翠率羞涩得像前排的小女生;新雨后的梨树叶子漫过院墙,反射着明光向我招手。我想象着父亲知道他的小儿子想学习想上进以后的高兴劲。
推开大门,叫了几声“大大”,公鸡惊慌失措地从堂屋里跑了出来。我歪着头看梨树,梨子还没开个,绿得让人心花怒放。阳光穿透梨树叶耀得人眼疼。
父亲扛着一捆柴草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父亲抹了一把脸坐下,一家人才各就各位,坐在紧靠书桌的饭桌周围。母亲宣布开饭,姐姐跑去给父亲盛饭。
“学不用上了,明天去挑水浇麻缨吧!”父亲搁下饭碗像是在说我。
罩子灯放在书桌上,父亲坐在灯下的黑影里,我只能看见灯火,看不清他老人家的脸。我家本来没有罩子灯,父亲为了方便哥哥姐姐晚上做作业,卖了大米买了盏罩子灯。
热血沸腾了一下午,我冷静下来,心里开始犯嘀咕。感觉父亲搁下饭碗出去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我急切地叫了一声“大大……”

父亲坐在了大椅子上,拉开书桌抽屉撕张旧本子纸就着书桌折了一道,左手食指和中指摁住一头,右手食指将那道折子压了一遍。父亲两只手捏起那张纸看了看,舌头垫在下嘴唇上,用唾液将那道折从这头润到那头,然后慢条斯理地把那道折撕开,左手食指居中,拇指和中指往上翘起把张纸条压成了槽,右手往槽里匀着烟丝鼻子里“嗯?”了一声。
我的心收紧了说:“老师说我复习能考高中。”
父亲没说话,卷好了烟点着,咳了一声站起来,走了。我看着父亲伟岸的背影,想起草料场里的哥哥,没吃完那顿饭。
我跟着父亲挑水浇玉米。玉米地离小河三百多米远,父亲挑起水桶一口气就来到玉米地;我挑着水桶一路歪斜,歇三次才能到地头。我把水桶放在地上,拿起水瓢,一株玉米半瓢水。
“我想再去上学。”休息的时候我说。
父亲没说话,挑起水桶,迈着疲惫的脚步,回家午睡去了。那时候父亲已经开了二年的豆腐坊,每天凌晨一点起床,天亮后挑着豆腐沿街叫卖。
心里有事,我就没睡好觉;后半夜听见父亲拉风箱的声音坐起来。风箱“呱嗒呱嗒”地响,这时候去找父亲说事儿肯定不行。风箱停了,我连忙穿鞋。
父亲透过水蒸气看见我一愣,问:“起这么早干什么?”
“大大,我想上学……老师说我……复习……学英语……能考上高中。”
“咱老祖坟上……没冒那股青烟!”
“我真想上学!”
父亲舀起一舀子水准备刷锅,听了我执拗的话把水倒掉说:“你哥都不行,你更不行!”说着把舀子扔进大锅里。
白铁舀子在大锅里发出“咣啷啷”的声响。
新学期开始了,我低落的情绪终于得到了父亲的关注。梨长得比鸡卵大,眼看要赶上鹅卵的时候。父亲叫我。我来到梨树下,立正,看大脚趾。脚趾旁,一只蚂蚁在急急忙忙地向着梨树奔跑。父亲坐在木墩上,旱烟锅子“吱啦啦”地响。
“还想上学?”这句话带着烟味和温度。
我可怜巴巴地看着父亲点点头。
“看行动吧!”
我不知所措地看着父亲又点点头。
“你真有那才分,自学也行!”
我看父亲的眼睛,父亲眼圈是黑的,目光亲和。我低下头没点头,听见父亲说,“自古以来有出息的人都得经历磨难……家里遭难才出能人……自学也能成才……”
父亲当时应该有一肚子劳其心志的说教,没说出来,眼角有些湿。我不知道父亲要表达什么。
“……看行动吧,你上学上的早,要是真有那才分,过了年再去复习也不迟,我去和老师说说……”父亲的话留了半截,我站在梨树下慢慢品。梨树叶想遮住太阳却不能,洒漏着耀眼的光芒。那光芒随时被遮挡,又随时穿透缝隙,洒在地上。我相信父亲的力量,坚信父亲和老师说说就会起作用。
有了英语成绩中考肯定没问题,自学应该从英语开始。我留意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讲座马上就要开课,给电台写信求购教材,期待回信。一天,两天,三天……十天后收到回信,售罄。我给远在胜利油田的四叔写信。四叔骑车从油田去淄博,只买到了广播英语教材的上册。
买到了英语教材,我就和同学一起去老师家。老师说真想上进,可以给我保留一个复习的学籍名额,再和我父亲慢慢沟通。自学很顺利,英语讲座从五点二十开始,五点五十结束。我每天走着坐着练口型,背单词,嘴里嘀嘀咕咕,村里人听不懂以为我得了精神病。父亲每天五点十分准时叫我起床听英语讲座。从秋天到冬天,一切顺利,英语学得像模像样,其他课程复习也按自己的计划悄悄地进行。
时间一天天地挨过了春节,迎来一个被干旱煎熬的春天。梨花终于开满了枝头。风吹来,花瓣扑簌簌地落了一地,枝头有了稀稀拉拉的桂圆大小的梨果。我站在梨树下问父亲什么时候让我去学校。父亲一愣说你怎又想起这一出。我说我从来就没忘过,你答应过我的,去和老师说说,过了年去学校复读也不迟。父亲铁着脸没说话。我问父亲你不是说看行动的吗?父亲满眼的无奈。
我和同学一起去找老师问学籍的事儿。老师说这事必须得我父亲说话才行。
我站在梨树下歪着头质问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待我。父亲拿出了*手锏说:“想上学可以,和我签个合同,每天只给你三个煎饼,考不上大学不给你盖房子娶媳妇!”
我仰视着父亲,那张脸仿佛是青铜铸就的,尊严不容侵犯。我咬咬牙,不看父亲看树,果疏叶密,树叶间没透过来一丝儿阳光。我想起阿Q画的圆圈,攥起拳头,发出歇斯底里的呐喊:“你不让我上学……行!我……自学……我要成为作家!!”
青铜脸上有了胜利者的蔑视和不屑,把“心高够不着天”六个字撂在地上,去了西头的锅屋。
枣树下传来铁铲子戗锅底的声音。
我攥着拳头,闭上眼睛砸自己的脑袋,对父权的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失败。一股热的东西从紧闭的眼角窜了出来,流过嘴角,流向下巴,越往下流淌越冰冷。锥心的铲子声停歇了,耳边传来天鹅的叫声。空中,十几只大雁排成行,从南方飞来,往北方飞去。
“吧嗒,吧嗒。”荔枝大小的青涩的梨子跌落在我脚边,一个,两个,三个……果皮跌破,苦涩的汁液四处流淌。
我站在苦涩的中央,张开双臂拥抱天空。大雁越飞越远,变成十几个成排的黑点,把那悠远的叫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图片源自网络)
【作者简介】作者冉纸(冉祥熙),山东临沂人,一九六七年十月出生,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水牛坟》《追忆一九三八》,诗集《小冉时代》,散文随笔《人生之端》。作品散见于《山东文学》《天池小小说》《百花园》《齐鲁文学年选》和《当代小说》。
壹点号当代散文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