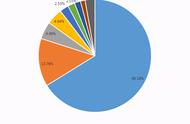第二章 源流
我国境内许多民族的形成一般都经过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民族的发展阶段,而回族却不同。它是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逐渐形成的,它的主体来自西域,却繁衍于中国。它的形成跨越了从氏族到民族的所有阶段,这是回族形成的特殊性。
诚然,回族的主体来自西域,而西域这一个概念其范围非常大,从地理位置而言,它领有中亚、西亚等广大地区;从民族而言,则分属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其他中亚人等。因此,唐、宋时期的西域是一个复杂的地理概念。唐代,广阔的西域已为伊斯兰文化所统一,由于东西文化交流的需要,西域人陆陆续续进入中国,是伊斯兰文化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并在中国居留下来,从唐到宋,被称为蕃客,其后裔被称为土生蕃客,这是回族来源的主干,昭通许多家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十三世纪,蒙古大汗西征,中亚、西亚广大地区为蒙古征服,回师东进时,大批的西域人又被裹协而来,或从政,或从商,绝大多数从军,“上马以备战斗,下马则屯聚养”,分别编入“探马赤军”和“回回亲军”之中。不论他们来自何方,也不论他们所从事什么职业,统称为色目人,有时也称为回回。回回是色目人中的伊斯兰教信仰者,是色目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大批的色目人与原来的蕃客、土生蕃客的后裔不期而遇后,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特征的民族在东方开始展现其端倪。为了适应中华文化传统,伊斯兰文化以其理念的开放性对儒家文化作了精心选择,从而创造了回族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文化通过汉语传播吸取华夏文化精华,是中国回族得以形成的基础条件。留居昭通的色目人在他们的生活实践中具备了这个条件,于是就自然地演化为回族。
明初,朱元璋派遣傅友德率兰玉、沐英等回族将领进入黔、滇,所率兵丁多是西北和江南回民。为了在政治上控制黔西北、滇东北地区,进而稳定西南大局,便以乌撒(威宁)为据点,屯兵驻守,于是威宁便一跃而为军事重镇,驻守的回族屯军一面为朝廷守土争城,一面逐步向民户转化,成为地道的回族。同时又有上千回军在昭通葫芦口与八仙海屯垦。乌蒙山回族就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由于乌蒙土司禄氏有较强的保守性,对非其族类采取不甚欢迎的态度,致使昭通回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改土归流前后,清政府采取利用汉族、回族以镇压彝族的方针,不仅将哈元生将军所率的回军投入军事行动,而且还征调回民作为临时“乡兵”参与所谓的“平叛”。军事结束,一部分回族将士被安置在昭通领土占籍,紧接着又以优厚的条件招垦,于是,威宁、宣威、会泽、东川、曲靖等地回民便蜂拥前来垦植,目前昭通回族的分布状况基本上开始于这个时期。
如果说唐、宋的蕃客与土生蕃客是回族的首批先民,那么元代的色目回回则是回族的第二批先民,这两批先民就是构成回族的主要来源,而明、清进入昭通的回回,不论他们来自哪里,都是回族的迁徙和蔓衍,简言之,是民族的发展,并不是支系的嬗变,昭通回族是全国回族的一个有机的部分。
那么,当昭通回族这个民族群体形成以后,有没有其它民族以群体或部分融入到回族中呢?回答是肯定的。据《元史》记载,元代,畏兀儿(维吾尔)人曾在昭通屯戍,这部分人便成了昭通回族的一部分。又据有关家谱记载,回族中的保姓、铁姓、余姓,原是蒙古贵族,元、明时期先后融入昭通回族,成为著名的阿訇世家。明、清之际融入回族的尚有汉民。目前,昭通回族有108姓,传统的姓氏有马、赛、撒、锁、纳、张、李、杨、米等20余姓,其它许多姓氏来源还有种种不同说法,未能确考。据家谱记载,从汉族融入的姓有孔、阮、冯等姓,家族人口已成千上万,而且历代都有非常著名的大阿訇,有的还握宗教的牛耳,有崇高的威望。除此,雍、乾年间还有彝民融入到回族当中,《大师马家谱》、《松林马家谱》、《都民军马家谱》都有明确记载。以上事例说明回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回族不是以血缘或地域为基础形成的群体,而是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以汉语为交际媒介,并通过使用汉语进而吸收儒家先进文化(包括与伊斯兰文化重合的理念)而形成的文化群体。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回族所具有的浓郁的乡土观念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众所周知,昭通汉、彝、苗等民族称回族为“亲戚边”,不正是通过文化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注释吗?
关于昭通回族源流,正史记载太略,地方志书语焉不详。改革开放以来所掀起的回族历史研究大潮中,拥有16万人口的昭通回族历史与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关注,求其原因,在于资料太少。为了弥补这个不足,特不嫌其烦地将有关资料统为一篇,供研究参考。
一、唐、宋时期
中华回族的来源是多元的,是以西域人为主体,与汉族、蒙族、维族及其它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回族的母体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但它不断地吸收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文化。回族及其文化同时萌发于唐、宋时期。
公元七世纪,在亚洲东西两端同时出现了两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国,一个是以儒家文化为立国之基的大唐帝国,一个是以伊斯兰文化为立国根本的阿拉伯帝国。大唐帝国的文化西越葱岭,向中亚一带深入,而阿拉伯文化则东穿黑海和草原,也向中亚一带传播。古丝绸之路的商业交往成为两大帝国联系的契机,而丝绸却成为两种文化交流的纽带。阿拉伯语称中国为“逊尼”,它的意思就是丝绸之国。两个文明大国终于在沙漠的绿洲间各自获得了对方的信息。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获得了有关中国的所有信息后,向穆斯林世界发出了庄严的号召:“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也应当前去学习。”这无疑是知识的一道彩虹,是通向中国的一座友谊的桥梁。在先知睿智的召感下,阿拉伯派遣出向大唐皇帝致意的使臣,派遣出大批以交换为任的商人。他们怀着美好的憧憬,络绎不绝地奔走在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上,纷纷扬扬地来到东方第一大城——长安。据《旧唐书》和《府册元龟》的记载,从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到公元789年(贞元十四年),阿拉伯帝国到大唐首都长安通聘的使团就有37次之多,平均每四年一次,来往之密,古代外交史上罕有。使者和商人为了表示对大唐皇帝的敬意,常携来大量名贵的阿拉伯特产(方物),有香料、犀牙、珍珠、龙脑、乳香等,受到皇宫、贵族社会的普遍欢迎(杨怀忠《回族史论稿》)。当时唐朝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统治阶级认为“四夷”来朝是天下归心的表现,从而表现出少见的阔绰和大度,回赐的东西远远超过进贡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种以政治包装的通商活动,中、阿双方都从中得到了实惠。作为通聘的使者,来来去去,一批去了又来一批,并不是一种稳定的职业,他们所起到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搭桥引路作用。而商人却不同,他们既可以来了又去,还可以去了又来,不受时间的限制,唐朝政府给阿拉伯商人以优厚的待遇,为他们构筑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便长期居住下来,在异国土地上娶妻生子,招夫纳婿,一代一代地繁衍着种族。为了生活的方便,他们聚街而居;为了过宗教生活,他们在聚居之处兴建礼拜堂,“小集中”的局面就这样形成。实际上在西域商人这个社会群体中,包含有阿拉伯人、中亚人、阿富汗人、西突厥人、回纥人等,全由“伊斯兰”文化这一个纽带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各自的母语并不给他们带来交际的方便,于是他们遵照先知“到中国学习”的训导,选择汉语作为相互交流、联系的工具,回族说汉语自此开始。不过这一个社会群体在唐朝人的眼光中,是属于商人,而且是有不同于华夏文化的商人,因此,概称之为“胡商”或“蕃客”,表明留居中国的西域人在政治上还没有取得“中华”的国籍,在文化心态上还没有适应中国的文化方式,所使用的汉语也并不娴熟。总而言之,外来文化的特征(至少是表面特征)还居于主导地位。因之,称为“胡商”、“蕃客”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到了唐玄宗开元以后,大唐帝国内部政局变化,致使西域的交通不畅,于是商人又凭着他们丰富的世界知识,开通了从阿拉伯半岛沿波斯湾通向中国南方的海路,使者、商人与唐朝前期一样,不绝如缕,历晚唐、五代以到两宋一直兴旺不衰。据杨怀中先生《回族史论稿》统计,从公元968年(宋开宝元年)到公元1168年(宋乾道四年),阿拉伯帝国派遣到宋使团达49次之多,历两百年,平均每四年一次,其密度与唐时相等。西域与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紧密可见一斑。
经过唐、宋时期的蕴酿,定居中国的西域人至少已经历了二十多代,取得了“土生蕃客”(侨民)的称谓,他们对华夏文化不仅适应还有较深的了解;他们的人数已经不少,而且分布呈“线、点”的推移。一般来说,长江以北,从长安推向郑州、开封、洛阳、济宁,然后沿运河南抵扬州;长江以南,则沿南海、东海、从广州到泉州、明州、杭州,然后沿运河北抵扬州。唐、宋时期,扬州成了中华穆斯林最集中的城市。这是先民独特的向心推移方式。如图:
长安→开封→洛阳→济州
↓
扬州
↑
广州→泉州→明州→杭州
当推移到一个城市以后,为了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方便,往往建立清真寺(当时多称为礼拜寺),并且围绕清真寺聚族而居。以后回族在全国范围内“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就在此时打下了基础。唐宋时斯扬州的穆斯林相当多《新唐书·四神恭传》载:“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到了明末,清军残*扬州军民二十多万,其中回族就达两万伍千余人(杜文秀《古兰释义》)。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至于南方的广州,唐时,李勉任岭南节度观察使,“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实行海洋开放政策,原先,每年从阿拉伯来的船舶仅四、五艘,而到公元769年(大历四年)末,“至者四千余”(《旧唐书·李勉传》卷131)。杨怀中先生推算:“若以每舟容载200人计之,四千余船舶当载人至八十余万,一年之中,每日有十一艘进口,二千二百余人登岸。唐时广州海外贸易之盛,可以想见”(《回族史论稿》)。其中,有人回去,有人又留下来,土生“蕃客”的层积也就越来越深了。
唐、宋时期,土生“蕃客”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自然会把“蕃商”的活动领域扩大,深入到军事、政治、文化领域。
唐天宝年间,安禄山率兵反叛,洛阳、长安相继失陷。“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以文平郡王为天下兵马元帅,率溯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等兵二十万以进讨。……贼将张通驻守长安,闻守忠败,弃城走,遂克京城。”(《新唐书·代宗纪》)那么,所谓“大食兵”是怎么一回事呢?《文献通考·大食传》说:“阿蒲罗拔为王,更号黑衣大食,蒲罗死,弟阿恭拂立。至德初(公元756年)遣使者朝贡,代宗取其兵平两京师。”千里迢迢武装朝贡,这是不可能的。实际是唐朝政府向大食国借兵,现在昭通回族还盛传“唐朝政府以三千汉人换八百回回”的故事,就是由这段史实演化出来的。战争结束以后,所有大食兵丁(包括原来的“蕃客”,乐于居住在东土,不愿再回到故地去。唐朝政府就“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对大食兵的统领,则封为“兵马使”或“牙将”而且将他们“分隶神策两军”(《资治通鉴》),其政治地位在禁军之上,给养十分丰厚。这是回族先民由从商转到从军的开始。不止如此,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阿拉伯使者含差、乌鸡、沙北前来朝贡,“皆拜中郎将”(《文献通考》),这样,回族的先民又取得了在东土“从政”的资格。到了宋朝开宝元年(公元968年),阿拉伯帝国“遗使来朝贡。四年,又贡方物以其使李诃末为怀化将军,特以金花五色绫纸写官诰以赐”(《文献通考》)。南宋末年,南方福建泉州的蒲寿庚也是来自西域的“蕃客”,曾为南宋朝廷平海盗有功,“累官福建沿海都制使,总海舶”(《闽书》卷十五)。以上事实说明,回族先民在唐、宋时期,有的已分别取得了中华国籍,其上层人物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民享有较高的待遇,他们的出现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汉文化方面,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唐朝大中二年(848年)“大食国人李彦升,为大梁连帅范阳公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全唐诗文·华心说》),值得大书的是,五代西蜀的回族先民(波斯人)文学家李洵。李洵,字德润,祖辈来华后客居长安。唐末,随僖州入蜀,居四川梓州。王建割据西蜀,纳其妹李舜弦为妃,洵以文才为王建所赏识,成为“花间派”词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十四国春秋·李洵传》),所写的词,《花间集》收37首,《全唐诗》第十二函第十册录洵诗词54首,其妹李舜弦诗三首。李洵的词风格清淡,写情写景真实,更善用典故,“九疑山”、“三湘水”、“巫峡、楚王、瑶姬”、“越王台”、“刘阮”、“婵娟”、“巴楚”、“朝云暮雨”、“南浦”、“汀洲”等文人常用的地名、人名和典故,在抒发自己的感情时,信手拈来,结合得天衣无缝。读了李洵的诗,谁也无法相信,他还是一个才华化不几代的蕃客呢!
民族学家以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2卷)。根据这个观点,有人认为唐宋时期的“蕃客”和“土生蕃客”原来既没有共同语言,来华后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语言,加上没有共同的地域,所以似乎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来看待。殊不知作为一个民族(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也不是以地域为基础的部落联盟)的本质条件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条件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蕃客和现代回族几乎完全一样,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必须明白,当时的回族先民既有较浓厚的阿拉伯故土情绪,但是也非常热爱中华,而且在主动缩短文化上的距离,积极消除在文化上的陌生感。元明以后,特别是当代回族,已经从理性上认识到回族的来源是多元的,是以西域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为主体掺和了维吾尔族、蒙古族、汉族的血统,文化上以伊斯兰文化为主要特征,同时吸取许多民族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华夏文化)而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民族,虽然形成的时间较晚,但也应当算得上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兄弟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代回族所具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从唐、宋时期回族先民那里继承来的。据此,把回族形成的时间下限到元、明之交或明代,恐嫌失之过晚。
回族先民来源于阿拉伯、波斯、中亚这一事实,不仅为历史文献所证实,而且也为昭通回族的许多家谱所证实。蔡家地马、下坝马、松林马、陕西马、马家屯马、陆良马、海子屯李、阮、米、锁、虎等十多姓的宗谱,对各自先祖从西域来华的时间都有明确的记载。
据《陆良马氏族谱》(包括“河西马”)的记载,该族在隋朝(589——618)即已进入中国:
(族)移民,由(西域)至东(东土)渐自隋朝,籍贯陕西熟皮巷,移居应天府,南京籍。
据马良益先生称,该谱系根据立于贵州威宁鸭子塘的祖碑写成(碑毁于文革期间),详见《昭通回族历史资料》。那么昭通陆良马姓(包括河西马)及知识界中一些人认为回族先民在隋朝时期进入中国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呢?
《明史·西域传》根据《通典》、《新旧唐书》的《西域传》说:
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干葛始传其教入中国。迄于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
诚然,伊斯兰教在隋文帝开皇中期就已传入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生于公元570(南朝陈宣帝太建二年),开皇年间,他20岁上下,曾走南闯北,一面经商,一面观察社会,增长见识,属于伊斯兰的酝酿时期。到了大业六年(610年),他四十岁,正式奉天启创立了伊斯兰教,这时,隋文帝已辞世10年,而大业也正是隋朝的兴旺时期,有西域人进入中国是有可能的。但西域人进入中国并不等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二者是有区别的,但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大业时期来华的西域人即皈伊斯兰教则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下坝马姓、陕西马姓、都民军马姓、海子屯李姓、米姓、锁姓等宗谱则认为他们的先祖来自唐太宗贞观年间。
《昭通下坝马姓族谱》说:
旧谱其溯源由来,上悉渊源,幸得踪有据。吾教先世原居西域国。贵圣在位,兴教劝化,(时当)唐贞观元年,唐王夜梦感悟,钦差唐王驾下大臣石棠奉旨西域国,晏请贵圣驾下臣员葛师爸爸来至中国,随从三千人马,奉旨迁居陕西长安府内仓门口,建修清真寺,迨后流派繁衍,分迁居于西安府各处。
《陕西马姓族谱》说:
起祖相乾公,原籍西域国居住,因唐朝外藩未宁,内宫不安,四季反常,五谷欠收,而人心惶惶。某夜,唐皇梦见西方回回进宫与王交谈,并献安邦治国之策,辗转之下,异常畅快。次日设朝,即派使臣往西域国传递国书,西域国王(穆罕默德圣人)派遣葛师随同使者来到陕西长安城。俗云“三千换八百”之故事也。此后我国顺民即住中国,协助太宗平定四方叛乱。……我起祖就住陕西省灵陶府内。
《马氏族谱历年间叙〉(陕西马姓)说:
我族源起西域,唐贞观年间来到中国首敕囗奉住陕西西安,后才移居甘肃,故我族姓氏便命为陕西马。
明确说祖先来自唐朝贞观年间的尚有锁(所)姓,其昭通大蒿地坟山《锁姓碑文》说:
鼻祖原名冉,唐太宗李世民从母罗梭请来,移陕西长安城内,受唐主钦赐封参将(将军)世职,后派往固原柳树巷白塔前(见《昭通回族社会历史资料》)。
而《锁氏家谱总序》所述则略详于墓碑:
鼻祖源远流长,唐……遣臣石棠至西域,……往母鲁素,奉请……穆圣后派遣与众族来东土,先祖住陕西长安门(城)内,受唐主钦赐封参将(将军),世职。后又派往固原柳树巷白塔面前。
“母罗梭、母鲁素”系同名异译,滇西一带回族有的认为先民来自“鲁穆国”,“鲁穆”可能就是“母罗梭”音译的变异。
昭通回族以为先民系唐贞观年间来华之说外,尚有延和、天宝二说。
《蔡家地马姓族谱》说:
至延和初(公元712年),奉命来中国,蒙唐皇建寺安置,落籍太原,仍封袭号,宠礼上宾,以大师名家。厥后,宋、辽治兵,(女)真乘衅,宋、元鼎革之交,以兵燹,故(离)中原,祖居固原柳树巷。
继云:吾祖实起自委里阿式麦克城,阿波斯爸爸之后裔,阿波斯兄弟十人,乃吾贵圣亲叔父。阿波斯雁行第六,后裔兄弟四位来东北(土),是唐延和初来中国。
“延和”为唐玄宗即位二年后五月间所改的年号,旋即改为先天、开元,距天宝尚有30年。至于家谱所提到的“阿波斯”,有的史书写为“阿拔斯”,《新唐书》和《文献通考》又写为“阿蒲斯”。对此,《大师马家谱历时系统图考大司马氏渊源史考》说: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树之有根,水之有源。知其先后,则道原矣。……穆罕默德之亲叔父阿拔斯乃吾鼻祖也……居为将,圣世后裔,生于高贵圣人之家。曾孙阿拔斯乃阿拉伯第二王朝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开国之君,建都巴格达,世袭五百零八载。吾族起始祖公讳泽源,乃穆罕默德亲五叔阿拔斯第四十二代孙,是阿拔斯之曾孙艾卜阿拔斯国之第三十八代孙。
持唐玄宗天宝年间(722—755)进入中国的有马家屯、松林马、虎姓等。
《马家屯马氏家谱序》说:
唐贞观(天宝)时,安禄山叛乱,国政乱如丝麻,玄宗避兵西蜀,郭汾阳来请我族援助。我族本至圣之遗训抑强扶弱之精神,慨然义助。无几何,国泰民安。玄宗回銮长安,再三挽留我族,于咸阳建筑王府,敕封首领为咸阳王,优裕我族,此为我族之入中国籍也。当是时也,宣扬圣教而人才稀有,(乃)派人回桑梓,聘请邃于经学者,来至中国以掌教。(但)我祖根,原住于近东不花次城,为大教长职,亦在聘请之列,此我族来至中国之始祖也。盘踞于陕西省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居焉。
本至圣传教之训条,宣扬教化清真(多词妙序泉涌),授其教者,馨沐降服。人才之多,硕然荟萃,胤胤相传。
《松林马姓家谱序》说:
盖闻木之长者,必因其根;水欲流之远者,必依其源。……我祖先原为西域圣裔,于天宝元年春来至中国,居陕西西安,传圣道立清教多年,唐皇乃命工部督匠,建寺长安,赐名清教寺,用天经教化民众。……我祖先姓马者,是波斯文之词首,音同汉语之马而来。以因唐皇封为太师,故有太师马之称。……因子孙繁衍,始迁各方,唐皇乃命我祖移住固原府寺口子居住,系名门望族。
《松林马氏族谱新序》说:
祖先则为子孙之本源,不可不究其源,循其根。我先祖,据传原系阿拉伯穆斯林,于天宝年间来到中国,寓居陕西长安。先祖姓马,是因阿文名字的词首音与汉语马字同音。后由于子孙繁衍,始分别迁往他处。我族先祖迁往陕西固原府(宁夏回族自治区)寺口子居住,遂发展成为该地名门望族。
《虎姓族谱序》说:
唐王奉请西兵,镇压国土,征剿四方匪徒,吾祖奉请来朝。唐王亲封虎威将军。……平服之后,封赐采邑于陕西西安府红弯子,故由此,子孙永远姓虎。吾祖世代住陕西,以后子孙繁衍,各居一方,有过广东者、山东者、又有山西、湖南、湖北、四川诸省。吾祖之居住陕西,世代久远,由唐至宋、元、明、清,千百余年。
此外,李姓、米姓等家族,都自认为先祖从唐时进入中国,唯具体年代不详。
《海子屯李氏家谱序》说:
追溯吾先祖由来,原系西域阿拉伯,至圣兴教劝化执政时期,于唐朝奉诏,随遣贡使抵中朝,受赐奉安,居于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仓门口,继迁徙于固原州平凉府李旺堡。
《米氏家谱序》说:
盖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惟光前之盛,而有裕后之兴也。我族原系陕西省汉中府南郑县塔耳巷。考其原来,祖籍西域,自唐奉命来于中国,命居陕西,世代相传,其荣世者,不可尽述,所叙耳,沧海一粟。原祖世代,扶帝治国,修身齐家,有功家国,帝爱如珍,但祖辈传家,耕读为本,坚辞爵禄,帝拒辞未许,世代受爵。
以上二姓并杨、段等姓进入昭通的时间虽有参差,但在追述祖先来华的时代则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唐时,这种口碑的说法已成为民族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根据上述,可知昭通回族中的一部分实系唐代“蕃客”和“土生蕃客”的后代子孙。例如唐代长安有熟皮巷这个地名,表明当时的蕃客所从事的职业是“皮革”,而昭通回民有许多家族都是出名的“皮革世家”,昭通西城毛货街即因之而得名。从熟皮巷到毛货街,表明蕃客(回族先民)有其源远流长的职业。
唐初,政府轻徭薄赋,采取了一系列使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措施,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对外开放丝绸之路,从而将大批西域人吸引到中国来,或经商,或传播文化,或交流技术,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开放浪潮。当时穆罕默德圣人通过伊斯兰教运动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其后继人阿拔斯帝国,则将伊斯兰文化传播到毗连中国的葱岭以西地区,并且相继传入中国,而陕西则是回回先民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站口,从某种意义上说,陕西西安是回族先民的发祥地,因此昭通回族言必称“陕西”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文献(包括家谱),还缺乏回族先民进入乌蒙山区的记载,民间也没有这样的传说,这是值得注意的。
二、元朝时期
元蒙时期,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人随着蒙古铁骑移入中国,出现了回回先民移入东方的高潮,人口之多和来势之猛远远超过了唐宋时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就在这个时期,回回先民首次进入昭通,通过从军、屯垦等活动方式和分布于其它地区的先民一道,按照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演化而为回族。
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从宁夏进入甘肃,经六盘水集结于临洮,进入到四川北部松潘以后,便兵分三路直扑大理。大理国统治者段氏凭苍山、洱海的天然地势拒守不降,经过激烈战斗,元蒙大军终于一举攻下大理,消灭了这个割据云南三百多年的民族政权,完成了扼长江上游以制南宋的战略部署。
元蒙十万大军中有来自西域的回回军约五万余人。他们“性强悍,作战勇猛,骁勇善战,所向报靡。”(《大理古佚书钞》李浩《三迤随笔》),在攻下大理城的战役中立下大功。大理攻陷后,元世祖亲拨回回军四千人留守,在大理南北五里亭屯回部各一千,龙首、龙尾城各一千,军属三千。军饷由大理路供给(《大理古佚书钞》玉笛山人《淮城夜语》)其它回回军则随蒙古大将兀良合台征讨滇中、滇东以及川西南、黔西等地尚未臣服蒙古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元宪宗四年(公元1254年)兀良合台先后平定合剌章水城(禄劝)、罗部(罗次)、昆泽(宜良)、押赤(昆明),初步稳定了云南形势。接着又兵分两路,一路攻下秃哥赤(贵阳),一路攻罗罗斯(西昌)。控制了原大理国“五城、八府、四郡”及乌、白蛮三十七部的全部疆域。每攻下一个城市或战略要地都分别派遣回回军参与留守,尔后云南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即始于这个时期。
元宪宗六年(公元1256年)兀良合台受蒙哥命打通与四川驻军会师的通道,率兵征乌蒙(昭通),攻下由秃剌蛮(土僚蛮)据守的四川筠连等三座城市,攻破长江以北的马湖(雷波、屏山),直逼叙府(宜宾),与宋将张都统兵三万激战,夺其船二百艘于马湖江,通道嘉定(乐山)、重庆、合州(合川)与四川会合。完成平定马湖江的任务后,沿旧路,经乌蒙返回云南。(《元史·兀良合台传》兀良合台援川战役,虽也在攻城夺寨,但对乌蒙来说,纯属过境性质。援川蒙古军中有回回军,自不待言。返回云南时有没有遣回回军留守,尚缺资料。但是,不论怎么说,这是回回先民首次进入昭通的历史纪录,应该引起重视。
根据《元史》记载,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到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十二年间,因蒙古的政治、军事文化与乌蒙山区以彝文化为主体的地方民族文化产生了严重的碰撞,导致了彝民的不满和反抗,致使元朝政府多次派兵前来剿抚,每一次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回回军,这是回回军无法回避的历史苛派。这就是说,为王前驱、讨伐反朝廷的政治集团或地方民族势力是回族先民进入昭通,及至落笈昭通的历史原因。
不过,应当看到,军事职业却为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直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得从回回先民的族属说起。
昭通回回先民系来自大理的西域人。那么西域人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大理古佚书钞》的《淮城夜语》以为回回军系“色目人”,“皆来自波斯、突厥部”,就是说,被称为回回的色目人分属于不同的地域、国家和民族,各具有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但却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即《淮城夜语》说的:“信阿拉,尊穆罕默德为圣。……忌酒、不食猪、螺、黄鳝。……作战勇猛,以死为荣,至阿拉神殿安适。”所述都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典型特征。蒙古王公贵族按照回回兵宗教信仰的这个特点将他们组合在一起,编制为有严格纪律的军事组织,过着共同的军、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十分便于管理,对完成军事和其它任务起到了良好效果,同时对军事组织素质的提高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大大地促进了宗教礼仪的规范和整合,各种各样的殊方异域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礼仪的影响下逐渐向统一,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日积月累,“认同感”在方方面面不断强化,一个崭新的社会群体即将跨进民族范畴的历史门槛。
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昭通回回民族的先民,马不停蹄地从西域来到中华,从北方走向西南,从大理走到昭通;从金戈铁马的戍卒到扶耧弹鞭的屯垦,最后,由军户演化为编民,成为乌蒙山下的穆斯林回族。对于这一段历史渊源,《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六说:
回民之来昭,据旧志所载,实起元时,以兵屯田,多半皆系回人,后遂流落于此。
据彼教中人言,(伊斯兰教)流传已数千年矣。至隋时,有穆罕默德,奉真主之命,在土耳其讲经传教,后始流入中国。考《明史·外国传》:有默德那,即回回祖。国王谟罕蓦,亦作默德,生而圣灵,臣服西域诸国,国久尊为别谱援尔,译言天使也。隋开皇中,其教即传入中国,后安、史之乱,回纥出兵五千人,相助灭之,遂多留中土,其教遂散在四方。昭之回教则自元时派兵屯田,流落于此。
邱树森先生在论述元代云南回族的来源和发展时,引用了《昭通县志稿》的有关论断(见《中国回族史》上册223页)
三、明朝时期
明初,随着明王朝对西南的用兵,四方回回又一次涌进云南,贵州乌撒是回族进入云南的第一个站口。早在元代,乌撒、乌蒙宣慰司就驻在威宁,主管乌撒、乌蒙的军事政治和屯田事宜,该司“秩从二品,每司宣抚使一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兼架阁管勾一员,正九品”(《元史·百官制》)。宣抚司以下中级官员多由回族担任。威宁不仅是政治中心,交通枢纽,而且也是回族进入西南的首批聚居地。元未两次战争以后,一部分乌蒙回回屯户退到这里,或继续军屯,或转为农户,有少数衣食难济的则成为土司的佃户。政治、经济状况与元初相比已经大大不如,只缘时间较短,所以还没有达到冷落萧条的地步。
公元1831年(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率左副将兰玉、右路副将沐英,领步骑兵三十七万,从四川永宁下,进军云南,与云南右丞实卜(土官)战于威宁,实卜投降,明朝即以威宁为据点,左控乌蒙、马湖、罗罗斯、芒部、永宁,右制水西、顺元诸部,并筑城乌撒(《明史·傅友德传》)。次年四月实卜复叛,平定后,明王朝当即决定:“赤水立一卫,毕节立一卫,七星关立一卫,赫章、迤那(今昭通东四十里)、瓦甸、迤北分中立一卫,”同时部署“东川之兵驻于七星关之南、乌撒之北,中为一卫,其粮饷,则东川之民给之。自以南至七星关为一卫,令六诏、羿子等蛮给之”(张紞《机务钞黄》)。如此部署,军事问题暂行得到了解决,但粮饷仍然非常紧张,遂又决定使戍兵屯田,“傅友德命其子为屯田长,屯垦北关至下坝一带;监军王绳武屯垦大桥(今称杨凹桥)一带;管成垦乌木屯一带;费诗屯垦二屯一带”(《威宁县志》见《贵州文丛》1982.1期)。而兰玉、沐英等都是跟随明太祖起义的江南回族,所带兵丁也多系回族,奉令屯田后,屯田事业在元朝的基础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今昭通回族的家谱对这一段史实都有较为详尽的纪录。
《下坝马姓族谱序》说:
吾太始祖公讳无稽,于大明洪武二年(按应为十四年或十五年)受参戍(钦大降),补乌撒卫千总(侯)。自陕西西安府长安县高坎子柳树湾奉委升迁贵州大定府补任乌撒(钦),护守军门,遂先乌撒卫,建宅茔于城北外下坝狮子马金等山。
《马家屯马氏族谱序》说:
我祖踞于陕西省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居焉。本至圣传教之训条,宣扬教化清白(真),多妙词,序如泉涌,授其教者,馨沐降服,人才之多,硕然荟萃,胤胤相传,迨至明洪武十四年,边省云贵多事,我世祖衣戎南征,有功于国,封为将军之职,卜居贵州威宁县马家屯。
《马家屯三公世系碑记》说:
三公讳超、讳越、讳起,昆季三人者陕西平凉府固原柳树湾马氏望族也。其先始祖公于有明洪武十四年,从丽江王傅公(友德)节征云南,道经贵州,一路望风效顺,安抚得宜,始祖以军功留守乌撒卫,(晋封)建节将军,世袭罔替,历二百余纪。至天启二年,水西安邦彦作乱,宜(迭)遭兵燹,家谱失迷(觅)……
此外,《鲁甸胡寨遇选祖碑文》说:
公讳遇选,时昌威郡,世祖元龙公之次子也。洪武十四年,由陕西柳树湾来游贵州,落籍威郡洋汪桥(今讹为杨凹桥)广积德善,十余传,而子孙振振绳绳居焉。威邑郡人号称为马家屯。
又,大关县高桥区《马公讳贤图之墓》说:
壹血(窃)闻孝之至者终必慎,思之深者渊源远。(公)西犹(域)国之人也。考公先代,原籍平凉,自洪武十四年随军到威洲(州)属之马家屯。高祖寅龙,长子遇魁,次遇连,授职杨丰千总。
又昭通得马寨《马和文墓碑》说:
盖闻马公和文者,原籍陕西平凉府固原州。明朝开基,随军出征,分到威宁马家屯,创业此乡得马寨。系先君贤图之子也。
昭通《松林马姓族谱·朝珍公碑文》:
先祖马能,陕西固原寺口子,望族。马骏自洪武时平滇,以军功留守乌撒卫。至明未,迭遭兵燹,家谱失觅,不可考。
《元位祖公碑文》、《建藩祖公碑序》则谓“自洪武年间移居威宁乌撒屯,世居卯官屯。”或谓“自明洪武间从军乌撒卫,世居威宁之卯官屯。”据以上碑文及旧谱,《松林马氏族谱序》(新序)说:
明朝洪武十四年,先祖马能、马俊二公随军南征,战滇黔,留守乌撒卫。世居威宁城内,祖茔在城西火龙山。……为避战乱,我九世祖鹏鳌、俊起及钟灵公后裔迁居威宁城西杨万桥。
《威宁杨旺桥清柯山虎姓登龙祖碑序》:
吾祖生三子,小祖公落四川成都华阳县,讳不可考。大祖公自公,二祖公自强,由洪武年间奉调来黔,开辟乌撒、盐仓,平定后,兼任贵州巡抚部僚,报领葡萄井丰登山地二型。
而《虎姓狮子山封山碑文》则说“明末奉征剿川黔,戎务。”恐“明末”为“明初”之误。
根据上引,可知“下坝马”姓、“马家屯马”姓、“松林马”姓、虎姓等四姓,其先民都是洪武十四年前后来平定滇黔的中下级军官,军旅毕,留乌撒为官,数代后,成为威宁回民中的名门望族,直到清初。
除军官外,大量的是兵卒或一般平民。《海子屯李姓家程·威宁海子屯四楞碑序》说:
我族先祖李公讳国安于洪武十四年来自陕西(按为兰玉旧部),随军抵威宁,事峻,即落业于海子屯。
鲁甸岩洞《凤仪山四楞碑序》与上文略异:
公讳李国安,祖母谢氏,始祖粤稽其先,起籍陕西省固原州人也,身到威宁阳观山安居乐业。
李姓传到第三代“启字辈”,家业兴旺,挤身入仕林。海子屯李姓启能授武德将军,启檀授怀远将军,启唐授骁骑将军、武功将军,启明为武训和武义都尉。为从平民到望族的典型。李姓移居昭通、鲁甸后一直为回族望族中的首姓。
来威宁的回族平民中尚有锁姓。《锁氏宗谱序》说“洪武年间,先祖明德、新德二公奉旨调派威宁州城,后领土杨旺桥落业居住。至今子孙繁衍,移居四方。”昭通大蒿地《锁姓碑文》也说:“洪武年间,余祖奉旨调派来威宁杨旺桥筲箕湾居住。”
明末,因从事经商贸易而落籍于威宁的为“蔡家地马”姓。《大师马氏家谱序》说:
洪武十六年,有翰林院编修马沙者,系鼻祖之后裔,因讲解西竺(域)所贡天经(古兰经)八卷,蒙明主见喜,仍敕封大师之职,继美于鼻祖,所云明哲之后必有大渭(贵),此也。其后世,历代相承,或以文兴,或以武仕,代有其人。……迨至明熹朝,忠贤矫旨,包藏祸心。吾家来威宁之起祖公讳泽源,窃窥其弊,守道不仕。于天启二年由柳树巷假贸易为名,客游于黔,不一其年,以待世清,始归来。讵意帝位靡常,将厌明德,钤启清朝,加以闯贼首炽乱阶,兵戈云扰于中原,篡逆风尘于上国,于是落业威郡不作归计。
蔡家地马姓,经济实力雄厚,崇祯年间即有守备马泽源,迨迁到昭通后,为回民中之望族。
明朝一代,乌蒙与乌撒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机构设置都完全相同,但乌蒙土司(乌蒙军民府)有较强的保守性和拒外性,不适宜于屯垦,更不适宜于经商。这与回族的特点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居处乌撒的回回虽与乌蒙近在咫尺,并不移入,最多只有一些商人作些流通的买卖罢了。但是,为了控制乌蒙,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就曾经设过乌蒙卫(《嘉靖贵州志》),同时置“乌蒙军民府”(《明史·地理志》),洪武二十年(1387年)“诏以长兴侯耿炳文所部33000人,由回族将军马烨统率,屯戍在大关、昭通、鲁甸(《太祖实录》卷186、188)。杜文秀《古兰释义附录》)。从此,南北两方的回族荟萃于乌蒙山区,使这里成为西南回族人数最多的聚居区。马烨调任贵州都指挥使后,也有回族将领继续来乌蒙屯守。杜文秀《古兰释义八千题附来源》一文说:
(赛典赤)三十八代马文英之后马文衡后裔马德崇(按:据《赛典赤家谱》马尚文家藏本作“马德宗”)入昭通为政教总管,分支各村,到明朝更有众多回回充实。
《赛典赤》家谱马尚文本也说:
(赛典赤)三十八世等三支,祖马文衡,四子马德宗(崇)始入昭通。……昭通马仲鹏、三十九世祖分支德京之后。
马德崇、马仲鹏都是赛典赤后裔,明代在昭通为官后,其子孙都留在昭通,马文衡还为昭通“政教总管”。可见明代并非没有回回。
公元1730年(雍正八年),乌蒙镇总兵刘起元“私派公费、侵欺粮饷、客民被刧,混将头人拷比”(《世宗实录》),激成民变,时“乌蒙商民万计”(《圣武记·西南夷改流记》)其中有不少的回族,多半是明代遗留下来的。
综上所述,明朝是回族进入昭通乌撒的第二高潮期。《滇云历年传》卷六说:“傅友德留兵守御乌撒、乌蒙等处,会师中庆。”看来是有根据的。
四、清朝时期
清代是昭通回族发展的关键时期。雍正、乾隆年间,回族通过军旅、屯田、经商和传教等途径进入昭通,来人之多,声势之猛胜过元、明两朝,出现了移入的第三次高潮。
首先,回族因从军而移入昭通。
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清政府在乌蒙、芒部两处实行改土归流,以满、汉地主阶级的流官统治来代替以土司、土目为代表的奴隶制或封建领主统治制。四月,御批鄂尔泰上报的改流方案,初定先从巧家动手,然后计及乌蒙,徐图镇雄,或者一举两就,或者出其不意,或者令二土府互相吞拼,然后翦除,达到“悉为归辖流官,其一切土目尽行更撤”(《世宗实录》)。谕令下,鄂尔泰采用“互相吞拼”的方案,重用“夷奸”土司之弟禄鼎坤作内应,并派遣威宁镇标中军游击哈元生为右翼,率兵两千多名,协同中军刘起元进剿。当时土司禄万钟年幼袭职,军权全操在叔父禄鼎坤手中,无力抗拒,先逃芒部,后与芒部土司陇庆侯企图逃四川,到石门关被擒,乌蒙、芒部两土府便全部崩溃。事平,刘起元虚报战功,哈元生也以“日踏三江、夜夺八寨”的“军功”进封安笼镇总兵。实际情况是哈元生为威宁游击,系河北河间回族,平素兵不满千,奉调后,为了凑数就在下坝、蔡家地、杨旺桥,马家屯等回族村寨召集回族子弟为临时乡兵,这些回族子弟平素就与乌蒙彝族有较多的经济联系,了解乌蒙内情,熟悉山道,加上乌蒙土司不战而走,他们便避实就虚控制了乌蒙,成全哈元生立了所谓的战功。雍正六年,哈元生赴新任,回族临时乡兵多半遣回威宁务农,少部分则服役于乌蒙镇,或者在威宁、乌蒙之间从事贸易,收牛购马。许多回民重新进入昭通,改土归流是一个契机。但是落籍乌蒙,甚至报领土地之事还未曾出现,从雍正五年到八年的短暂时间内,彝、回、汉各族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
公元1730年(雍正八年),为戡定乌蒙起义,一部分回族将士又随哈元生进入乌蒙。起义平定后,这些军官“领土占籍,择取地方,悉得东、南、北一带高原”(《昭通县志·民族志》)即从桃源沿乌蒙山一直伸到大关的广大地区。
比如李翠,为海子屯李姓四世祖,随哈元生将军前来平定乌蒙,“随营补授昭通镇标左、右营把总、千总、前营游府,奉满引见,授直隶紫金关参将,诰授武功将军。报领昭通八仙海,落户建宅,故称官厅。……分头落业于昭、鲁各地,繁衍至今”(《海子屯李氏家谱·谱序》)。《戛利德超祖父墓志》也说:“公讳翠,启唐公之长子也。启唐公由武举随营补授威宁镇右标千总,于雍正八年随哈老将军出师乌蒙……随师攻战,带翠于军前,翠先父尽忠疆场,损躯报国。翠蒙庙荫,报补威宁镇标把总,历陞昭通镇标前游府。”现在李姓子孙遍及昭、鲁各地。
平定乌蒙时充任军官的尚有“蔡家地马”姓。该姓《起祖泽源公碑序》说:“雍正初年,乌蒙开辟,各祖后裔从军至昭,领照为业,遂家焉。”同治《鲁甸拖姑清真寺碑记》说:“先辈传言,雍正年间,乌蒙开辟,各姓祖人落籍于此,马氏祖燐灿、燐炽以举人随哈将军征平乌逆,落于此地。录正册、纳粮。”关于马氏,《大师马家谱历时系统图考》136页说:
四世三祖公之琼,乃登先祖三子,生子五人,道称名门五桂:燐、灿、煐、煜、炽。灿公授正四品都司,辛卯科进士。灿、炽、二祖率各姓祖人建拖姑寺,煜、瑛、辉三人率各姓建撮落清真寺。
这就是说一支落籍桃源拖姑,一支落籍今永丰布嘎,蔡家地马姓为昭鲁回民中望族。
马家屯马姓系明朝中叶随王骥南征而落籍于威宁马家屯巨族,清初移居昭通,《马家屯马氏族史资料》说:
雍正八年,乌蒙作乱,五世侍卫将军马炳衢奉令随哈元生将军率三世祖玉杯、玉选、玉珍,四世祖中雄、五世祖天衢等族众,统带八十梁子(屯落)征剿叛逆。玉怀公功绩出众,封为千总,九年招安,十年太平,炳衢公即报领土地,落籍昭通小凤凰山。三世祖玉选公弃政耕耘,落籍鲁甸拖姑,玉珍公落业于山口子、玉佩公落业于大柳树,忠骥公落业于昭通小凤凰山。天衢公落业于鲁甸岔冲,玉怀公返祖茔。
“统带八十匹梁子”,说明来征乌蒙的是各族乡兵,由汉、回、彝各族组成,结束,“弃政”即“复员”。
军官中还有虎姓。《威宁烂泥沟虎姓家谱》说:
清朝雍正年,乌蒙作乱,帝王又派贵州提督哈元生为师(帅),吾祖上弟兄七人同领兵征剿。平服后,领食邑之土地,今昭通东门外起,抵至白泥井、水塘坝一带,葫芦坪、元宝山、花鹿圈、鹿柴冲。
今昭通守望乡,太平乡为该姓主要聚居地。
因随军有功,后在昭、鲁报领土地的还有“陕西马”、客籍马和赛、锁等姓。
清康熙年间,我高祖公马玉德中壬子科武举、在清朝供职。饬其子马公相乾同哈将军前往云贵效命。在乌蒙苦战数载,住鲁甸拖姑,娶蔡家地马姓祖婆,就此安家落户。(《陕西马家谱序》)
盖闻吾之高祖马富,曾祖采林、祖父延瑚、延顺,自雍正八年凯旋,九年招安,人民稀罕,烟火寥落,奉拨下鲁报领田地。(《鲁甸牛头寨清真寺碑》)
考我赛姓子孙,一支落籍石屏,清初开辟乌蒙,赛林公随军来昭,落业鲁甸,住地便以赛家营为名。(《赛姓赛家营支系族谱》)
当时鄂尔泰征剿乌蒙,兵分三路,东川路由提督张耀祖指挥,所率系滇中一带兵员,其中也有回族兵丁,如赛姓就是。但不一定都是有军职。
永清兄弟随同哈将军出力,报效有功,由昭通报(领)田地,奉终归主,葬朱家山。必选来小龙洞报领土地,生三子。……到大蒿地报领土地(《昭通大蒿地锁姓碑文》)。
清朝雍正年间,移入昭通的尚有丁姓。据《丁氏族谱》称:原籍南京大梨树人。明太祖洪武初年,钦命敕封祖传宗为将军之衔,遂与弟传海二人领兵到云南,落籍宣威永安铺。军务毕,传宗祖授曲寻协,历任九年。传海一支迁入柳花村后失传。传宗回南京接发妻喻氏来滇,生一子名铎,及长成,授炎方汛官,妻钱氏生子七人:邱斗、邱明、邱明、邱红、邱辅、邱祖、邱珍、邱昌。移入昭通始末,《族谱》说:
清康熙间,丁姓之后尚凤公移居威宁白土坎。雍正九年又来鲁择居盛化庄(即今岩洞丁家湾)。原配谢氏无后,继娶李氏祖母,生三男二女:长子天贵、次子天朝、三子天相。大贵公寿享百岁,号百寿公,二生文季、文成、文顺、文德,乾隆初,天贵子孙移居恩安(今昭通市)高桥之半边箐;十五年,文季、文林搬至江半坡,后散居桃源、龙头山等地。
丁姓的有关资料完整的叙述了该姓迁移的过程,是研究昭通回族迁徙的重要线索,只是从事何种职业,凭什么落籍鲁甸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但从移入的时间和地点、研究来看,也是从军来的。
今昭通地区回族,据《昭通回族社会历史资料》统计共有70姓;《昭通市回族志》(初稿)统计,共有83姓;《鲁甸县回族志》(初稿)统计,共有70来姓;《鲁甸县志》统计有83姓,《昭通地区志》统计,共有84姓,绝大多数都是清代雍、乾两朝进入昭通。而作为军职进入的只有八姓,不及回族姓氏总数的十分之一。历来一些人总认为昭通回族都是随哈元生平定乌蒙而进入的说法,看来并不全面,也不准确。历史事实是,改土归流前乌蒙地方就有回族,天砥是主要聚居区。两次乌蒙战争中有少数回族地方乡兵(包括少数下级军官)作为清政府“以回制彝”的工具进入昭通,正如咸、同年间昭通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当权派从凉山调彝民镇压回民一样,罪魁祸首是清朝统治阶级,无论回族、彝族或汉族都不能负这个历史责任。弄清楚这段史实,对于澄清一些谬说,加强民族大团结有重要意义。
第二,乾隆初年,为了填补乌蒙地区的空虚,应命招耕,大量回族进入昭通报领土地,成为农民以至于今。
公元1732年(雍正十年),即乌蒙平定后一年,当时昭通“人民稀罕,烟火寥落”(《牛头寨清真寺碑》),“既遭兵燹,城市庐舍俱为灰烬,士民散亡,百事旁午”(《昭通志稿·艺文志》引知府徐德裕《新建昭通府学碑记》)。“锋镝之余,招徕安插仅七百余户(估计昭通、鲁甸两县入籍人口不超过四千人),土地荒芜过半”(沈生遴《恩安添建蓄水坝碑记》)。面对着这种残破不堪的局面,接替鄂尔泰的云贵总督高其倬上奏《委员赴昭办理开垦疏》说:
臣查昭通一郡,四面环山,兵米自外州县运往,转输不易,若本地耕获,有资于军粮甚便,且田畴渐广(赤地千里,有田地而无人垦种),则民户日增(即招垦植之人以填补昭通的空虚),可以移易夷习,事属有益。既不可缓,而转瞬春耕时又将届。臣随批定,并遴楚雄府储之盘,带领侯补府、州之顾维铸、钱湟,学习进士黄事鉴,试用胡茵,前往昭通,专办垦务。
《奏疏》明确提出如下一些具体办法:
(一)、雍正十年招垦七百户,次年将招垦一千户。
(二)、将昭通荒芜田亩按水、旱、生、熟四项尽先分配给夷民(口头禅,夷民所存无几)然后按先来后到原则,每人给田二十亩(包括兵户在内)。
(三)、前来垦户,途中大户给银五分、小户给银三分。到昭通后“借发牛、种,开垦为业”(《云南事略》)
(四)、其田,按年陸续收其稻谷,照时价计算,扣还工本。扣清之后,即令起科纳赋之处,仍令输米,以供兵食,以省运费。其田给与执照,永远为业。
当时徐成贞任昭通镇总兵,根据云贵总督高其倬的指示,在屯办人员的协同下,乃下令“凡避贼逃亡及被胁从者,无论汉、回、夷、苗概为招抚”(《昭通志稿·官师志》)。按,乌蒙大起义以彝族为主体,有汉、回、苗参与,现在罪被赦,得到了分配土地的权利。高其倬的新政策,立即受到了滇东和黔西北一带无地农民的热烈拥护,顿时形成了向昭通移民的高潮,主体是回族,其次为汉族。
明朝前期,威宁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区,回族居住在县城马坡,郊外下坝、海子屯、马家屯、卯官屯、杨旺桥等处,因人多族众,土地人均占有量日益减少,加上富户的兼併,生活越来越困难,已逐步向离城较远的戛得、野窝坪子、哈剌河、果化等地迁移,而且逼近乌蒙的边缘。公元1432年(宣德七年)乌撒土官禄尼强占了乌蒙土司辖地麻窝山以西北广大土地,回族随着禄尼的势力迁到了这片土地的迤那、牛棚子、稻田坝、高坎子等地区。明朝出面调解,乌蒙土司禄召以十分之三的土地让乌撒,息讼(《宣宗实录》)。威宁回民因争生存而快速的移动锋芒受到了抑制。本来,回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快速度流动(包括征战的鞍马生涯、畜牧和商业)几乎已成为这个民族的主要生活方式,数百年的旅途奔波使他们感到劳累和疲倦,于是到了明朝中后期,也就渐渐地习惯了安土重迁的农业生活。但是黔西北、滇东曲靖、宣威等大片土地上,移民很快就人满为患,人均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加上大姓的兼併,无地和少地的赤贫农民频频出现,移外屯垦已有了实际需要。当乌蒙改土归流以后,人口和生产出现了真空,而清政府为了弥补他们残酷屠戮的罪过,不得不采取高额代价招耕招种,这种“优惠政策”,具有相当高的吸引力,符合回族社会发展要求,于是举家、举族、举寨向乌蒙移动的运作就合情合理地开展起来。
(铁姓)祖籍沾益州保家乡,遗传鲁甸拖姑。……三祖之来昭也,雍正八年,……哈公奉旨征剿,……昭地空虚,奉命招耕,于是二伯祖在曲靖奉父命,于雍正九年,入鲁报领地方,家室一同到此。(《乾隆铁氏宗谱序》
又:二世祖递传三世祖,昆季四人、定远居长,所遗三子,艰险来鲁开辟之祖也。(《光绪铁氏宗谱序》)
四辈祖朝林、甲林、贞林、祥林、金林、成林,到昭通报领鹿柴冲、葫芦坪、宝山、凉水井。(《虎姓登龙祖碑序》)
余祖父兄弟四人,长子甲林、次祥林、三子珍林、四子金林,雍正八年,平服乌蒙,改为昭通,余祖父自杨旺桥迁昭,报领田地。(《虎姓虎龙山祖碑》)按:此为虎姓未曾从军的一支,与烂泥沟虎姓不同。
二世祖撒西昌,历任贵州参将。雍正年,乌蒙叛乱,奉旨征剿,得胜后,病故于威宁下坝。西昌公娶李氏祖母,生三世祖公太吉,吉公娶马氏祖母,生四世祖,长房如玉,住威宁下坝,有七子,二子于乾隆十六年迁鲁甸小黑山,五房住昭通靖安。有四子,分居于青冈岭、大营、鲁脊、高桥。(《撒氏家程》)
四世祖马承璋,由陕西升任贵州乌撒卫中营游府(击);又有族人马文德进士为乌撒守府,与祖同营酌议,俱落业于城北门外。仍选宅茔于下坝、狮子、马金等山安殁(埋)。人烟广众,子孙兴盛,移昭通、鲁甸、东川、宣威、永善、寻甸、镇雄等地。(《下坝马氏族谱序》)
今乌蒙平定,由贵州迁支昭通恩安县城外东、南、西、北,报领土地,落叶生根。(《下坝马姓序谱·总法约录》)
乌逆跳梁,授首归疆。公偕族人拓地鲁邑,爰居爰处,复振声名于荒隅。(《戚大荣墓志铭》)
陕西籍之张姓始祖生三子,长子于雍正年间迁贵州威宁北门外下坝家屯落业。其裔连林、连禄分迁东川以擢河;连琼之后,分迁昭通之龙洞汛、八仙营、桃园、新岔冲。(《张姓谱序》)
李公讳琦,字特庵,素有策略,远近佩服,生长于威宁海子屯,雍正九年,迁居岩洞。(《菁门前李琦祖墓碑》)
又:四世祖乃纷纷迁居昭、鲁等地,领土耕食。(《李国安祖墓碑》)
康熙十四年,公先君以故祖军功将从军,大兵征剿吴逆(吴三桂),以军功驻扎汉中,卒于军。诞生公昆仲三人,惟图公天资超群,倜傥不凡,承受父志,少以游骑,射游西安邑郡……。长象乾,次应乾,康熙四十三年,祖公率二子高祖氏从军,原任贵州威宁镇韩公来镇,随营効用,拔补右营把总,旋补中营千总。雍正年间,効用,拔补中营把总,旋补中营千总。雍正间,树公古州,升都司,特授贵州铜仁府地标,龙头营副将军一第加四级,纪录五次。丕想以从军年迈满弱,由任回威郡,继至昭邑。长君入籍昭郡,复以骑士仕。卒于官舍,葬于马家屯。(《光绪都民军马姓族谱序》)
夷蛮叛乱,雍正九年荡平。招民昭通营业。(松林马《道光诰授武德将军马公讳俊起府群墓铭》)
五世晋伯兮,惟公独传。乌蒙开疆兮,公垦昭阳。成业花鹿兮,因陸陈朴。英雄臣荣兮,四子永昌。三支守鹿兮,臣公离堂。赴鲁创业兮,桃源实往。(松林马《马公再祖婆纳氏墓铭》)按:“因陸陈相”(意思不明,可能系“因庐城畔”之误。
朝珍公,原配下坝马马氏,克偕内助,同入于昭,报领此土方土地。(松林马《朝珍公墓铭》)
雍正年间,乌蒙改土,始祖落籍于白坡塘。(松林马《元位祖公墓铭》)
雍正十一年入昭,报领此方田地,建立清真寺一座。立行教门,经书两全。虑滇少差役繁重,乃以孙晋贤、晋杰之名承载粮册。一文一武,长为昭郡诸生首领,历来不苦徭役,足征年祖先见之明。(松林马《成龙祖公墓铭》)
雍正八年,改土归流,建藩公移鲁甸,拖姑山根脚。成龙公于雍正十一年举家迁高松树。(《松林马姓家谱序》)
本朝定鼎,惟曾祖皆(偕)叔曾祖同来此邦置产,伯曾祖置有此方田地,遂居于此焉。(松林马《道光藩祖公碑序》)
清雍正年,乌蒙开辟,各支□□□□领照,献、秀、先、勲落八仙营大坪子,焜落鲁甸岔冲□□□□□家院子。(《蔡家地马家谱·四世祖支琦分派图考》)
雍正八年,昭邑改土。余外曾祖与外叔曾祖辈,始入昭报领土地。余外曾祖之琦公领出于郡,属八仙营;外曾祖之远、之玙,一领于所罗,一领于天梯、龙头山,而公之祖父之琼公遂乃移居于此焉。(蔡家地马《武仪将军一元墓铭》)
四世二祖公之远乃登先祖之次子,生一子鳞润,清雍季,随族弟至昭落业撮落山。(蔡家地马《大师马家谱历时系统考·鳞、润分派图考》)
这种迁徙运作,对于农民来说,是非常艰苦的。如锁姓的几支人,几乎同时在1728年(雍正六年)就迁入昭通花鹿圈,《锁氏族谱序》只一笔带过。而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五月二十七日立的《皇清待赠显妣母马氏老孺人之墓》碑铭却如实地记下了迁徙的艰辛,说:
余家始在威邑杨旺桥居住。因雍正六年昭通改土,故有昭邑之东名曰花鹿圈,领土三分,粮、册山三项。国贤、永明、永辅继因兵变复回昭邑。未几而蠢蛮复平。又十九年仍归昭邑,料理田园,升科开辟,分拨与侄。粘树囗各管各业,不得紊乱。啟其明也,何知昊天不惠,出威(威宁)身殁,入祖茔安葬。此乃立业之始终也。恐后子孙衍众,不知其田,因立书于马氏族人之墓,永垂不朽云。
从上述所引族谱、碑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前来昭通报领土地的回族主要为威宁回民,其次为曲靖回民;二、威宁回族中的望族大姓如“蔡家地马”、“下坝马”、锁姓、虎姓等人口众多,支派纷繁,其中有些家庭因有军功,而在昭、鲁分配了土地(比较优厚),而大多数则属于招耕时报领土地,不能一概而论;第三、清政府的招耕政策,纯属权宜之计,乾隆登基后,即行停止,未分配的土地作为官府财产,由官府售卖,所以乾隆以后移入昭通回族的土地是向官府买来的,松林马建藩的“置产”就反映了这个事实。另据“都民军马”后裔马鸿凡介绍,他们祖辈移到昭、鲁时,已不能报领土地,大师马(蔡家地马)老主人念在同乡同族之谊,将鲁甸拖姑一片土地送给都民军马姓应乾公长子,以后应乾公长子在昭通“以骑射仕”(任武职),家道又才发展起来。第四,还有许多家族也是改土归流前后移入昭通、鲁的,只是族人分散,没有家谱可稽,有待调查后补充。
第三,经商回民落籍昭通。
乾嘉之际,“时际承平,户口当极蕃衍,况昭属通衢,四方杂聚,庶哉之叹,不让于卫”(《昭通志稿》卷二“食货志·户口”)“昭通入版图较晚(按,此说大误),然以地绾川黔,商贾幅辏,货物殷繁,为滇东商务中心。”(《民国昭通县志稿》)由于地当孔道,所以汉、回各族商人纷纷前来贸易,《民国昭通志》卷六《氏族志》说:
昭与黔、蜀相邻,地当孔道,商贾云集。当其盛时,四城均有当铺及毛货店,均系陕人。在乾隆中,乐马厂大旺,湖广人相率而来,不知凡几。江右人贩运布疋,设号贸易者尤多(谚有遍地江西之说),远及闽粤之人亦闻风蚁附。既来则安居乐业,长养子孙,久之悉入昭籍。
《昭通县志》所说甚是。昭通回族中一些家谱的记载,是这段论述最好的补充:
成福公生子广济、济子有六。来滇之原,延周老祖系济三子。乾隆元年,贸易滇南,来于昭通,开号“同仁”,复来鲁甸,报业拖姑(《昭通米氏家谱序》)
延美之子,原籍陕西,共叔守业。其后大招游落迤西;大方游乐马厂,大名游落威宁,延周六子仍住拖姑。(《显考米公广济大人之墓铭》)
按:“同仁”为昭通城最早的“回回药”铺。“游业”就是经商。
清朝初年,始祖(耀天公)由河西移往鲁甸。天公生四子:金山、金玉、金堂,分居昭、鲁各地。当鲁甸乐马厂大旺之际,堂公到厂办矿,遂得利万金,在鲁甸大开商号,发展资本,并置产拖姑。(《昭通河西马家谱序》)
我高祖朝选公,于乾隆年间,自甘肃秦州盐关假贸易来滇,经东川、落于昭通。见所罗地方土厚地宽,柴方水便,于是置产安居。(《陕西马氏家谱》“九四续编”
客籍马,原陕西籍,后迁居应天府高石坎。始祖芝远公奉命入滇。(曾)任浔阳,(宁)波府事。流传十余代迁居曲靖。雍正元年第十六世祖万遴公移威宁,雍正八年,来岩洞,办乐马烧炼银罐。(《鲁甸县回族志》)
按客籍马狭义指马姓来自陕西一支,后又泛称来自各地并未冠地名以示区别的其它马姓。
城区回族,多属经商之户与仕宦之族,咸同事变前已有近千家,五千余口,全都是雍、乾、嘉、道四朝从外地移入的。在乐马厂开矿的回族矿户,也多半置产鲁甸并落户,故,昭通回族经商的传统能一直流传下来。。
第四、外来伊斯兰教阿訇落籍昭通。
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无论男女老少都严格以《古兰》和《圣训》作为自己的信仰与行为规范,生活与风俗习惯都有其特殊性,而婚丧和宗教活动必须由教长、阿訇主持。为了宗教和生活的方便,一般都聚族而居,并在中心地点建立清真寺。雍乾以后,昭、鲁两地清真寺已有七十多所(昭通市就有四十八所),每所礼拜寺都有阿訇负责教务,开办经堂教育,许多阿訇都是外地请来的:
显考撒公之贤,生于康熙丁丑九月,卒于乾隆戊辰。威宁下坝掌教公之子也。其始祖原籍陕西固原州,望族。明洪武年间奉调南征从戍者。戎平后,籍于黔属威宁,即公之本支也。闻其先公以来,世行衣思了姆(清真),故虽宦游而实能体真主之命,循贵圣之踪……故举之以一坝之掌教。原配祖妣季世,乃生公昆仲七人。公次行,其长昆及众,敬处曲属宣威底母。之兄四,分处威宁之三元山,海子屯。其季兄二支沦没。雍正八年,昭通改土,公乃入昭,创业于此。与此方亲友立以思了母,袭先人之业,为此方之掌教,承领正道之纲维,遂世居于此(马登昆撰《撒芝桂墓铭》
群众十八姓人商议,铁老以嫫推荐,四位乡老到大理官义(按:应为关迤)村家中,请老爸爸传经立教。……到了拖姑礼拜寺,传经立教十二年,乾隆三十二年归回。(《赛老爸爸支系谱序》)
刘氏,置业杨旺桥,传至二世,生四公,长公希璠,娶李氏生八公,五子奇公移于昭通,属白泥井。希贵公生二子,长回跃,次回英,学优教严,移昭通鲁甸大水塘。(《昭通刘氏碑记》)
道光年间,昭通匪患成风,剿压不住,高祖父马祥阿訇暗委以龙洞汛巡官之职,明以传教来到昭通。首至迭马寨,后以龙洞汛为根据地。(马良益《陆凉马来源》)
又据《昭通市回族志》载,昭通、鲁甸甄姓,元祖名甄详,系陕西西河东里寨人,伊斯兰教阿訇。乾隆初年,游学来昭,落籍昭通天砥,开设经馆,传经立教,为著名学者。咸同变乱后,天砥夷为平地,甄姓子孙遂迁移昭通四乡。
昭通回族属伊斯兰教改的母派,清真寺教长或主持教务阿訇实行民主聘任制,三年一届,届满即告退,数百年间除文革期间停止活动外,都有阿訇蝉联,当本地缺乏合适的阿訇时就向外地聘,大理、巍山、玉溪、沙甸、曲靖都有人前来传经立教,最后落籍昭通,成为昭通穆斯林。这也是昭通回族来源的一部分。
第五,回族仕宦人家落籍昭通。
清代,昭通为滇东北重镇,有镇、府两辕与州、县、厅等行政机构,所任官员绝大部分为满、汉、蒙三族,也有少量的回族官员,如合姓,据其族人说本是哈元生将军的后裔,去“口”即为合。此外,马晋琦,四川人,因军功,嘉庆二十三年任昭通知府;赛枝大,青海卫回族,县知事,雍正八年死于昭通;冶大雄,四川回族,乾隆十年任昭通镇总兵;马彪,陕西回族,乾隆二十六年任总兵;马维祺,建水回族,光绪二十三年任总兵,后任四川提督;马镇山,直隶侍卫,光绪三十三年任总兵。中营游击有陕西宁夏回族马秉伦,守备有大和回族马福寿,昆明回族马世兴并马兆龙等,多数家人及家丁也有落籍昭通的,所谓的昭通“客籍马”多半与这些仕宦人家有关。
第六,昭通汉民融入回族。
回族不是以血缘为纽带所形成的民族,而是以伊斯兰文化为共同凝聚力而形成的特殊民族,清代,就有许多汉民融合到回族群体当中。
融入回族的汉民有孔、张、王、阮、冯等姓。
孔姓本山东曲阜孔圣人后裔。明初,有将军孔公锡奉命在威宁孔家湾屯田(《威宁县志》),长期与回族生活在一起。清初,威宁杨旺桥刘吉字瑞祥者,原系陕西西安府午门人氏,“洞习回族《宝命真经》(《古兰经》),长而遨游滇、黔,行抵威宁,为回掌教,适值贵州提督韩将军讳忠征剿乌撒,凯旋还转威宁,屯军杨旺桥。见回教寺院倒塌,传问乡人,俱述人少无力,不克重建。将军欣然允以,代为建造,劝孔姓捐地,搬土运石,以全军之力,积聚为山,元祖绘图建寺,不日成之”(《昭通刘氏碑序》)。据说,孔姓就在这时前后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后嗣以诗礼传家,信仰诚笃,将儒学伦理与伊斯兰教教义有机揉合起来,大大地丰富了伊斯兰文化,也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
融入回族的还有阮姓。《昭通阮姓家谱序》说:
哈元生将军征乌蒙,元公(阮姓始祖)自备征鞍(属乡兵),操戈入伍,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封刚武兄(义)郎之衔。走览乌蒙各地,惟鲁甸拖姑之地适宜。……母子搬迁后,改为阮家院,从此进入光明正教(按:指皈依伊斯兰教)(《阮姓家谱序文》)再按:该族四世祖阮世美为昭通伊斯兰教著名阿訇,被誉称为“阮老爸爸”。
融入昭通回族的尚有鲁甸小冲张姓。该姓祖籍江西井岗山,乾隆时到鲁甸乐马厂开银矿,家业发旺,置产小冲。始祖公三兄弟,伯、仲世守汉规,三弟则皈依伊斯兰教。一家两族,坟山、连在一起,汉族祭祖,回族一支自动交祭奠费用,不参加行礼;回族过节,汉族一支主动道贺。如今回、汉两支族族长为回族张某,该族长已过古稀,银须飘洒,红光满面,在族中有崇高之威望,在回族社会中是少有的德高望重长者。
融入回族的尚有鲁甸大水井回族乡冯姓。据《冯氏宗族谱碑序》称,该族始祖冯朝,祖籍南京应天府柳树湾,元末为红巾军,明太祖朱元璋攻占集庆,冯朝充任军前先锋,世袭百户。正统间,四世祖冯祐随兵部尚书王骥征陇川,因军功陞授副千户,八世祖冯琦授前职,官守备,其后嗣落业于曲靖柳树湾屯垦。十二世祖护送胞姐家小归故里昭通鲁甸黄家山,并落籍。以白银数千两置良田、山林数百亩。遂称作冯家大院子。又经过五代,一场灾难降临冯家,《族谱》说:
世态炎凉,有财有业就有敌。黄氏人别宗亲,歹心遽起,欲侵吞吾祖业,威逼呈出契约,密谋欲将十六世少主墜入深隧。吾祖公开亮年轻聪颖,,胆略过人,忍辱负重,避其锋,星夜潜逃桃源,投蔡家地马姓之怀抱。德高望重之马氏,慧眼金睛,宽厚待人,视吾祖公如子,念开亮公淳厚朴实,胆实过人,将宝千金许配于我祖公,马氏祖婆也。
吾十六世祖公弃汉投穆斯林怀抱,朝日、朝释成为伊斯兰教胞。默安拉之恩赐,娶祖婆马氏,返鲁甸马鹿沟康家院子、营头,新观音寺常住,重振祖业。马氏祖婆育十七世弟兄五人,始祖婆一人迄今以五支系屯居,淳亲共族,故曰冯家院子。
吾祖公默安拉之恩赐,常葆依嫫乃之光亮,不惜财帛资助舍邻,享有积厚培德之美称。
这个由汉而回的冯家院子,虽饱经沧桑,但没有一家杂姓,全族四十余户,一百四十多人,周环十里松林、草坪、緜海,耕地数百亩,有清真寺,有小学,无文盲,也没有吸毒、贩毒、盗窃的犯罪现象,全村生活中上,非常注重科学种田。生态环境古朴,民风淳厚。在世风日下之世并不多见,无论回、汉,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伊斯兰文化对这个山村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汉而回的,尚有“王”姓。这得从“都民军马”说起。雍正四年,该姓始祖马图,官威宁镇标中营都司,在他奉命赴京前夕,为预防不测的事情发生,先立下《遗嘱》一道:
予以俸满赴京觐见,今将驻扎威邑官舍原由嘱言分关事,因交讬而两袖清风。明亮无嗣,有家人一房,草房数间,暂为安身之计。余以年迈,恐日后各支子孙争论,故立分关贰张为证其委。
兄先云生一子,名体乾,俱已完婚,娶媳,各配成室,女出生聘马门。其有家人一房,名曰小四三,系沾益州王宾家人,于康熙五十六年同亲友惠志仁、马兴洲用银二十两买民为仆,又用银十六两作财礼,娶妻陶氏为室。念小四忠勤可佳,故特更名为超用,视义女、义儿。今将买契文一张,会同亲友烧毁。令伊在家照管家屋,各自过日,不得以家人相待。超用所生三女一子,长女分与长子象乾为义女、次女分与次子应乾为义女,暂为押长,日后出嫁,俱为义女相称,不得以家人使唤。所留一子一女,为超用抚养,另自过日。但不得背恩忘义欺主,倘有此情,准其各支子孙执字鸣官,依律治罪。其草房后三间分与侄体乾母子代居,不得变卖,前柒间分与象乾、应乾二人,东西居住,以中为界,不得争论。后有一间,超用安身,不得出外,致超用所关饷银,令伊自用。日后过日,不许哪支争夺,恐后无凭,立此永远分关遗嘱为据。
凭众亲友
白重光、苏国辅、马守俊
任昌华、马兴洲、马公禧
马圣公
代字人惠以仁(笔)
大清雍正四年二月十六日
立永久遗嘱人马图立
按伊斯兰教律,穆斯林都是代主治世的人,所有的人在安拉面前都是是平等的。因此穆斯林不能蓄奴,凡奴隶应即早给予解放,解放后,奴隶在人格上、经济上和其它权利方面与其它人享有同等地位,如果收为族人则奴隶与子女有同样的权利。王小四三一系就在伊斯兰教律和马图仁厚心肠的关照下成为回族的一员。
第七、昭通彝民融入回族
雍正八年,滇东北彝族大起义被清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凡参加起义的各族人无不受到非人的待遇。其中,彝民的遭遇尤为悲惨。绝大部分彝民不在战争中打死,就以“叛夷”的身份*死;一小部分逃过金沙江落籍凉山或者遁入深山老林,恢复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一部分年轻彝女则被官兵强收为妻妾,被挑筋断指的彝民则作为官兵的战利品,继续沦为奴隶。《昭通县志稿》说:“考昭之旧志,四乡分为四十三甲三百三十一村,夷民半。迨后屡遭兵燹,四境之人逃散死亡,所存无几。”较准确的反映了历史事实。
从雍正五年开始,昭通“设流官坐治,而汉人已占多数”(《昭通志稿·人种志》),其中有所谓的“八大指挥”的高级军官,“咸视西南二乡(洒渔、土城等地)其地皆为膏腴,遂占籍焉”(《昭通县志稿·氏族》)。这些军官不仅“占籍”,而且占有奴隶(数量不少),只因“时异势殊,陵谷变迁,求其姓氏已不可考”(注同上)。所以蓄奴的事没有记载下来。“领土占籍”的尚有哈元生将军进入乌蒙的少量的中、下级回族军官,如蔡家地马姓的“名门五桂”,马瑛正四品都司、马炽授正四品都司,马之玙为五品武将军(守备),位在总兵、副将、参将、游击之下(《蔡家地马姓族谱》),但因建立了“军功”,所以除占有部分土地而外,还蒙“浩荡皇恩”,得赏赐彝民为奴隶。蔡家地马姓恪守清真,按伊斯兰教律是不能蓄奴的。但皇恩又不能拒绝,为了生存只有勉强地接受下来。《族谱》记载道:
归登先公为奴的有马鲁者并其子小黑;
归登先公长子之琦为奴的有小僧贵并其子福寿;
归登先公孙鳞辉为奴的有小蛮子、载宝;
归登先公孙鳞瑛为奴的有四寿及其子长宝,马成及其子小麻子;
归登先公孙鳞秀为奴的有小娃。
七品(都司)军官之家就分到奴隶十一名,那么其它都司以上的游击、参将、副将所分到的奴隶数目就可想而知了。
被分配到落籍昭通军官家为奴的彝民,以后情况如何呢?“八大指挥”家的奴隶下落不明,而分配给蔡家地马姓的奴隶则有了明确的交代,即把他们“释入本姓”。登先公耋耄之年果断地还了这一笔“良心债”后溘然仙逝。《蔡家地马族谱·准附宗末图》详细记载了登先公率先“释奴”附宗的情况:
一、登先公准以马鲁者释附本姓,更名马应枝,其子取名马用瑞;
二、之琦公准以小僧贵之子福寿释附本姓,更名马全福;
三、鳞辉公准以小蛮子释附本姓,更名马忠瑞;
四、鳞辉公准以载宝释附本姓,更名马坤瑞(应观公立后);
五、鳞瑛公支内、族内准四寿之子长宝释附本姓,更名马全县;
六、鳞瑛公支内,族内议准以马成之子小麻子释附本姓,更名马全德,此一支列于应选之后;
七、鳞秀公准以小娃释附本姓,更名马全寿。
以上数名皆系尽忠家庭,获长者至喜,真主更转先人(按:更转有醒令、拨转的意思)释入宗姓,族中人等后世子孙,务体良法(按:即体会先人此举的良苦用心),一体相看,不可贱辱。伊等无知,轻慢族中老幼,合族公议以责罚;有坏教规者,通知合族仍复将此人收与族长为奴,切务隐昧矣。
彝族融入回族的尚有松林马姓的几个支系,据《松林马姓家谱》记载:
建藩公孙有元一支,下有“老草人→蛮子→马乖→聪明→马雄→马永”一系,据该姓字辈排行为“运开祯祥、良裕昌程、永崇昭礼”,很明显,马永之前五代不入松林字辈,而老草人、蛮子等名称并不符合回族的取名习惯,颇有汉人称彝人的特点,疑就是彝人,到“永”字辈以后,已与回族没有区别了。
又马晋仕支系下分彦荣、彦文、彦时三支,彦时支下有元宝、二宝、黑贵一系,黑贵自然也是融入回族中的彝民。
又如屏藩祖公下“泰”字支系,咸丰年间从昭通白坡塘绕迁四处到野马海炉罐子居住,其世系为:“草鞋→马广→蛮子”,被称为凉山支系,显然也是融入回族中的彝民。
据父老相传,雍、乾间落籍昭通的回民许多都是只身而来,很少有带家眷的,为了繁衍民族,不娶汉、彝女子婚配人口就不能得到发展,这是《古兰经》和圣训所特许的,这种通融,保证了回族像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没有特殊原因出现,民族是不会凋零的。
根据以上的叙述和分析,可知清朝前期是昭通回族发展的较好时期,现在回族的布局和族姓分布都是这个时期基本形成的。
清朝后期,特别是咸、同年间,昭通回族的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挫折,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有的居民点如天砥等重要地方被夷为平地。为了躲避屠*,许多人逃离昭通,远走他乡。《民国昭通县志志稿》卷六“氏族志”说回族“自遭咸同之变,逃徙死亡不知其数。至承平后,经六十年之休养以迄今日调查(1865——1914)……生齿亦不少,惟其所居之地竟皆瘠薄,竟有衣食难济者。”其实就在号称“五族共和”的民国时期,昭通回族尽管在含辛茹苦地惨淡经营,仍没有改变困难处境,一直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昭通解放,昭通回族开始得到新生,由于没有战乱,五十年间社会安定,回族人口有少量的移动,举族举寨迁徙的情况已根本绝迹。
来源:昭通回族学会
编辑:都市时报一点关注 张丽青
审核:冯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