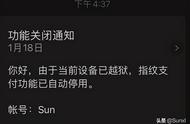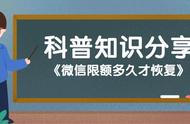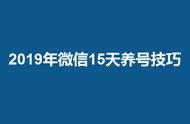今年浙江高考语文满分作文引发广泛争议,评卷组长也受了相应处分,理由是“在评卷结束后未经允许擅自泄露考生作文答卷及评卷细节,严重违反了评卷工作纪律”,对引爆点《生活在树上》倒是不置可否。而社会上有关“文章晦涩多用生僻词”“引用大量名人名言,没有标注出处,没有自己的理解和论述”等批评,窃以为则是毁之太过。
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若是遇上毛奇龄这样的“杠精”,对苏东坡“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句,也能挑出个“鹅也先知,如何只说鸭耶”的毛病。所以说,历来赴考是“场中莫论文”。“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愿朱衣暗点头”一叹,确也道出了千百年来的实情。而今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节骨眼上,偏要出来“炫技”,惹来千万人大逞口舌,陈组长的确是犯了大忌,挨罚也不算冤。
再说苏东坡,当初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欧阳修阅卷后赞不绝口,可文中“皋陶三*”“尧三不*”的“典故”,却让这位文宗不知有何出处,梅尧臣接茬说:道理讲明白了,又何须出处?欧阳修很笃定:“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又言:“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等到苏轼上门拜谢座师,被问及此事,他干脆用三国孔融故事搪塞。既然“苏东坡自造典故,欧阳修青眼有加”能成为佳话,今日又何必苛责一名“引用大量名人名言,没有标注出处”的考生呢?
苏东坡试卷受青睐,也是他赶上了时候。《宋史·苏轼传》云:“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当时就有刘几这样的人喜写诡谲险怪的文句,连试举文章都要来段“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的险句,偏偏遇上欧阳修主考,其憎恶之至,先是批“秀才刺,试官刷”,再用红笔打叉“红勒帛”,犹不解恨,书“大纰缪”三字张榜公布,害得刘几后来只好改名应试。
要说刘几,也真是个人才,史称“知晓音律”“知保州,治状为河北第一”。对于欧阳修的择才好恶,时人也不是没有异议的。欧阳修曰:“除恶务本,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人回应:“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类似“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也有点委婉规劝的意思。
至于《生活在树上》一文,一会儿“海德格尔”“米沃什”“卡尔维诺”,一会儿“嚆矢”“玉墀”“婞直”,虽有人批评这是“佶屈聱牙”,但多少能看出这名考生的文字功底是好的。既然高考是为国选才,这名考生显然也是具备了某方面的才识,其作文纵然谈不上“满分”,也不至于被人轻诋若此。中国汉字有9万多个,但常用字只有3500个左右,某些人看不懂的未必别人就不能用,不然还要编什么《辞海》《辞源》?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071万,若按评论者大言“写文章就是说话,用浅白的语言把问题说清楚说透”的单一标准,几人能显个?照我理解,《生活在树上》的作者实为出了“剑走偏锋”的险着,没准是个“刘几”式的奇才?!
所谓应试,自有不得已的对策。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刊《拒绝当一个标准产品》的报道,说记者老陶的女儿陶雨晴被香港浸会大学录取了,“应该是写作特长起了作用”,还探讨了“高考使几乎所有人都很难受甚至是痛苦”“孩子的天赋,到底有多少值得维护发展的价值,家长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和体制的矛盾”等问题。即便是这个曾被学校逼着去看心理医生的“问题孩子”,也多少有些应世之举,问她“今年高考作文《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咋写的”,原来是考试前准备了一套东西,不管什么作文题,都可以套进去,能引申上去,“语文一共考了123分,作文分肯定不少”。
前些年,中国教育在线总编陈志文发文《高考作文到底在考什么?》,内有“高考命题是一个专业问题,真不是谁都可以给指导的”一句,又说不妨少些“炒作与口水”,而为“让高考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考试,更为科学,更为公平”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些话于今细品,愈觉有味。
马二先生说:“到本(明)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在选才制度面前,孔夫子尚且无奈,今人又何必求全于一名高中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