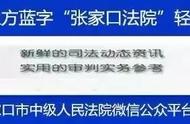真正的艺术品是永垂不朽的,但对艺术的解释却是与世推移、永无穷尽的。当代作家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多年来一直是中学、大学语文教科书上的必选篇目,但对它的阐释则始终局限在“歌颂人民战士”,“表现军民关系”这样一个单一的角度和肤浅的层次上;颇具权威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学参考书》上这样讲,无数个教师便如此教,似乎《百合花》有这样几个概念就“盖棺论定”了!
其实,《百合花》作为一个艺术品,它的思想、艺术内涵是颇为丰富的、复杂的,必然深藏着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能用一、二个概念就把它囊括殆尽,那么它就绝不会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我以为,这篇作品的深层内涵和艺术价值,在于表现了一个稚嫩而蓬勃的生命在严酷的战争中的悄然消失和毁灭,作者谱写了一曲纯真、深情的青春与生命的挽歌。正是这年轻生命的毁灭和作者那种不无“感伤”的情感流溢,构成了作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恒久的艺术魅力。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观照、品味《百合花》的话,我们对作品的思想内涵、人物塑造、艺术手法等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庶几才能较准确地把握住这篇作品的艺术核心所在。当然这样的解释也只能是向作品的艺术深处挺进一步,并不可能穷尽它。
我们很习惯于概括一篇作品的所谓主题思想,并常常是站在社会功利的立场,来判定一篇作品的价值。其实,一篇真正的艺术品的思想内涵,往往是多义的、多元的、深层的,很难让人一眼看透。在高中语文《教学参考书》中,《百合花》的主题思想被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塑造了通讯员和新媳妇这两个平凡而又感人的人物形象,歌颂了他们为革命甘愿献出一切的崇高品质,表现了军民之间和革命同志之间纯洁真挚的深厚感情。”这一作品的主题概括,其实只触及到了作品的基本故事和表层意义,离作品的深层内涵还很遥远呢。主题思想往往被看作一篇作品的核心和灵魂,我们的眼光既然被束缚在这样一个表面层次上,那么我们对整个作品的认识,就势必要简单化、功利化,从而远离了作品的艺术本质。我们知道,作品的思想倾向,是从作品整体情节的深层结构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的,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往往不为作家的主观意图所左右。乍一看,《百合花》是写了一个年轻通讯员的英勇献身,是写了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纯洁真挚”的军民感情。但细细看去,我们就会发现,如上所述的故事和内容只是一个表象而已,作品的深层结构则是由这样两条轴线构成的,一条是作为故事背景的一场攻打海岸的激烈战斗,一条是一个年轻可爱的通讯员的死以及这个小通讯员在两个青年女性心灵上激起的心理波澜,——写两个女性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反衬小通讯员。这两条主线像两座峰巅,在作品中巍然耸立,越垒越高,构成了作品的独特造型。尽管作家没有正面写那场战争,但战争的紧张气氛、刀光剑影、血与火的拼搏,却在整个作品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弥漫着。就在这样一幅硝烟滚滚的大背景上,那个青春焕发、刚刚涉足人生的年轻通讯员却像一颗流星一样,倏然消失和毁灭了,只在那个文工团团员“我”和新媳妇的心灵上,留下了难灭的印象、强烈的震惊和深深的怀恋。透过这种对比强烈的情节和作家饱蘸感情的描叙,我们当然可以感受到人民战士的崇高品德、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但我们不是更能感受到美好的青春与生命被战争毁灭的悲惨情景吗?作者越是把小通讯员写得纯朴、真诚、稚嫩,我们就越感到青春与生命的鲜活与珍贵,也越感到战争的严酷。尽管正义战争是无可非议的,我们的作家也不会像西方作家那样具有反战情绪,但不管是任何战争,都要毁灭生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讴歌人的青春与生命,揭示人在战争中被毁灭的情景,哀悼生命的死亡,我想也是无可指责的吧?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与许许多多世界文学名著相通的主题,我想这正是这篇小说具有隽永的艺术内涵的奥秘所在。
从这样的角度把握主题,不仅有作品的情节可作依据,同时从作家的创作谈中也可得到印证。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载《青春》1980年11期)一文中,作家几次谈到她在战争年代那简陋的包扎所工作时的深切感受:伤员一个个从前线抬下来,“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我就着天上大个儿的圆月,翻看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止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若干年后,那些生龙活虎却突然死去的战士的形象还深印在她的脑海里,“他还只刚刚开始生活,还没有涉足过爱情的幸福。……我当时主要想的就是这些,至于主题是什么,副主题又是什么,主要事件又是什么,我都没有考虑过。”由此可见,作家创作这篇小说时,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一些左的创作思想和模式的影响,但她并没有完全从理性化的角度,去全力表现什么人民战士的“崇高品质”、“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而是从生活出发,从感性出发,去表现那些年轻战士在战争中的猝然死亡,表达她对他们的痛惜、哀悼之情。作家在这样的心境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其思想内涵就必然是模糊的、多义的、深层的、带着感情色彩的。
作家的思想感情倾向,直接影响着他的人物形象塑造。语文《教学参考书》在概括《百合花》人物塑造的特点时说:“作者运用典型化的方法,使通讯员和新媳妇这两个人物既概括了我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所具有的共性,又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做到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达到了典型的高度。这是肤浅的主题概括下的产物,也是对典型化理论的生搬硬套。《百合花》作为一篇富有“抒情诗风味”(茅盾语)的艺术品,它的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情感性和抒情性。它的主题并不深沉、新鲜,只是由于作家情感的深厚和真挚,才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变得深远、广博起来,——这也许是作家创作时始料未及的。它的人物塑造,也不见得有什么高超之处,更谈不上达到了典型的高度。严格地说,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是三个“扁型”人物。但茹志鹃在人物塑造上自有她的“拿手”之处,这就是她充分展现了那个小通讯员的青春、生命之美,三个人物的人情、人性之美,使她笔下的这三个类型化的人物,带上了某种象征、诗意的色彩,产生了一种蕴藉、优美的审美效果。
那个连姓名都没有的小通讯员的形象,塑造得确实是十分感人的,他的年轻、英俊,似乎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像一株挺拔的嫩竹子。青春正悄悄地萌发,但自尊和腼腆的性格,使他在年轻女性面前变得更加局促、羞怯,努力避而远之。他纯朴、执拗、坦率,当他借被子遭到新媳妇的拒绝后,他骂她“死封建”,对新媳妇的转变傲然不理,但当他得知真情后,又后悔不已,坚持要把被子送还人家。他对同志真诚、细心,对上级的任务尽心竭力,对革命事业充满献身精神……小通讯员的这些性格,在作品中描绘得精细入微、栩栩如生。但是我以为,如果从独立的单个人的性格世界来看,这些性格特征还很难说是独特的、深刻的、丰厚的,它更具有一个年轻战士的共性特征(类型化性格)。这里妙就妙在作家是把这些性格特征作为青春与生命的一种表现、一种象征来写的(作家也许是无意识达到了这个层次),使读者在作品中感受到的,不完全是这个小通讯员鲜明的性格,更多的是这个年轻战士那种蓬勃、美好的青春与生命的魅力。把这个年轻的生命放置到那场血与火的大战役的背景上,我们才深深感受到了那个年轻战士青春与生命的短促、珍贵和辉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小通讯员的形象,是诗意化了的青春与生命的象征。
《百合花》所以具有那样浓郁的艺术魅力,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品中那个年轻通讯员与那两位年轻女性之间构成的那种纯洁、美好而又微妙、含蓄的关系。我们当然可以从同志之情、军民之情这样的角度来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作品的表现只限于此,我敢断言,它会像当时无数表现战争题材的小说一样,被人们忘在九霄云外。作家曾经坦率地承认,小说“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颂歌”。作家对两位女性的身份、性格等的设计是颇有深意的,她们同那位年轻通讯员的矛盾、纠葛也是很有戏剧性的。文工团员的“我”,大方、爽朗、机灵,与通讯员的年龄不相上下,且又是同乡,在战场上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邂逅相遇,自然会在心灵中产生许多共鸣、好感。从上前沿一路“竞走”和对话的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而且“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小通讯员呢?从他对“我”的躲避、关心、留馒头等细节中,也可看出他对文工团员的好感和喜爱来,两个青年男女之间这种潜意识的流露,正是青春与人性的一种自然表现。当然我们还不能把它说成是一种爱情,但确实是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我们亦可把它称为青年男女之间的一种爱欲。茹志鹃在谈到塑造新媳妇时说:“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我写<百合花>的经过》)其实作家只道出了个中奥秘的一面,一个正沉醉于爱的新娘子,与一个青春勃发但还没有涉足爱情的年轻战士,自然可以形成强烈的反衬,使我们对小通讯员的死产生痛惜之情,但二者之间就没有一种情感的碰撞和吸引了吗?我想是有的。一个处于爱情之中的少妇,心里蕴满了幸福与甜蜜,她的心理也是很微妙的,她会觉得所有青春焕发的男子都是可亲可爱的,特别是对于通讯员这样一个朴实、英俊、腼腆的小伙子,她会对他投去更多的关怀、爱怜之情。而一个小伙子在新媳妇面前,也会感到爱的博大,分享到一种爱的甜蜜。这种情感的交流,虽然是在潜意识深处进行的,但人们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体验到它。作者凭着她那女性特有的细腻、敏锐的感觉和情感,把这一切微妙的心理都表现了出来,才使那种直观的军民关系表现得如此丰富而动人。是的,虽然刚刚开始生活的小通讯员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离开了人间,但他也得到了些许纯洁、温馨的爱,使读者那痛惜的心灵得到了一丝安慰。青春与生命在战火中得到了永生。
《百合花》是一篇烙印着深刻时代印记的作品,更是一篇蕴含着作家艺术才气的作品,我们只有抛开陈腐的教学思维模式,沉潜到作品的思想艺术深处,才能真正认识、把握这篇作品的艺术价值。
作者:段崇轩,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文章来源|国文锋语
编 辑|古 月
校 对|智 齿
责 编|鹃 子
副 主 编|温 鹃 常 璐
主 编|李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