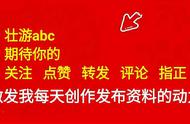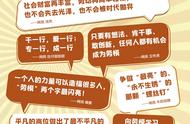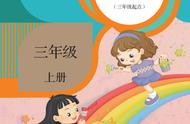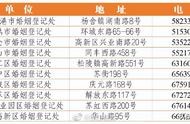柳鸣九在北京大学期间。
一个“小小西西弗斯”
我生平拥有很多热心的读者(今称为“粉丝”),其数量恐怕是相当之大,仅主动热情写信的、索取签名的、索取赠书的、索取“墨宝题辞”的就不计其数,在我风华正茂的时候,还曾得到过不止一个红颜读者的特别青睐,其中有一位某个大城市的大学生特别令我难忘,她的热情显然超出了一般读者,她的聪慧与才能也给人深刻的印象,她不仅来信倾诉读书心得,寄来她所描绘的萨特素描,而且还赠送过感人的小礼物……我视热心读者为我的上帝,备加珍视我与他们的纯粹神交的关系,一直恪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对他们索取签名、题词、赠书的要求有求必应,而且在赠书方面格外慷慨大方;另一条是,从不谋面,力避谋面,以效钱锺书“母鸡能生蛋即可,何必让它见人”一语之智慧,即使与上述热心的红颜读者也仅限于纯文化的神交,终未见面。
但在前几年夏天,不见读者的规矩,被我打破了一次。
事情是这样的,有位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位姓朱的热心读者,此君早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在一家银行任中层干部,是一位真正的“法兰西文学之友”,专门收集有关法国文学以及法国文化的书籍,藏书品种之齐全、藏书数量之巨大令人惊奇。他托人向我转达一个要求,希望我为他所藏的一部分“柳氏文化学术产品”签名,我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考虑到他这种兴趣已发展成一项藏书事业,而且已经达到了一个专业图书馆的规模,值得大力支持,又考虑到他要求我签名的书并非区区小数,而是相当大一批,我便索性慷慨到位,玉成其事,约他把要我签名的书带到我常请客的那家陕西餐馆,而且因为凡是法国文学的书他都收集,所以由我作东邀约罗新璋与谭立德两位老友也参加,让朱君把他们两位的书也一起带来。到时候,四位都如约而至,朱君开车载了好几大箱书,绝大部分都是柳某的“劳动产品”,于是,在一个包间里,享用这家的招牌菜葫芦鸡之前,我们三人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总算帮朱君完成了他的心愿。
说实话,我即使只在每一本书上签一个名,总数好几个纸箱的书要签完也是一项“体力活”,何况我握笔的右手已归“帕金森氏”所有……书摊了一大桌子,我每签一本,朱君就把它们在墙边摞上,一本一本添加上去,最后,朱君把我签完了的书全摞在墙边,其高度达到了一米八九,据朱君称,他只带来了他的一部分“柳氏制造”,还有相当一部分,实在不好意思全都带来……至此,罗新璋君按他每逢聚会都要摄影几张的习惯,又掏出他的精巧相机,朱君当然也带上了自己的相机,两人都“咔嚓”了不少张,靠墙而立的那一大堆书自然在拍照之列,几位友人也一定要我站在那一堆书旁边,为我拍照留念。我从来都自称是“矮个子”,实际身高仅一米五九,墙边那一堆书的高度,显然超过了我本人,算是以最低达标程度印证了我是“著作等身”。这张照片后来流传到了网上。
除一个“著作等身”的评语鉴定和一大群读者粉丝外,还有我在文化出版领域中所拥有的广泛人脉,这绝不是靠请客吃饭、施惠送礼、拉帮结派、讨好卖乖、曲意逢迎等世故俗套的方式所赢得、所建立的,所有这些世俗方式恰巧是我最不擅长、最不适应、最无能为力的,而且,即使我有这份才能,我也没有这些世俗方式所必须依仗的权力加地位与财富等“硬件”。
我在文化出版领域人脉形成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是《法国文学史》《萨特研究》“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70卷)、《世界短篇爱情小说选评》“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西方文艺思潮论丛”等产品在社会上取得较为轰动的效应,其学术文化观点与独特的出版创意给了读书界与文化出版界深刻的印象,加上我又在“共鸣”问题全国性论争、批日丹诺夫论断、为萨特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等文化学术事件中扮演了主角,全国文化出版界恐怕都已熟知我的名字,并开始对我建立了文化学术的信任。随着人脉的广延,学术文化项目一个接一个地纷至沓来,委托给我,于是,又陆续有一大批主编项目成果成功问世。发展到这种局面,人脉已经不需要去刻意建构疏通,而是自动延伸,派生繁衍,而我则坐收其效。到了退休以后,国内出版机构登门拜访的老总与编辑人员仍络绎不绝,诚邀力约,委以重头的项目。幸亏我离老年痴呆还很遥远,脑力尚充分够用,居然也做成了几件令人瞩目的事情,主要有“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已出21种)、“本色文丛”(已出34种)、“外国文学经典”(已出60卷)、《世界诗歌经典作家》(20卷)、“世界散文八大家”(8卷)、“世界名著名译文库”(87种)。

《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从已出成果的项目来看,我的工作范围已经从我的本专业扩到了整个外国文学领域。如果说我在组织本专业的大型项目时以自己已有的地利人和之便而得心应手、顺利通行的话,那么,有的项目跨出了我的专业学科范围,便面临着“人生地不熟”的问题了。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问题都相当顺利地解决了,解决方式很简单:我需要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专家或其他语种的学者、教授、译者合作时,一般总是写一封诚邀的信件或打电话,对方是我所敬重的、心仪已久的,同样,我也是被对方所熟知的,只要互报姓名,合作几乎成功了一半。这种情况似可谓人脉自通,但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合作,往往是项目已经作成,而双方却一直尚未谋面,我与不少文化名家的关系都是如此,如在“本色文丛”中与邵燕祥、李国文、刘再复、韩少功、陈建功、钟叔河、流沙河、止庵、毕飞宇、肖复兴、王春瑜、屠岸、蓝英年、潘向黎,在“世界名著名译文库”中与英美文学专家孙致礼、殷企平、吴钧陶、方华文,与俄语翻译家臧仲伦、徐振亚等。总之,人脉就像一个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
我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草根学者,我只是要做书、编书,为了做书、编书,我有这点人脉就足够了。在浩瀚的学海中,我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不过是萤光之一闪;在辽阔的时空中,我不过是一根速朽的芦苇……
先哲加缪在他的名著中曾留下这样一则隽永的寓言:众神为惩罚西西弗斯,判处他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由于本身的重量,巨石总要不断滚下山来,西西弗斯又得把石块再推上山去,但见他全身肌肉紧绷,脸颊紧靠巨石,肩头死扛,腿脚硬撑,双手竭力前推,如此反复推石上山,永无止境……
西西弗斯不幸吗?加缪答曰:不!他是幸福的,因为他经历了过程,体验了奋斗的艰辛与愉悦,攀登山顶的拼搏,足以充实一颗人心……
我没有西西弗斯推石上山那种悲壮与坚毅,但我也是推石上山者,算得上是一个“小小西西弗斯”,既然毕生干此营生,在回顾一生的路的时候,就不妨审视一下我推的是什么样的一块“巨石”?它究竟有多少分量?我究竟把它推到了什么样的高度?我推石上山的力量是什么?力量的源泉何在?

1981年,柳鸣九在萨特墓前。
所推巨石的三大板块
我往前推的这块“石”的第一大板块是文学史研究。我是学外文出身,毕生都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桥”上讨生活,其劳作基本性质不外是“搬运”或“转运”,在中国干这一行的人为数并不少,区别就看怎么干、*规模与*技艺水平了。中国人往往把在桥上做文化学术转运工作的人,统称为翻译家,其实,桥上转运者的劳作远远不止于单纯意义上的翻译,翻译仅为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劳务还有普查、探寻、发现、发掘、研究、鉴定、分析、阐释、说明、介绍、评论,这些劳作可归结为学者劳动,这种劳动不仅需要外语能力,而且需要明智的思想辨析与深刻的思考钻探力,需要对各国文化有全盘认知、互通处理的智慧,其整体的艰辛程度不下于单纯的翻译,但没有翻译那么容易出活,那么立竿见影。我所从事的正是学者劳动,其劳动成果主要就是文学史论著。我作为首创者、组织者、主编与主要撰写者,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多卷本国别文学史专著《法国文学史》,以充足、翔实的资料,比较全面介绍与论述了法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写得甚为用心用力,历时十几年,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
文学史研究是我学术文化的立足点,站在这块坚实的场地上,不仅自然而然结出了其他一些评论著作的果实,如《走近雨果》《自然主义大师左拉》《超越荒诞》《从选择到反抗》等,而且派生出、繁衍出、带动出我整个的“编书业务”,从小到大,从法国文学到整个外国文学,像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最后达到了“卷帙繁多”的浩大规模。

《法国文学史(全3册)》,柳鸣九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
我往前推的这块“石”中的第二大板块是理论批评。我对理论并无天生的兴趣,我也并非素来擅长于逻辑思辨,我投身于此,仅仅是因为我大学毕业后最先是分配到文艺理论工作岗位上,理论批评自然而然就成了我的分内的职守,有点“先入为主”,在这个领域,我才得以从开端到有所作为。其中的某些作为,尚不失为令人瞩目的“学术事”“文化事”,如1950年代,以一系列颇有规模的论文引发出全国性的“共鸣”问题大论争;“文化大革命”后,又以一系列大篇幅的檄文,而率先切中要害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改革开放之初,以“三箭连发”的锐势,对长期统治中国文化界的日丹诺夫论断揭竿而起;继而又以《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和《萨特研究》一书发个性自主的先声,引起了全国学界的关注……
我向前推的大石中第三个板块是散文随笔写作。我对写作兴趣是早已有之,只是深感时间与精力不足,笔头亦不健,不敢轻易跨出一步。我打破这种保守状态是在1981年访问法国期间,在那次学术访问中,法方热情帮我安排了与一些知名作家与学者的见面访谈,他们几乎都是已享誉世界的人物,如尤瑟纳尔、西蒙娜·德·波伏娃、娜塔丽·萨洛特、罗伯·葛利叶、米歇尔·布托以及皮埃尔·瑟盖斯、克洛德·伽里玛等。
从一开始,我就感到机遇极其难得,这些高规格的约见,不仅满足了我“有幸一见”这些我仰慕的作家的虚荣心与自得感,而且必然会给我的研究工作带来丰富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只要使用得好,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有此思想预期,我每次上门去拜访时,都不厌其烦背着一台笨重的录音机,一手执笔记本,一手执笔,样子着实有点可笑。虽然风度欠佳,所幸我在法国文学方面至少还是一个“有准备的人”,是一个能进行对话交流的人,何况这些访问有老同学金志平君同行,有正在巴黎大学念博士的沈志明君协助,因此,每一次都甚为成功,得到对方认真、热情、友好的回答。我获得了我所切望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由世界第一流作家亲自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如此丰富,如此珍贵,如果不好好写些东西出来,那就太可惜了,太辜负这一次次费时费力又费心的访谈了。在我的构思中,一本书如果以这样特定的学术文化的“干货”作为基础,加上个人独特的印象与心理性格描绘,再加上若干花絮性的细节记述与比较感性、比较生动、比较洒脱的文字风格,必定是一本有学术文史价值同时又为人喜闻乐见的书,而这本书的题名可定为《巴黎对话录》。这便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