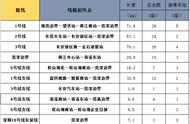在内蒙古草原,悠远悲美的马头琴、粗犷苍凉的蒙古族歌曲是多数人对内蒙古音乐之美的普遍认识。但是蒙古族独创的民粹文化中,“呼麦”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更是悠远中的悠远,悲美中的悲美。

有关呼麦的产生,蒙古人有一奇特说法:古代先民在深山中活动,见河汊分流,瀑布飞泻,山鸣谷应,动人心魄,声闻数十里,便加以模仿,遂产生了呼麦。从呼麦产生的传说以及曲目的题材内容来看,呼麦是当时蒙古山林狩猎文化时期的一种艺术产物。
“呼麦”,蒙语名为“浩林·潮尔”,“浩林”即咽喉之意。“潮尔”有“琴”、“和声”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喉琴”或“喉中和声”的意思。这种“喉音”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它运用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个人同时唱出两种声音,形成罕见的多声形态。

可以想象,金色圣山,苍鹰掠过,在无尽的草原上,残阳如血,马群长嘶,一群身着各色蒙古袍的人们围坐在牛粪篝火旁。焰烈膛红,四野绵绵。在一曲幽怨悲怆的马头琴之后,一个身材高大的蒙古族小伙子,开始从喉咙的最深处,发出史上最低沉沙哑的唱吟。
以蒙语发音的呼麦声音类似人类在最沙哑、最干涸的状态下,以喉咙和头腔共振产生的深度岩层下的地质嘶吼。旋律和曲调接近藏传佛教中的喇嘛清晨诵经,在沉郁幽森中投射出宗教音乐的神秘之美。
几乎没有多少汉人能够听得懂他在唱什么,几乎没有多少人听不懂他的心声是什么。呼麦如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作品,没有精准的写实临摹,却有精深的色彩意境,它穿越视觉和听觉的浓重表象,直达诉求者的内心最深处。
“呼麦”在内蒙古草原曾绝迹了100多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优秀的蒙古族音乐工作者通过引进和修复,逐步开始将这门独特的民族艺术唤醒,并引入音乐的高等学府殿堂。
长调的悠扬委婉,马头琴的如泣如诉,呼麦的深沉玄鸣钩织出内蒙古草原音乐民俗文化的原生意境。那悠长的声音中透露出的是沧桑,是忧郁,是辽阔旷野上寂寞惆怅的感觉。他们唱着马,唱着鹰,唱着草原,也唱着爱情。在这个歌的海洋、酒的故乡上,狼行穿越,马步奔腾。

世界上很少有这样一个民族,穿越700多年的马背征战,颠覆东西方农耕文化的种种窠臼,在曾经的*戮和血战中,在雪域高原、牧草荒漠的历史频道转换中,在连接多瑙河文化和黄河文化的酣战屠戮中,孕育出如此静谧深邃,旷远悲怆的音乐艺术,在铁马兵戈的“大动”中,创造出孤狼望月般的“大静”之音。
这,也许就是永远说不尽理不清的呼麦艺术魅力,是对大自然原始、野性生命的挚爱,对历史感、宿命感的音乐诠释。
呼麦,大草原的深喉,蒙古族的心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