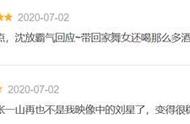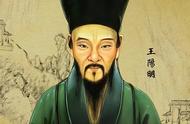老人送我一本《张培林画集》,我一有空就翻看,无法把充满激情的作品与眼前言谈举止都小心翼翼的老人联系起来,我试图找到其中的原由,对我而言,张培林是个谜,我也同样需要小心翼翼揭开谜底,寻找答案。历史是个小姑娘,有话语权的人可以随意打扮她。历史也是个金矿,你不发掘不探寻,金子是不会主动跳出来的。
和一般画家的画册不同,在张培林的画集后面,有他的《自传》和《给赵荆的信》,这些文字似乎为读者更进一步了解他作了注解。
通过这些文字,他坦诚地回忆了一个爱好文艺却身陷贫困、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所经历的一切。这些文字述说了一个画家生活、学习、思考和创作的经历。
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和艺术生涯做缜密的回顾与反思,这样的文字出现在画集中,本身就是不多见的现象。有的画集也有类似的文字,大多是自我介绍,自吹自擂,泛泛而谈,不知所云,对于这样没有个性与思想的文字,许多读者也是一掠而过的,然而,我却无法绕过张培林的这些文字去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他的经历颇为特殊,却也印证了我们苦难的民族所走过的道路。他小学没有毕业,却喜欢文章绘画,因为这个爱好,被选送至省城艺术干部学校做短期美术培训。在省城,他头一次见到电灯泡,困惑于发光的钨丝,时时对着电灯泡枯坐发呆。由于勤奋的学习和突出的成绩,被学校校长力群赏识,力群放言:“咱们学校培养出个小画家”。他爱编写戏曲段子,也曾经写过小话剧,客串角色。然而,在1957年开始的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风暴中,他未能幸免,他被打成右派,他编写的戏曲中反动分子的言论被当做张培林的言论,成了张培林右派的罪证。于是他被当成管制对象,参加村里的劳动。每当村里的高音喇叭响起,他便紧张起来,即便这样,村里、公社和县里要搞宣传,还会有人想到他。从这点来说,他还有些利用价值。通过村委会,他被调到各个单位按照人家要求,往单位的照壁上画《*去安源》和忠字图案,单位按照每日两块钱的报酬支付给随张培林一道来的副业村长,村里再给张培林记十个工分。偶尔遇见好心人,也会避开副业村长给张培林点“小费”。
曾经张培林推着借来的自行车,夹着一卷白报纸,到离自己村子三十里地的偏僻小村,按每幅二斤玉米的价格给村民画些中堂,画些吉祥图案,一天下来,赚得的玉米足有百八十斤。好歹翻山越岭把玉米推到家里,可还是让革命群众举报。村委会知道此事之后,组织对其的批斗,罪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在这样度日如年的生活中,他也坚定地相信未来,他没有丢弃手中的画笔,田间地头,他画,饭前睡后,他画。他就好似从自行车上滚下的玉米棒子,滚下来再捡起,捡起再滚下。忍辱却不屈。
他的坚持有了盼头,终于,1978年,他重新获得名誉,回到工作岗位。
兴致勃勃地在县文化馆干了几年,仍然不改性情,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县文化馆要说地位不高,可是在县里,却相当于国家的文化部。他的举动最后招来了闲人的琐议,导致领导的不满。于是索性辞职投身到北京画院王文芳先生门下,开始正儿八经地学习中国山水画。那年,他已近五十岁。何以选择山水而避开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人物画?经历过政治风雨的张培林认为,画山水画相对“安全”。这种当下看来奇特的理由,却是张培林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无奈的选择,也是当时文学艺术从业者所面对着严峻现实。

然而这短短两年的学习,却为他以后的艺术之路奠定基础。对五十岁的人,是没法一板一眼教其技法的,恩师王文芳鼓励他:“你大胆地画!”于是张培林在宣纸上开始了笨拙却充满激情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与校正,摸索与探寻之后,张培林的作品逐渐呈现出强烈的个人面貌来。他也逐渐找到了使自己心灵悸动的精神元素,并努力地把其表现出来。
研修结束,同班同学一起开了个画展。张培林的前言只有十个字“我从山里来,还回山里去”。朴实无华的语言和充满激情的画作吸引着每一个参观者。如其所言,张培林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留在北京,而是回到了家乡。
对于北京甚至太原来说,山西晋中的和顺县其实是太偏僻了,可是他却毅然决然地回去了。这里不只有他的家庭,更有他的记忆。城市对于他而言,是陌生的,繁华对于他而言,是暂时的。他离不开生他养他的太行山,他自信能从中找到新的精神之力,创作之源。可是这也意味着孤独与寂寞,甚至被人遗忘。这情形其实是有些悲壮的,注定了他要在孤独中成长,也注定了他的艺术创作是充满了自信和感人的力量的。犹如高更离开了证券交易所到了荒蛮的塔希提岛,是放逐也是回归。结果是不可知的,但孤独却是必须忍受的。
当他站在家乡的山上时,一种久违的感情涌上心头。这样也好,他离开了城市里所谓艺术圈的喧嚣与浮躁,可以平心静气地直面山和水,直面自己的心灵,也可以认真地画好每一笔。面对着白纸,他开始了创作。
一年之后,当他携带几十幅作品在省城展览时,立刻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山沟里出了金凤凰”有人这样评价。
不是没有留在省城工作的机会,但是张培林清楚地知道,他离不开太行山。在省城办完事情,他又转身回到了和顺。
正如张培林当年在北京画院结业展中所说的那样“我从山里来,还要回到山里去”。他把这句话朴实的话语作为誓言,远离城市的喧嚣,二十年如一日,他在太行山区偏僻的县城里,埋头作画,注视着眼前的山,关注着自己的灵魂,在宣纸上苦心经营,寻找着灵魂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从学习绘画,到自由表达,张培林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他是笨拙的,却也是真诚的。


一、看张培林的画,只看一幅是不行的,必须看全部。因为一幅不足以反映其探索求真的艰辛历程,不足以知晓其奋斗挣扎的蜿蜒心路。几百张作品首尾相连,浑然相契,自成一部磅礴大气高潮迭起的长篇小说,一曲蜿蜒悱恻欲舍不能的交响乐。
大凡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内心与表达应该是一致的,人们从他的作品中,读到了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比如鲁迅,比如郁达夫。内山完造在回忆鲁迅时说,鲁迅写作的特点是从不隐瞒或掩饰自己的观点,有什么想法就写出来,就发表。如果将来发现有些观点错误,以后再修正。从这方面来说,这也是鲁迅之所以成为一代文豪的原因之一。作品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其实是他全部生命的副产品。
二、从1986年开始,张培林的作品便呈现一种自有的特色来。他的画不大追求表面的笔墨韵味,而是企图通过画面表达精神层面。即使是小品、习作,也似乎努力地想挣脱笔墨的束缚,竭力地想寻求一种精神的出口,灵魂的寄宿之所。画面上的石头、山脉、流水和小屋孤独却有力,执拗却坚强。即使是以太行山为创作母体,他也不太拘泥于太行山的外貌特征,而是述说山的灵魂和精神。观者看到的不是对太行山的自然描述,而是作者难以安静的心灵。
三、张培林的绘画主题是太行山,和那些背着画夹写生的艺术学校的学生和城市里的专业画家不同的是,作为山的儿子,他真正懂得山的语言,知道山的哀愁和兴奋,同时更清楚自己的哀愁和愉快,他知道山的不屈和挣扎,也更清楚自己的表达和渴望。于是在他的笔下,那些被人司空见惯的山脉、水、树和杂草有了呼吸,有了生命,有了承接往来,有了生死契阔。
凤凰涅槃,是从火里得到再生。如火如荼的岁月没有摧毁他,把他变得渺小,反而锻造了一个艺术上无比创造力的人。表面的唯诺是时代的烙印,似乎表明那个时代的胜利,可并不代表他内心的无力,他通过作品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更为强大的自己。从这方面来说,他其实是胜利者。一个真正的画家,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将永远知道自己表达着什么。
四、画册中,这些大大小小的画作按创作时期被分组,被冠以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犹如组曲,跌宕起伏,反应了作者于太行山题材的不同探索阶段。张培林因为避祸,选择了山水画的创作,但这并没有使他走向风景画家的道路,相反,他从另外的侧面和高度更加关注人的呼吸的命运。看看这些画作的小标题吧。
(一)亲吻笔墨1986-1989(萌动、寻觅中的宣泄、旧题新咏);
(二)墨的诱惑1988-1991(生命的执著、寰宇恩泽、山与水、心灵空间、被遗弃的图画);
(三)谧谧灰调1992-1994(鸦鸣远去、心路遥遥、倔强闪烁、炕头诙谐、诡诘梦幻、孤独者的思考);
(四)久违的红色1994-1998(飘动与滞留、记忆中的院落、畅怀、虔诚者的守候、寥廓天际、心象的位置、怪诞的错位);
(五)小品百味1993-2000(留的空白好走路);
(六)戏闹五彩1999-2003(缠绵唏嘘、风景、啊,迟到的金色)
五、《迟到的金色》组画,就名称来说,可谓恰到好处。金色的山峰,如高速行驶的巨型火车,通体透着刺眼的光芒,无所畏惧,穿过幽暗漫长的悲苦岁月,不再哀伤,不再忧愤,突兀却急速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六、传统的中国画讲求文学性,表现为题诗、闲章、书法、章法布局互相呼应,画面讲求造型的生动、笔墨的韵味和黑白的处理,追求文字对画面的点题和深化,文学更多时候表现的是画家的审美趣味和综合素养,在画面上体现文人综合素养,是许多中国画家的毕生追求。
而张培林的画面却是不着一字,其实是有意为之。在他的画面上很少甚至没有传统书画里表现的要素,只是一味黑黢黢的画面,他所表达的文学性是内在的精神,这种文学性在张培林在对中国山水画研习的基础上,把自己对命运的感悟和喟叹,对人生的认识和沉思,映射在巨大无边的太行山上,画的是山,写的是心灵。在幽暗崎岖的羊肠小路旁矗立着的石头小屋,孤寂而又坚韧,在山与天空的接壤处兀自耸立着的树,无云的土地上拔地而起的石头泛着青光。沉默的石头,翻滚的泥土,坚韧的山峰被赋予了生命,它们或沉默,或疾行,或孤独地耸立,构成了一幅幅充满激情的画面。
七、张培林的作品也重视文学性,这种文学性是司马迁忍辱写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觉醒与渴望,是被缚的奴隶的尊严,是一曲饱含血泪的《密西西比河》。如果把他的作品比作文学作品的话,不是《水浒》,而是《红与黑》,不是《红楼梦》,而是《巴黎圣母院》。
八、李可染画面上的一束光,影响着他的学生们,也影响着学生的学生——张培林。这束从伦勃朗那里借来的光给中国画增加了力量与厚重,在前辈的画面里,这束光是画面的亮点,引导着观众的视线,而在张培林的画上,这束光除了使人更加集中注意力以外,更是灵魂的出口,是生活的希望。
九、在当今画界,张培林是一个特殊的符号,通过这个特殊的符号,人们可以理解我们民族的苦难悲壮以及她的渴望和奋斗。
十、张培林的画,从不成熟到成熟,从欲言又止到畅所欲言,从不断更新到自我否定,像是一个踯躅学步的孩子终于长大成人,带着人对自由的渴望,跌跌撞撞,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何尝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写照,他就像堂吉诃德,把手中的仅有的画笔当做长矛刺向命运,刺向生活,刺向命运。
十一、读他画,不能不说他的人,看他的人,不能不说到他画。
十二、看张培林的画,我不由得想到珂勒惠支,那个一开始对社会的不仁充满愤恨,到头来对人类的悲剧满是怜悯情怀的人,只有这种情怀,超越了国界,种族,历史和文化,才能真正打动人心。张培林金色和黑色混杂,混乱与庄严并存的画面也使我想到了卫俊秀的书法,粗看枝桠重叠,细看惊心动魄。
十三、都说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绘画的不二法门,真正的艺术家会被造化做感动,但不会被造化所迷惑,所拘泥。然而造化对于张培林来说,不只是面前的太行山,更是他的遭遇,他在作品中述说自己的身世,经历并没有被遗忘,张培林反而从经历中吸取了更大的力量。
在青年时候,张培林没有受到学院式正统的美术教育,年纪大了,才以进修的方式接触到中国画。然而,这对他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因为他在进修之前,已经包含了生活的困难和激情,已经准备好了满肚子的话,进修不过是一个契机,画种也不外乎是一种形式,在北京的学习更使他有可能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倾泻而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张培林的绘画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许多人在他的画前驻足,思考,为了淋漓酣畅的表达,更为卑微又伟大的生命尊严。廖冰兄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张培林这里是不适用的。一飞冲天的猛禽,是涅槃的凤凰,是被缚的奴隶的觉醒。
十四、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直至现在,张培林的身份是县文化馆的退休人员,这是中国从事艺术专业最底层的工作岗位。在这个以社会地位、级别职称论英雄,论作品价格的国度,把艺术娱乐化工具化的当代,注定他的作品将曲高和寡。可是他的作品已经远远超越某些人们从有色眼镜中看到的和感知的程度,他的灵魂也早已和那些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一道,他应该也可以获得比现在更多的人的关注,赢得尊敬和荣誉。
十五、中国文化的两面体现在张培林的身上,一是因言获罪的传统,二是艺术家在这样的环境中的自我更新。
十六、时间对张培林来说,似乎还富裕,又似乎已经不多。他放下了画笔,关了电脑,要到外边走走,看看。2010年,他去了上海世博会,一待就是一星期,他有些贪婪地看着那些现代科技制造的各种奇观,无比兴奋。回到和顺休息了一段,他又跑到香港,虽是旅游,可是领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林林总总,看到了一国两制下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差异。
张培林还想到外边走走,可是冬天了,想必也是冷清。于是他就在和顺呆着,盼望春天的到来。身子乏了,就到澡堂泡个澡,在热气腾腾的澡堂里,思前想后。也曾夜深人静,看着这些耗去自己大半辈子时间和精力的画作潸然泪下,不知身在何处。也曾羡慕别的画家,会走马灯变戏法似地画出一张张画,然后卖钱。也曾想以流行笔法画它一画,可是一拿笔,就想到自己的命运和自己一直坚持的艺术观点。
十七、张培林把自己称为北派的传人。北派,以北方山水雄浑壮阔为基调的审美趣味,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伸张。
焯父
书法家杨金贵的艺术人生高巧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去拜见中国书协会员杨金贵老师。年近七旬的他春风满面,这是惊呼我们的意料。虽然我知道搞艺术的人是不会老的,但像他这样能比实际年龄年轻至少二十岁是让人不可想象的。是什么独特的秘方让他如此的年轻气盛精力充沛呢?带着这样的神秘疑问我开始和他畅谈。
杨老师1948出生在沁源郭道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用他的话讲是当时村里最穷的。小学三年级时随父母迁居到平遥千庄乡林坡村的小山沟里。自此,杨金贵便成了“平遥人”。林坡村离城60华里,树林密结,经常出野猪、豹子没有等。然而,林里的山桃树叶、榆树叶、柳树叶和山杏叶成了人们最钟爱的食物。等到秋天把捡来的野树叶煮熟,放在大篮里砸上石头,然后拿到河水里冲刷,最后放在大缸里压紧,一年到头的食物就全靠它了。早晨起来米汤、糠炒面;中午切点胡萝卜樱樱(用来去野菜的苦味)下点小米,再做一些高粱面叫“和粢饭”,或者把野菜高粱面和成丸子蘸点盐水吃;晚上还是糠炒面。
上学时天不亮就背着书包步行出发了,到中午吃点糠炒面,喝点老师们剩下的面汤就心满意足了。等到休息了回到家里才是最累的时候,要去地里施肥、挖野菜、割草、采蘑菇、拾牛粪、捡椴芽、拾地谷类,还有捡村民挖剩下的土豆等等,有时候还会抓到蛇。大冬天去上山砍柴抬杆,下雪天还是带点糠炒面。饿了的时候吃一口糠炒面,就上雪水就是中午饭。有一次年仅12岁的他抬杆时吐了血,回到家里又看不起病,只有泡上黑豆、喝自己的小便来治病。病稍微好了就赶紧去磨面,以便过年能吃上点包皮面。
当时正值“赶英超美”、“砸锅卖铁”、“吃大锅饭”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潮。家里所有的锅灶和铁具一夜之间都被砸烂支持大炼钢铁;一吹哨,全村人赶紧统一排队去吃大锅饭。17岁那年,他去千庄乡做了话务员,过年过节偶尔才能吃上荞面油糕,这就是享福了。后来凭自己的努力担任团委*,经常下乡到偏远落后的南岭底村。纪念抗日英雄梁奔前在三岔口讲话,那一幕是他这辈子记忆中最神圣最壮烈的时刻。直到去相亲,还是穿着大拇指露在外面的破布鞋和补了又补的烂棉袄。后来岳父家人告诉他,当时过来看热闹的孩子们数了数他棉袄上的补丁竟然有17块。
艰苦的生活一直熬到1970年。当时虽然能吃饱了,但还是离不开糠炒面。6月的一天,汾西矿务局来招工。为了照顾贫困和上进青年,全公社有两个指标,他当时是团员、是积极分子,乡里就推荐他报名。结果体检时他体重只有90斤,太瘦了,不符合标准。他打听到招工的张师傅是河南林县人,憨厚老实,对人又和蔼可亲。于是赶紧去找张师傅求情,但张师傅还是说:“煤矿工作是苦力工,像你这身体根本吃不消”。当时他的脑子里嗡地一下,心想这下可就完了,意识本能让他扑通地跪倒在张师傅面前连声叫:“好心的叔叔,可怜收下我吧,我是因为家里穷吃上不饭没长肉,到了煤矿吃上饭以后还会长个、还会长肉的。”最后几个招工的师傅确实是看到他可怜,就按特殊招工对象收留了他。
1970年7月7日,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他和全县百名矿工坐上了南下两渡煤矿的列车,尽管酷暑难挡,然而心情是激动、欢喜和愉悦的。
培训三天后便开始下井挖煤。井下工作8小时,连食堂吃饭、往井口走、换窑衣和开班前会下来就是12小时。下井前夏天换窑衣还好说,冬天衣服冰凉、汗臭味很浓难闻。到了井下黑乎乎的谁也认不得谁,只能看到眼睛和牙齿。人们在井下没有什么不敢说的脏臭话、还有阴*话,让人恶心想吐。下班后洗澡遇到停水,用手捧起来的水都是稠乎乎的。爱抽烟的工人烟瘾发作时,澡堂里便开始抽烟,烟雾难挡。
他天生胆子大,山村里出来不怕苦、不怕累。又有一个月50斤粮的诱惑,每天下井都是匍匐进去,用短锹先挖上坑,才能蹲下。下班后饿得慌,先买两个窝头边走边吃,等排到时再买一斤面条。每月先把粗粮吃完,把细粮省下来攒够一袋白面的饭票,回家前兑换成白面给家里带回去。白面晾到院子里,邻居们投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说他妈生了个有出息的好儿子。他每月66块钱的工资给父母40元,自己仅留26元生活费,月月如此直到结婚生子。从来没有养成超支花钱的习惯。
煤矿有三大自然灾害:一是顶板塌陷,二是透水,三是瓦斯爆炸。他们这批新工人干了有十几天后,有一天突然有辆煤车跑了,正值下班途中的七名矿工被撞伤,其中有一名矿工是和他同一宿舍的矿友。听说被撞的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当用手抓住小腿的时候,小腿竟被折了回来!仔细一看鞋子里都是血……那次事故之后,好多新去的工人都跑回了平遥,不想再到矿上。(按生产煤的吨数,60万吨的矿井只许死1—2人,但工伤是常事情。有被电死的、有顶板塌了压死的、有被闷死的、有幸免没死也是痨下残疾的、还有被吓得得了精神病了的,相比之下他还算是幸运儿。)
1978年,灵石县文化馆举办书法展览,矿上组织人们去观看,有一幅字深深地吸引了他(后来上海书协主席周慧君写的鲁迅诗)。当时他立在那里一步也舍不得离开,从那时起,他便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书法写好。
回到矿上,他便到处找旧报纸开始练字,忽然发现矿宣传部有位老师临摹的一本字帖很好,于是很大胆地向这位老师借了两天。借到之后如获至宝地抓紧一切时间疯狂临帖。等到还字帖时,老师看到自己临摹的字真是吃了一惊,那是他临的第一本字帖《颜真卿多宝塔碑》,当时市场上还没有卖的字帖。有一天在井下和工友说起自己想写书法没有字帖可临时,工友便说他家里有爷爷留下来的一本字帖,等到他拿来时才知道是唐代欧阳修九成宫折合页的书法字帖。他每天除了下井和睡觉外的时间都用来临帖。当时他们的宿舍在马路上,工友们上下班路过难免会进去小坐,但他一边谈笑,一边写字。给每个人都画了素描相片贴到墙上,不写名字都能得以辨认。没有桌子,就从井下偷上木块拼到一起,下面垫上砖块垒起来就是桌子。井下停电的时候,就用粉笔在大板锹上练字;回家在火车上拿速写本写画;自留地里干活累了用树枝坐下来画写等等,连老婆都说他是“神经病”。
在两渡矿上谁都知道,有两个写书法出名的叫贺兴瑞和景伯龙。凡是两渡的重要活动标语都是他俩来写。他悄悄地在宿舍的墙上写下了“赶上景伯龙,超过贺兴瑞”,每天下班便刻苦用功写字。下班休息,别人都在睡觉,他便开始写书法。但是临摹什么呢?正好一个宿舍的舍友有本*诗词,对于从来没见过这么好书的他来讲,真是爱不释手,一口气就把39页*诗词都背了下来。经过几个月的临摹,他感觉上手很快。后来轮休回到平遥,想找人给指导一下。据当时县交通局局长介绍,交通局下面搬运社有个木工懂书法和篆刻。于是他拿着自己临摹的*诗词欣喜若狂地找到了老师。老师第一句问他,是自己爱好玩高兴呢?还是准备长期坚持写下去呢?他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肯定是想长期坚持写下去。于是老师告诉他想要长期坚持写下去,就得临摹名人的名碑和名帖,不能乱写。
有一次矿上举办首届书法展览,他便鼓起勇气去矿工会领了两张宣纸去参加比赛。开展的时候,矿友说他的作品是一等奖,那两名仰慕已久的书法家是二等奖。他欣喜若狂,高兴得快飞奔起来!(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勤学苦练总算有了点回报)。
1983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北京寄过来的中国书法杂志。上面刊登了他们矿上首届书法展览获奖作品,一等奖只有一名就是他。当时他瞪圆了眼睛不敢相信那是真实,因为长久以来他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的书法能有如此之大的名气。后来回到平遥答谢老师,老师已经在杂志上看到了他的楷书成就,为他打心底里高兴和欣慰。此后他挣着井下费,在井上到处写标语出板报。次年,他被单位选派到汾西矿务局书画培训一个月。报到后才知道培训是为了迎接全国煤矿第一届书法美术展,辅导他们的老师是从北京请来的书画名家。培训期间他用楷书写了兰亭序让老师一起带回北京参赛。几个月后矿务局来了通知,他的作品入选并邀去北京美术馆参加开幕式和参加中国煤炭部举办的书法培训班。去了之后才知道山西仅有三名作者入选。培训回来之后,他在矿务局也算小有名气,后来领导找到他要用他写的字改写汾西矿务局的牌匾。两渡火车站重建时,站长找到他让画了一张国画、一张油画和列车时刻表,还有四条条屏(后来离开二十多年后再回去,那些字画还挂在那里,亲切地让他回忆良久)。
1984年,他被调到太原煤气化公司嘉乐泉矿,还是在井下工作。有一天下班途中,遇到了从两渡煤矿调来的霍经理和矿长相跟着。霍经理一下就认出了他“这不是杨金贵吗?你怎么也调过来了?”……简单的问候让他心里暖暖的不知说什么好!(在两渡时霍经理负责过矿工参加全国书画培训班,他也给霍经理写过字。所以对他还是有印象,能叫上他的名字)。过来十来天,矿上通知他去太原找霍经理,当时他以为是让他去写字,于是带了纸和笔去找霍经理,见了之后才知道是让他去找煤气化公司工会李主席。他也没说干什么,就赶紧去找李主席,以为是让给李主席写字。
见了李主席才知道,自己被调到了公司工会上班。又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情!他简直又一次兴奋到了极点。更是从来没有梦过的好事情,竟然能降临和光顾到他的头上。
就这样他从18年的井下煤矿工人,一下子变成煤气化公司的正式机关干部。一个小学生文凭的他能和大学生们一起办公,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自己数十年来如一日没有间断过刻苦练字的辛勤汗水换来的。他小心翼翼一如既往地坚持练习写字,就是领导们出国办事也都是带着他的书法作品,成了煤气化公司领导们礼尚往来的礼品。
而后来隔两年全公司就搞一次美术书法展,来推动公司的文化发展。相继又成立了书法协会,他被推选为书协主席。厂矿的标语,壁报还有每次活动的大标语都在他的带领下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
河西区每次举办书法展览活动,他的作品总是一等奖。他的楷书没人能超过,为推动整个河西区的书法文化建设,专门为他举办了“杨金贵书法展”。记得1990年5月17日,山西省科技馆阳光明媚、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省市县的领导书法家以及煤气化公司的领导们都出席了会议。展后山西电视台、中央四台和中央对外频道(用英语)都对煤矿书法家杨金贵进行了播出。小有名气之后,他更加的勤奋刻苦,还是不忘找古代名家的名帖进行临摹。为了读懂古文,先用小楷抄写两次“古文观止”。他多次参加省市和国家书法展览并获奖,先后又加入了省市书协。1994年加入了中国书协。
如今,他已年近花甲迈入古稀,当年的贵人霍经理也离开了人世。然而他不忘传授书法知识,经常给省市党校干部和社会各界喜爱书法的朋友们作讲座,同时也结识了不少有志创业的成功人士。他更没有忘记报答家乡的父老乡亲,用力所能及的书法作品来歌颂家乡平遥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平遥尽管是他的第二故乡,但他已深深融入和眷恋着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劳动人民。到现在他每天还坚持一至二小时的练笔,这是他做人的准则。也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
感受了一下午杨老师各种书法的飘逸与灵动,各种笔体展现的淋漓尽致,饱经风霜又丰富多彩。如此颇深的造诣肯定是得天于他苦难沧桑的一生。
灵石关生成先生的钢笔风景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