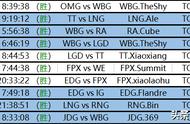所谓“伪知青”,即采取“投亲”形式、貌似落户乡下,空担知青其名、徒享知青之惠,未经下放之苦、不曾扎根农村,如我一般“是又不是,不是也是”的知青一代。处在知青下放岁月的末端,只是将户籍迁往农村,人却原地不动,未住一宿于“广阔天地”,未历半日之田间劳作,就是我“伪知青”生涯的真实写照。1974年,我还在上着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姐姐已经进入高中毕业季了。那时的街头,时常看到写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是作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的“最高指示”而深入到社会各阶层的。印象中,每每有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无论是主动申请还是被要求的,政府都会举行盛大的出行仪式。看着他们穿着或黄或蓝的军式服装、肩起背包、手提网兜坐在大卡车上的样子,感觉是一次光荣的奔赴。为此,接到通知的工厂、社区和学校,往往组织工人、居民和学生们,走到划定的街头区域,欢送一批批知识青年去“上山下乡干革命”。当时学生下放农村的政策是:家中独生子女毕业后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则按照“二三留一、四留二”的原则自主确定。具体走谁留谁,由各家商定后,将结果报备至所在公社(即居委会),到时由政府知青办统一协调安排下放至相应的公社(乡镇)村队。人是环境的动物,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便会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惯性。而习惯就像一座没有城墙的围城,虽然肉眼看不见它,却分明能感到它的无处不在,并且于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在城市环境中生活习惯了,倒也并不觉得有多少优越和伟大,日子就这样在简单和平凡中回环往复。可一旦走向城市之外,昂着首去靠近农村,便会觉得城市虽拥挤但很温馨,虽琐碎却有滋味。如此一比,作为“城里人”的高大和骄傲的形象,就清晰在言行举止里了。那个年代,生在城里,有了城市居民的户口,再俯视郊外的农村时,想不自以为是都难。何以至此?因为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城里的大人们虽然每天八小时在工厂商店里辛苦地工作着,却有着固定的工资,到月就能关饷,就可以买一些生存必需品,生活也随之润滑了起来。而乡下的大人们却要从早到晚地冒着风吹日晒、雨打霜侵,几乎是要没日没夜地躬身在农田里劳作。而且没有每月的固定工资可领,日常的家用全靠一年日积月累的劳动工分换取年终分配的有限收入,且用以支撑着全年的开支。所以就能省则省,能少花绝不多用。城里的孩子们从小就入托儿所、进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平素还有或多或少的零花钱可用;还有或稀罕或简单的零食可吃;星期天或节假日还可以有看电影、逛公园的休闲娱乐。而乡下几乎没有令人羡慕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乡下的小孩子就像小草一样在野地里疯长。即便长大了上学也要跑到很远的学校,还要帮助大人做些捡柴禾、打猪草、拾稻穗的活计。而且一般农村家庭的孩子很少能念到高中的,往往小学或初中一念完就告别了学校,就被家里的劳动力和田里的农活需要着,上高中就成了一种奢华。如果硬要说有休闲娱乐活动的话,那只能将在沟坎里抓鱼摸虾或光着屁股下河洗澡算在其中了。“农业落后于工业,乡村落后于城市,体力劳动者在文化技术水平、劳动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落后于脑力劳动者”,这就是存在于近现代人类社会的“三大差别”。这在我们一代始有记忆就有了依稀的认识,并随着日后的上学读书、参加生产和社会实践活动,就愈益地清楚和深刻了。我的母亲、三婶、四婶都曾生长、生活在农村,都以嫁给家境并不富裕的我父亲、三叔、四叔为荣。纵身一嫁而跳出了“农门”,迎接她们的将是梦一般美好的未来。虽然依旧简单与清贫,但那毕竟是城里人生活,自带着无数光环。六十年代初中期,虽然还没有“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背景,但“下放”一说已然存在。其主要是城市里的那些有历史问题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举家被迁徙到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记得小时候,我家附近薛家巷头开茶水炉的四妈妈家,东圈门12号的周先生家,以及双忠祠10号的江家,好像都是一夜之间从我们市井生活中消失了的,大人告诉说是全家被下放到兴化去了。上初中时,读了施耐庵的《水浒传》,才知道所谓“下放”,其实就类似于“有罪之身的发配”。门口的上述几家看起来都是好人,不知获了何罪?转而想想《水浒传》里被充军发配的,又有哪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十年,即1968年-1978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运动了,共计八千万“知青”大军席卷广阔天地,可谓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后来知道是那时的经济不发达,创造不出更多的就业岗位。而知识青年却如雨后春笋一般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使整个城市变得拥挤不堪,社会空间日趋促狭。与其静待蜂拥而出的知识青年在城里难作为甚或乱作为,不如令其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于是英明领袖发出英明号召,芸芸知青便成群结队、乖乖地“上山下乡”去了。如此一来的成效有目共睹:还城市以既有的宁静与平衡,还社会以有序的稳定与安生。

对于那个年代由城市“下放”到农村去的知青生活,其实我是没有直接感知的。如果设想将自己代入式地体验一把,或许是会像飞出鸟笼的小鸟一样,一下子解除了家庭家人和学校老师的束缚,呼吸着满满自由的空气,该是多么地舒爽和畅意。可这种新鲜的美好和放纵的自由,维持不了很久,旋即就会为举目无亲的孤寂、田间地头劳作的辛苦、以及事无巨细的自力更生而稀释成一锅的清汤寡水。最要命的是面对农村简单频繁的生产和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如何咬着牙在茫茫无期中说服自己试着隐忍、学会坚持。我居住的那条街巷中,也曾有六八届、六九届毕业后下放到乡下的家庭。那时候还没有知青返城回乡一说,一旦户口转到下放的农村,其身份立马就摇身一变为“乡下人”了。起初的几个月,中途或有回到城里的家中探望的,父母和家人都捧着极大的热情嘘寒问暖,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令其有备感关心的温暖。后来不知为何,就渐渐地变成了半年或一年才回来一趟。有时到了端午、中秋节日,也不见回家团圆的人影。我隐隐约约地感到,那是一种不同既往、难以言状的家庭氛围,尤其是兄弟姐妹言语的亲昵和投诸的眼神,在悄然无声地发生着改变。那种改变就像家中出现了乡下来的亲戚,就像突然多出一个人来分锅中羹。平素的大大咧咧,由于身份的置换而变得异常敏感,能从兄弟姐妹不经意的话语、声调和眼神中读出什么来。于是,就渐渐变得沉默寡语、不苟言笑了,就变得来去匆匆、“没有大事不登门”了......对此,我是有生活的,绝非一厢情愿地罔顾事实,或似是而非地神经过敏。小时候或有爷爷的农村表亲偶来看表哥表嫂,提半篮毛桃、番茄之类的;或有奶奶在杨庙胡庄的亲眷,为着家长里短的纠葛来请奶奶断个是非曲直。每当此时,爷爷奶奶自是准备比平时好些的饭菜,毕竟一年到头不常来。殊不知那些香喷喷的鱼肉蛋之类美味佳肴,不仅他们乡下很少有,就是我们城里平日饭桌上也少见。尤当这些我叫做三表爹二嬢孃的筷头在荤菜盘中盘旋的时候,心中就会生出余悸来;如果是第二、第三次伸筷出击,心中就会莫名地疼痛;遇到爷爷奶奶夹菜给他们,心中竟会暗自怀恨。以至于其后他们再到家里来的时候,甚至就厌烦得不再予以理会了。现在想来,真的嫌儿时的自己实在没出息,为了一己口腹之欲,不惜将内心的丑陋进行到底。带着这种儿时天性的丑陋,便试着去观察对门的老大和斜对门云姐从乡下回来的情况,好像他们家中这些我所熟悉的孩子,其言语神态的诸多表现,也大抵与我内心的不洁不善有些相仿佛。但愿我只是个别人家孩子,是个了无教养的另类。其实,人家兄弟姊妹感情好着呢,对下放农村的大哥二姐们,心中满是同情和怜惜。对其关爱尚且恐有不至,岂能无视血缘亲情而自顾猥琐地打着灰暗的“小九九”?姐姐到了高二下学期,就面临着毕业后的去向问题。或者下放农村,或者留城待业,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那时我们这一代大多数是三四个子女的家庭,更多子女的家庭也不少见。比如黄家园巷头东的谭家兄弟,分别生了八九个丫头;比如三祝庵中西段的刘皮匠和郭裁缝家也分别养了八九个孩子。因此,很多家庭面对自己子女的去留问题,都会面临着选择难、难选择的困惑与尬境。摆在当下,孰去孰留确是两难的选择。可在当时,好多人家几乎是一顿饭的工夫就交上了自己的答案。甚至有的都不用想,落笔就是自然而然。按照传统的习惯思维答题,自然是留男不留女,因为男子是家族的命脉,女子是泼出的盆水,无须多虑。按照年龄错落顺序排列,“留长走次”或“留次走长”(一般根据长次的性别来定)。这看起来是公道公允,儿女们也语塞,因为是自然的排序,想换位都不行。而政府对此往往不加干预,只要下放的指标落实到具体的人头就行。至于是谁戴了下放的帽子,家长缘何这般安排,干他鸟事,才不“咸吃萝卜淡操心”呢!我们家中有四个子女,就这么一姐一弟地相间出恰好。扬州有长女长子,山西有次女次子。山西那边是其次的,面临选择还有较远的距离,暂且不论罢了。姐姐当年就毕业,选择已是眼前的严峻,如何徘徊也终究绕不过去。也许是女孩子心思缜密活泛,也许事到临头不容不想,最终的结果是姐姐留城了,达到了她的所愿。对我们家来说,姐姐留城分配工作,家人似乎并没有被两难的困惑纠缠着,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

虽然事后父母曾流露过当时姐姐写过一封寄往山西的信,表达了自己身体不好、吃不了农村生产劳动的艰辛、想先行留城的诉求。但我知道,即便没有姐姐那封山西去信,她一样会留城分配工作的,这基于我们王家“重女抑男”的传统和父母正直坦然的为人。虽然间或听到过邻居家和家族其他成员对此有不同声音的异议,而在我来看,这一结果完全是势在必行的当然。因为“一切让着姐姐”观念意识,从小就耳濡目染后根植于心,并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就潜移默化成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天经地义。1977年,轮着我高中毕业,也同样地面临着下放农村的问题。不同的是问题已不是难题,无需家人们再进行平衡和选择。那年的暑假我去了山西,在父母工作的晋华纺织厂做着临时工。在中学放假其间做临时工,于我已是一种常态。曾为日用棉织厂加工手套,主要是用钩针、缝被针绞指头和绑子,三分钱一副,一个假期下来交学杂费无忧;曾在扬州食品制造厂分拣过西红柿,用于装箱出口,一天可以挣上八毛大钱;曾在扬州印染厂做过专值夜班的守卫,值一夜班就有一块银子的进项。这应算得上是勤工俭学了。假期的打工所得,除解决学期费用和留一点零花钱外,其余全部上缴给爷爷奶奶贴补家用了。如此来看,我在青少年的时候,的确是个听话懂事明理的好孩子。其实,当我在父母的工厂做零时工的时候,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我的社会角色就已经悄然变换为下放知青了。这其中老叔叔应是帮了忙的,否则,我断然不会以“投亲”的形式,将户口落在邗江县六圩公社永安大队头筐生产队的。因为当时政策允许以“投亲”形式落实下放的地点,因为婶婶的家就在那个公社大队生产队,因为当时那里社队经济发展比较好,一个工分值可达五六毛钱(好多农村的工分值只有两三毛钱)。这在当时,确实退而求次后的上好选项。其间,还闹了一出小故事。当年下放的时候,需要将本人的户口转往下放的公社。可是在具体操作时,家人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户口簿,自然怀疑是我为躲避下放而将户口簿藏匿了起来。这种怀疑是想当然的,也是爷爷奶奶所深信的,因为它符合通常“获利者疑也”的逻辑。就连山西的父母也相信是我从中作的祟,任我如何撇清也洗不白自己。后来,我连解释都觉得无趣,干脆一笑置之,权当“无若有”了。殊不知,一个小小户口簿遗失岂能挡得住下放政策的执行到位?难分明是我的天真还是家人的无邪?我的户口最终还是丝毫无碍地落在那个公社大队生产队里了。从山西回来后,我知道自己已是寄居在那个叫做“东圈门1号”的家里了,虽然爷爷奶奶和已经工作的姐姐并不这么看,但这无妨我内心的认知。虽然当时还没有知青回城的任何风声,但有关知青政策规定较过去已经相当宽松了:一是政府每月给每个知青发放生活补贴10元钱,每半年领取;二是公社每月给每个知青发放稻米30斤,无需付钱;三是不必定期到下放的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想在原来住地的家里待多久都行。77年10月,广播里传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就像一场十年不遇的海洋风暴,一时间呼啸在多少中华儿女的胸膛。作为在十年动乱的浑浑噩噩中惺忪成长的应届毕业生,我们有幸被列入可以参加的范围,算是最年幼无知的浮在浅表的一层了。几乎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化知识,就连简单的语法修辞、历史朝代的演变、祖国山川河流的地理都没弄明白,又几乎没有时间且不懂得如何去复习备考,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走上了考场。如果说对自己浅薄的文化底子还有点清醒的话,记得那年底我报考的是中专,选择的志愿是“徐州铁路师范”。这般选择,不知道是否与三叔有关,因为他是商专毕业,在徐州百货站工作,还因为读师范是免费的。俗话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我们这一代人如同滚滚投考洪流中的泡沫,自然就被冲刷到岸边的沙滩上。从瓜州回来的晚上,一身空空如也的落寞,似已预知着结果的渺茫。那一年高考中榜的,绝大多数是老三届下放农村的知青,因为他们文化基础来得扎实,还未及受到“文革动乱”的影响,并且参加高考几乎是他们从“广阔天地里”抽身而出的唯一希望。而我们这群“被耽误的一代”,能侥幸在浑水中摸到鱼虾的,可谓是寥寥无几。奇怪的是,落榜后,包括家人、同学和邻里,既没有人来继续鼓励,也没有人为之扼腕叹息,更没有人嗤之以鼻,当然也没有人痛悔难过。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一样的烟火生活依旧在那条熟悉的街巷里缓缓流动。这是否因为我居住附近百米人家没人参考?还是因为整个社会几乎没人知道我的参考?也许正是这样,因为我已是一名通过“投亲”方式下放的知青,除了家人外,再没有其他社会人关注我的存在了,包括我下放的社队,包括我熟悉的邻居。或是由于每月有着政府的知青生活补贴,还有着公社每月定额供应的知青口粮,即使赖在家中不到乡下劳动,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我并不是“坐在家里吃闲饭”的,当然也就不会有“冷言白眼、脸色难看”的“被羞愧”了。

为了备战1978年的高考,好像七五届以后的很多青年都在秣马厉兵地复习功课,有一种清风始来的感觉。当时,除了高中课本以外,几乎没有现成的复习资料,都在既有的教科书上下功夫。记得一次偶然路过国庆路上的新华书店,见有人在南侧的小门买书,近前一看是上海科技出版社再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赶紧买了一套,如获至宝。后来市内中学纷纷举办高考补习班,每晚七点至九点由各门老师进行讲大课,头二百人坐在礼堂内,很有一种“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豪情壮志。由于在上学阶段老师没有很好地教,学生也没有很好地学,“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便将文化知识积贫积弱的青年一代打得七零八落、狼狈不堪。如今,相距第二次高考也只有半年的时间,要想在半年内将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回炉再造,可谓是难如登天。那时面临着一大堆需要补习的各科文化内容,面临着也是匆忙上阵的老师“填鸭式”地上大课,除了死记硬背一些概念、定义、公式、定理外,几乎没有更好的学习方法,更谈不上懂得和理解。四年半的初高中学习生涯,我们是一路连玩带学中走过来的,没学到正儿八经的文化知识,玩得却很尽兴。尤其那时实行的开卷考试,只要临考前抖一点小机灵,开卷时能很快地翻找到书上现成的答案,速抄疾写往往就能考到很不错的高分。“分数高,学习就好”,这种全社会认知上的偏颇,也强化了我们在学习上投机取巧的钻营心理。那种“读死书、死读书”的努力与踏实,反而遭人诟病。于是,在家里迎考自学和补习班上课后,才猛地发觉自己无论是哪一科,都停留在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混沌阶段。老师曾教过的内容,能留在记忆中的,仅仅是一些残缺不全的知识碎片。正如夫子所言:“学,而后知不足”。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越学对自己越没有信心,越学越感到生活的孤独。带着这样的状态迎考,想要创造出“死鱼翻身”的奇迹,除非脑海中“忽有一道灵光闪现”。记得那年本地高考录取线是300分,老叔叔查了我分数说是288分,除语文、政治、历史,其他科目均在及格线以下。此后的接连几天,虽然家人和同学并未说过什么,但我的内心开始有了失落和无助的空虚,同时也开始有了“流浪在城市边缘”的索然,甚至有了想要一头扎到乡下去、远离熟悉的人群和街巷的冲动。恰在此时,有个要好的同学前来问我,说是其堂兄在某小学当校长,该校三年级语文老师因病住院,是否有意前往代课?学校在解放桥以东,距离不算远;月薪30元,收入也不错;代教小学三年级语文课,自忖“力所能及”;生活为之充实,还能走出“落榜有闲,无事生非”的阴影。于是,我便应了。大概是同学的父亲是校长的叔叔,在其面前说了些溢美之词。因而我未经试课,前去领了教材、备课本和笔墨之类的,就直接走上了三年级教室的讲台。当了代课老师才晓得,原来老师手中除了课本以外,还有对应的教学参考书,那上面每一课的生字、词解、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课时要求等什么都有,实际上就是一个书面老师。即便不会教书,照着上面的提纲去做,亦能勉强为师。难怪我们中学打篮球出身的班主任,居然又是教政治的主课老师,又是教语文的兼课老师呢!记得我走上讲台教的第一课《歌唱祖国》,好像是歌词。我在上面津津有味、滔滔不绝地讲着,一帮学生坐在课桌后张着眼睛、似懂非懂地听着。你还别说,那一刻初为人师的我,还真有了当初我们班主任老师的感觉,俨然一种神圣的奇妙。估计校长有意无意地在教室外听过我的课,感觉我讲课的声音甚是洪亮,普通话也比较标准,板书也很漂亮,讲解还算得法。否则,同学的父母怎会见面时对我褒奖不已呢。做代课老师的日子里,无论是校长与校工、同僚与学生,见面的问候或闲聊,必先冠以“某老师”的称谓,喊得人心中暖暖的。回到家后,我也乐意将上课的情况、校里所见所闻、家访的情形,以一种自豪的口吻复述给爷爷奶奶听。见我津津乐道地说得有礼有节、声情并茂,他们总是放下碗筷像学生一般认真倾听,而后点头称道:不错,我们家孙子长大成人了,是个小老师了。其实,此时称我老师是不够准确的,忽略了一个“代”字。从本质上讲,我只是小教队伍的“替补队员”和“临时工”而已。缘于我是校长介绍而来,教学表现也还不错,与同事相处比较谦和,加之因病告假的那位近期返岗无望。种种迹象表明我是可以较长时间“代”下去的,甚至有可能去掉“代”字(当时师资力量明显不足,在编教师严重短缺)。循着校长有条有理的分析和话语间透出的期许,我开始有了边教边学、再征明年的决心。因为不管是纳入“编制”的可能,还是努力复习再次应考的坚定,都是摘掉“知青”帽子、实现“农转非”的有效途径。于是生活的云层里,渐渐折射出希望的光芒来。那年深秋的一天,无意中在黄家园居委会门前看到了部队冬季招兵的横幅和标语,像是久埋于内心深处的一丝被触碰到了。此刻,我猛然醒悟,原来当兵到部队曾是深植我内心的一种*,可惜苦于一直没机会去实现它;原来当兵到部队也是摘掉“知青”帽子、实现“农转非”的第三条路。于是,闪身进去,稍加问询,知道自己完全符合应征入伍的条件;于是,同什么人也没说,便驱车前往下放的公社着手报名。接下来按照征兵程序,进行登记、审核、体检等,一切都很顺利。而我却像无事人一样地照常去学校讲课备课、批阅作文、作业和试卷、有重点地实施家访,履行着一名老师应尽的职责。一直到《入伍通知书》发放的那一刻,家人和邻里同学才知道我即将去服兵役的消息。虽然家人对此感到比较突然,但似乎也找不到好的反对理由。当然“生米已煮成熟饭”,反对亦无济于事。其实,家人早就知道这个孙子心里有事是不会和他们商量的,他们更知道自己给不出有用的意见。所以,孩子大了,自己的事情就由着他自己做主去吧。接到《入伍通知书》后,立即写信告知山西。父母对我的告知好像还是持支持的态度,毕竟当兵虽然要吃苦,但能锻炼改造人,这对于年轻的我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再说,打小我就独立惯了,他们相信我会很快适应部队艰苦环境和纪律约束的。真正对此高兴无比的还是我本人,其程度不亚于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心情就好像穿越到了1949年。因为从此后,我将告别下放的农村,摘掉“知青”帽子,实现“农转非”身份的回归;还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第三条道”,而且这条道靠着我自身努力已经走通了;更因为当兵是我冥冥之中的理想曙光,而这曙光如今已经照耀在我身上。我要走了,朝着北方的军营,向着未知的美好。于是,我骑着车子一路奔向落户一年多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为了感谢和告别。因为这里并没有想象中起早贪黑、稻田劳作、举目无亲、内心孤寂的悲凉,有的只是照顾、理解与宽容。我要走了,朝着北方的军营,向着未知的美好。于是,我最后一次来到代课的那座小学,也是为了感谢和道别。因为在这里我实现了从中学回到小学的一回反刍,实现了从学生转为老师的一次升华。虽只有短短的一百多个日子,却是我青少年芳华的一段美妙绽放,也是我步入社会后的一个干净而有力的起点。我要走了,朝着北方的军营,向着未知的美好。于是,我满怀诚恳地来到了左邻右舍的家里,还是为了感谢和道别。因为这里的街坊,这里的街巷不仅见证了我的成长,还给了我们一家老小许多的亲热体贴和关心照顾,让我感到了邻里之间的平和融洽和街巷烟火的脉脉温度。我要走了,朝着北方的军营,向着未知的美好。于是,我依依不舍地来到了爷爷奶奶面前,也还是为了感谢和道别。因为他们用与生俱来的质朴和善良滋润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尤其在我“非转农”的时光里,让我觉出了岁月温暖如初。惟愿离开我的日子后,他们继续葆有着安详与健康。我要走了,朝着北方的军营,向着未知的美好。于是,我满含深情地走进自己的小屋,依然是为了感谢和道别。将这十五年时光悠悠和熟悉的小屋四周悉数装入行囊中。当然少不了觉醒的书笔和文艺的口琴;少不了少年的吃苦耐劳和自强独立;少不了干净整齐的习惯和严于律己的自觉。因为,我执著地相信,未来的日子里,这一切都用得着。
简 介欣春,微名新春快乐,江苏广陵人。乐山乐水乐远野,且行且思且涂鸦。闲有捉笔时,聊表方寸心。若是因山因水、因人因事,由感而动,则想让文字发出自己的清音,竭力不染纤尘,是以慰藉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