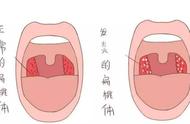文学大家巴金,早在1927年就在法国巴黎开始他的创作生活了。结果到了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发觉自己已被打成“阶级敌人”。“真是在顷刻之间,我已变成文学界中的一霸。”这位作家于1980年在日本京都的一次讲话中说:“我经常被拉出去在公共场所受批斗。”
在“四人帮”统治期间,他就住在上海。他被控为“叛徒”,被控为“反革命分子”。上海街头的墙上贴满了谴责他的大字报,勒令他不准再写作。从此,他再也不能拿起笔来写文章了:“足足十年就这样白白地虚掷掉”了。但是,巴金终于侥幸地活下来了。在“四人帮”粉碎后,他又拿起笔来写作了。
他早期的作品和小说,又重印发行,其中许多作品还译成英文和其他语种的译本,从而博得了世界各国的新读者。在中国,他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作协主席。
1984年5月,他病方愈就离开医院踏上旅途,来到东京参加国际笔会第47届年会。这是各国诗人、剧作家、编辑、散文家和小说家的一次集会。他作为一位贵宾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核时代的文学一一我们为什么写作?”的讲话。他的讲话把650位代表的注意力一下子吸住了。为什么写作?他说:“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我已经追求了一生。”巴金在讲话中说:“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答案。”他又说:“在东京的大会上我们用欢欣的语调畅谈未来的美景,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不想到广岛的悲剧。”
在这次年会上,巴金成为激动大会的中心人物。
巴金因患有“帕金森”病症,他走路须持手杖,看起来有点衰老;然而他那一口宏亮的四川乡音,说得很爽朗。他自称为“抱病的老人”。他十分怀念自己青年时代的巴黎生活。他的第一部小说《毁灭》就在巴黎创作的。那时,他怀念着自已的祖国,他对侨居美国的意大利进步工人萨珂和凡塞蒂受到监禁感到愤怒(注:这两位工人后来被指控同谋*人罪而被处死刑。英国作家辛克菜的小说《波士顿》就为这次冤案而写的)。他不但同凡塞蒂通信,而且还把凡塞蒂写的《自传》译成中文。就在他译完了这本书时,这两位工人被判了死刑。他为此愤慨万分。
他在大会上说,那时“我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一家小旅馆的五层楼上的一间小房间内,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急急地动着笔。”他接着说:“我写完了第一部小说时,心里的火渐渐熄灭,我得到了短时期的安宁。从1927年到现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终不曾放下这支笔。”
在东京招待会上,巴金畅谈他的作品和他的回忆录。他说,他不愿意“空手”离开人间。
他是不会“空手”离开人间的。1984年春在北京发行的英文《中国文学》杂志,就专载了新译的巴金的三篇早期作品和他在1980年访问东京时的讲话稿。这本杂志还报道说,四川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10卷本的《巴金创作五十年选集(1931~1981)》。
巴金把他自己的创作分为四个时期。1928~1948年为第一个时期。其间作品包括两部“三部曲”:《雾》《雨》《电》和《家》《春》《秋》。前者描写知识分子追求革命的曲折道路,后者抨击封建家庭的家长制的威权。这一时期的作品已收集在1962年出版的14卷本的《巴金选集》。第二时期也就是他第二个20年的创作时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过,作者自己对这一时期的作品并不满意。他说,这因为“我对新社会还不熟悉”。第三时期是作者处于“冬眠”状态时期,也就是“文革”时期。接着,就是作者的第四个创作时期。那时,他制订了一个5年创作计划。其中包括:现在已经出版的《随感》散文集;19世纪俄罗斯革命作家赫尔岑的5卷本回忆录《往事与思考》的译作。
……他在东京国际笔会的大会上一再地宣称:我写作,这是我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更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