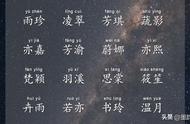<一>她走了三年了
林奕含走了三年了。她把她的苦痛与警醒留给世人。
三年前,她把她的经历喻在故事里,出版成册;她把她羞耻的疮疤与每一刻灵魂受到的折磨都揭开给人展览。然后离开。
这是多艰难的一件事呢?我想了很久想不出一个可堪譬喻的例子,因为我不曾经历,我无法确切地体会她有多痛。
接受访谈时,她说每一句话之间的停顿好像都在重新整理自己行将崩溃的情绪,那渗透进她每一寸血管里,已折辱她无数的分分秒秒,生生不息、不曾停止的情绪。
“我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就像有人失去他的眼睛然后再也拿不回来一样。但与其说是快乐,说得更准确一点是热情。我失去了吃东西的热情,我失去了与人交际的热情,以至于到最后我失去了对生命的热情。”所以她离开。
<二>她有错吗?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爱上了诱奸犯」的故事。”林奕含这样说。
房思琪为了防止自己无法自洽“自己”和“自己人生”的存在,她选择将发生的一切定义为“爱”。这当然不是普适的爱,因为在外人看来,她只是个“文学读太多”的疯子。可若不如此,她又当如何呢?是成为饼干,告诉自己最信赖的人,然后遭众叛亲离?还是成为郭晓琦,自暴自弃,糟蹋自己?还是公之于众,遭千夫所指?她没有选择,抑或是选择都摆在她面前,她选择最不致让她抛弃自己的那一条路。她选择“爱”上老师,这个剥光她的衣服,抽她巴掌却让她为之道歉的罪犯。「老师只是选择了粗暴的方式来爱你。」可她竟接受了,「当然要借口,没有借口,我跟你便不活了吗?」否则她要如何自洽呢?
她们本该有一个平凡而正常的人生轨迹,可她们的人生从少女时期就被性犯罪者给歪斜了。
她是她人生的赝品,于房思琪是,于林奕含也是。
<三>文学的爱与恨
林奕含是一个何其迷信文字的人,她享受文学的深奥,文字的精妙。可当她得知得诺奖的“文坛奇才”奈波尔却嫖娼家暴,在两性关系之间坏事做尽,她懵然了。
她不明白,“思无邪”到底是文人心之所向抑或只是他们的巧言令色?
“艺术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呢?”
“艺术是否本身就是一种巧言令色而已呢?
她这些年来所热爱的、唯一的慰藉与寄托,到头来却只是某些罪犯的巧言令色而已吗?
于是她把这些叩问灌进“李国华”里。
伊纹和思琪,她们都热爱文学,在文学之海中徜徉,以排解人生的苦闷。伊纹带思琪进入文学的大门,可思琪却在自己的世界观尚未成型时被国文老师李国华强行扭曲、歪斜,在这逐渐扭曲的爱情观中,她同样只能倚靠文学解释她“下等的”“畸爱”。她强迫自己是“曹衣带水”,李老师是“吴带当风”,否则她又该当如何呢?
「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
文学带给她们热爱、见地、更广域的思考方式,也实实在在地毁了她们。
“一个文人千锤百炼的真心,最终不过是食色性也而已。”林奕含想不明白。
<四>性教育
「思琪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的家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
妈妈诡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性教育不就是这样吗。”
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还没开学。」
我永远感谢我三岁时我的妈妈不是告诉我:我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而是在我生日时送了我一整套画本,告诉我我是从母亲的子宫里来的。我感谢我的妈妈从不对性教育讳莫如深,她告诉我:无论是谁都不可以碰你的下体。
可我没办法告诉全世界的妈妈:性教育不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而是给所有的人,所有有可能受到性侵害的人,以及所有有可能性侵害别人的人。
「思琪在家一面整理行李,一面用一种天真的口吻对妈妈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谁?”“不认识。”“这么小年纪就这么*。”
思琪不说话了,她一瞬间决定从此一辈子不说话了。」
看到这里一瞬间我觉得我失语了。“受害有罪论”还要从浩浩汤汤五千年的文明贯穿始终,仍然残害着现代文明高度发达下仍处于弱势的受害者吗?穿的少就活该被说“*”吗?长得漂亮示于人前就活该被强奸吗?「都怪你,你太漂亮了。」这句话还要成为多少犯罪者及帮凶的借口呢!
<五>抑郁症与精神病
“所谓的‘解离’呢,以前的人会叫它精神分裂。现在有一个比较优雅的名字,叫做‘思觉失调’。但我更喜欢用柏拉图的一句话来叙述它,就是‘灵肉对立’。因为我肉体受到的创痛太大了,以至于我的灵魂要离开我的身体我才能活下去。”
高二那年患上重度抑郁症,后来因为精神疾病一次重考、两度休学。她吃着让她思想迟钝的药,来麻痹她的苦痛。可外人却问她:“为什么不爬山、听音乐呢?”
可这病和白血病一样,不是人让自己的白血球乖乖的,白血病就没了。这病让人失去的情绪,和失去一条腿或一双眼也是一样的,不是听听音乐、爬爬山,告诉自己要快乐,那快乐就能复明的。
她的经历,她的思绪,从来都是她自己。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该为外人道。她无法控制自己解离,就好像她无法控制自*一样。这也不该为外人道:“你为什么不能坚强一点呢?”“如果她当时归顺了主便可解脱。”可说这话的人到底有什么资格和立场这样说呢?
她问:“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期待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褴褛、口齿不清、六十天不洗澡,他就会相信我有精神病?”难道苦痛只是世人所见的腌臜与不堪吗?人到底有多肤浅、多么不懂得共情与尊重呢?
“如果我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那么我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要成为一个对他人的痛苦有更多想象力的人;……;我想要成为一个可以实质上帮助精神病去污名化的人。”她走了三年了,这事依旧没有改变。还好她没抱着期待。
<六>后记
我看这本书时,仿若心被溺在深海里,无法呼救,无法呼吸,水压把心挤压得难以泵血,整个空间只有这一颗孤独而无助的心。我不敢说我可以完完全全体会到她们的伤痛,但我实实在在是在替她们、替所有有相似经历的人、替自己痛着的。
“在阅读的时候, 当你感受到痛苦,那都是真实的;但若你感受到了美,那也都是真实的。当你感受到那些所谓真实的痛苦,那全部都是由文字和修辞建构而来的。”
“书出版后我被冠上成功之类的字眼,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因为书里的李国华仍在执业,我走在路上还能看到他的招牌,他并没有死,也不会死,这样的事情仍然在发生,所以没什么成不成功。”她只好这样说。
林奕含不求读者怜悯,甚至不求社会因为她一个人的经历、她写的这本小说,可以对性犯罪有更实质性的制裁,因为她早就无力而失望了,也因为,她确确实实地明白这实在很难实现,她便不给自己这丝希冀了。“最初只是为了排解自己的情绪而写罢了。”她只好这样说。
,